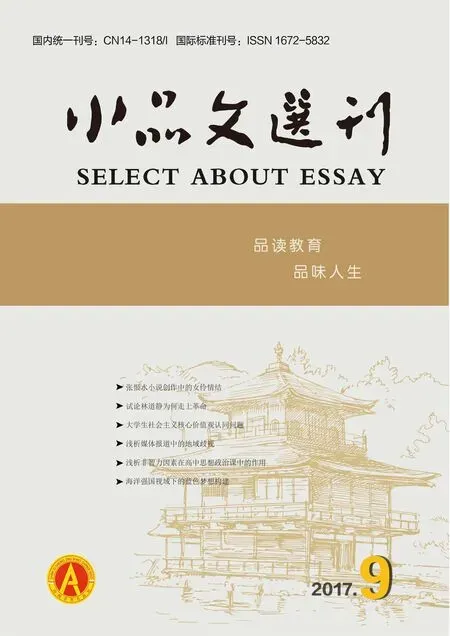《聊齋詩集》文獻綜述
屈廣博
(牡丹江師范學院文學院 黑龍江 牡丹江 157000)
《聊齋詩集》文獻綜述
屈廣博
(牡丹江師范學院文學院 黑龍江 牡丹江 157000)
蒲松齡在小說方面有著成績卓越,但是其詩文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忽視。其一生寫詩,內容涵蓋廣,包括農事詩、田園詩、寫實詩等。其文直追秦漢,而駢文較六朝之庾信不稍遜色;文以言志,詩以抒情。并在二十歲時與友人建立“呈中書社”。其詩在清時期與王士禎并稱,稱為“盛世變風”。
蒲松齡;山水;自悼意識
1 《聊齋詩集》版本研究
蒲松齡的《聊齋詩集》在后代已近失佚,蒲松齡大部分的詩文都保留在其他是人集子中。而第一個《聊齋文集》刊印于1935年第一次出版,現存有“清華本”“北大本”“馬本”等。但是很不幸“清華本”在1941年日軍轟炸西南聯合大學的圖書館是焚毀,“但羅爾剛尊胡適之囑抄錄的《聊齋遺集》本《三種目錄對照表》(中華書局的石鈔本,以及清華大學的藏鈔本,淄川馬立勛藏鈔本三種《聊齋全集》)和《詩集一》、《詩集二》使《聊齋詩集》“清華本”是可以復原的”[1]曾對清華本嘗試過復原。《聊齋詩集》(上海世紀書局出版原為《聊齋全集》,取其中二冊)原本是早期蒲松齡研究學者路大荒編著,根據其20歲時舉辦“呈中書社”到去世,根據胡適《辨偽舉例——蒲松齡的生年考》中“其中有《文集》四冊,《詩集》兩冊”。故可知“清華本”《詩集》一共兩冊。另北大圖書館《聊齋全集》毛筆豎鈔,共十冊(已失佚一冊)其中記錄“詩集一”左側有文:“詩集以馬本為抄本,并與清華本校之”而“詩集二”則標有“此集為‘清華本’獨有”。可知“北大本”是“馬本”和“清華本”的合集,并獨有“馬本”詩,而事實上隨著近代學者的研究,以及在20世紀80年代蒲松齡的軼文不斷出現,又新發現蒲松齡的詩近千首,故在二十世紀有新的學者重新進行了編著如盛偉又再次對《聊齋詩集》進行了論述,對蒲松齡的詩進行了不同種類的分類,聊齋先生的思想作了更為全面的論述。
2 蒲松齡生平及思想研究
不可否認的是蒲松齡的一生是失落的一生,其父蒲槃也是一位落榜的舉人,不得以經商起家,所以小時候的蒲松齡過了一段錦衣玉食的生活,而蒲松齡也子承父業,參加科舉考試,前半段得到過“南施北宋”中的施閨章的賞識。但是自此以后再無建樹,而且在蒲松齡成年不就,其父去世,家產被親戚分割,家道沒落,并且在后期由于長期不中舉人,所以蒲松齡在這期間積累了長期的生活體驗。而這些特點在《聊齋志異》中已經體現了出來,趙蔚芝先生《聊齋詩集箋注》(山東大學出版.1996),百馀萬字,注釋蒲松齡詩全面細致于古典、今典皆有所發明,對于推動蒲松齡詩作的研究工作功不可沒。孫興恒先生的《聊齋先生遺集》中可以發現聊齋先生的思想了解聊齋先生思想的最好的著作。以及牛斯凱《從《聊齋志異》家族倫理看蒲松齡對傳統社會秩序的矛盾思想》(曲阜師范大學.2015)邊昭月《繼承與超越——論聊齋志異與老子》(山東師范大學.2015),以上這些著作全面剖析了蒲松齡的思想,以及描寫了蒲松齡在多個層面上的對不同人的描寫。
3 《聊齋詩集》藝術成就研究
從《聊齋志異》中我們可以發現蒲松齡的詩也種類繁多,包括鄉村田園詩、諷刺詩、記事詩。宋好音在《“盛世”變風蒲翁詩——論《聊齋詩集》中的農村題材詩》(學術交流上2004)主要探討過蒲松齡的詩種類,認為蒲松齡的“神韻詩”含蓄蘊藉、委婉沖淡。尤其是其在農民方面的詩,起反應社會現實的厚度,其純真感人的詩情以及渾樸勁建的風格,是以王世貞為代表的“盛世元音”的異響。嘉慶年間張鵬展在《聊齋詩集序》說蒲松齡:“當漁洋司、秋谷太守互以聲價相高時,乃守其門徑,無所亦無所附。”[2]《四庫全書總目》總目稱其為:“以清新俊逸之才,范山模水,唱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翁然應之。”[2]其中,時小珍《蒲松齡詩歌研究》(贛南師范學院.2012),從蒲松齡詩中的重點出發,例如:山水、諷喻、詠懷、贈答等,在這幾種不同的類型詩中分析;通過蒲松齡的身世背景與蒲松齡不同時期的詩結合起來,顧問蒲松齡的詩在這篇論文里被分為,青年時期、中年時期、以及晚年時期,三個階段進行分析和探討,并且還在詩中闡述了蒲松齡的詩人形象,從科舉洛拓、地方名士、農民情懷等等可以說是全方位的分析了蒲松齡在不同階段的生活場景。而王同書《醇美雅趣詩文妙品——蒲松齡詩作初論》,在前人的基礎上從美學方面分析蒲松齡的詩歌,也是第一個比較少見的真正的從詩的美學角度出發,探討了蒲松齡詩中的詩意、詩美。蒲松齡和王士禎為同時代人,而且相互之間有交流,其“神韻詩”與王士禎的“神韻說”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是二人因為身份背景和生活經歷的不同導致詩風有很大的不同,蒲松齡的詩因為反映了時代的尖銳矛盾,也可看做是時代的“盛世元音”的“變風”,分深刻的思想精髓。 “蒲松齡主張作品應該“真”[3]關于蒲松齡詩學觀念的論述有《蒲松齡的詩學觀》李瑞豪(蒲松齡研究.2007)等。
4 《聊齋詩集》影響研究
在《呈中社序》里:“謝家嘲風弄月,遂足為呈士之章程乎載?”[4]認為寫詩本不就利于科舉考試,更何況寫小說呢?蒲松齡的落魄直接的導致他直面人生的精神,在《藥重書》中說:“山村之中,不惟無處可以問醫,并無錢可以市藥。”[5]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蒲松齡的生活狀態,陶淵明以一篇《桃花源記》表明出自己不同流合污,隱于自然回歸自然的狀態,我們知道的是陶淵明在“隱居”和“出仕”的選擇中也十分的矛盾,這與蒲松齡在寫詩和科舉上的矛盾相似,而不同的是陶淵明教與我們是避世的觀念,而蒲松齡則是直面人生,所以才有了《聊齋志異》中的諷刺精神,但是只有是發揮出了蒲松齡真正的才華,《蒲松齡生平述論》邵海清(杭州大學學報.1989)中對蒲松齡的的生活精作了的論述,《<聊齋>敘男女,蒲翁自情深——從蒲松齡詩文看其愛情生活》李伯齊(蒲松齡研.1989)從愛情詩的方面讓我們了解了直面現實中的文人精神的內在實質,相比較《聊齋志異》的諷刺而言,蒲松齡的詩文中直面現實的精神更值得我們思考。
[1] 鄒宗良《清華大學《聊齋詩集》鈔本研究》(聊齋詩詞研究.2014)
[2] 高明閣《聊齋詩集所反映的作者的思想與生活》(聊齋詩詞研究.2014)
[3] 李瑞豪《蒲松齡的詩學觀》(蒲松齡研究.2007)
[4] 邵海清《蒲松齡生平述論》(杭州大學學報.1989)
[5] 李伯齊《<聊齋>敘男女,蒲翁自情深——從蒲松齡詩文看其愛情生活》(蒲松齡研.1989)
I207
:A
:1672-5832(2017)09-003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