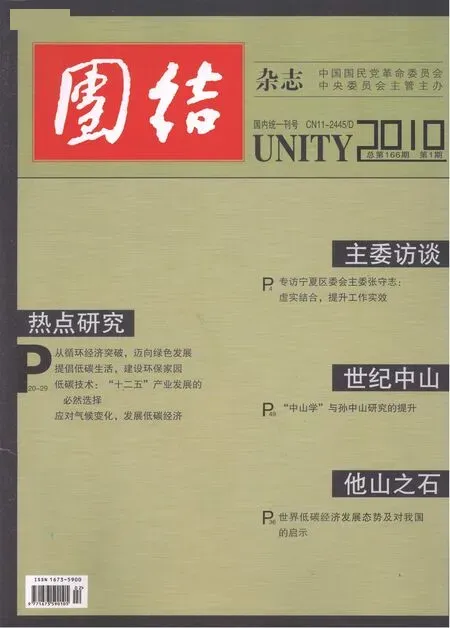低碳技術:“十二五”產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崔 成
低碳技術:“十二五”產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崔 成
氣候變化問題目前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博弈的焦點問題之一,大力發展低碳經濟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手段,而低碳經濟的競爭則主要反映在低碳技術的競爭和國際碳市場主導權的競爭兩個主要方面,其中低碳技術的競爭將直接決定未來氣候變化國際博弈的格局和走向。
發達國家意圖占領未來低碳技術制高點
舉世矚目的哥本哈根談判已經結束,但各國圍繞履約機制、量化減排目標、資金和技術機制、峰值時間以及長期目標等焦點問題的談判還遠未完成。目前的談判進程及各國的態度不僅反映出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對未來發展的環境空間的爭奪日趨激烈,也暴露出了發達國家在減排問題背后的主要利益考量。
美國是在談判中采取外松內緊政策的最典型國家,其所提的2020年比2005年減排17%的目標與公約及議定書要求相距甚遠,但在奧巴馬政府通過 《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等建立國內和國際碳市場,進一步加快低碳技術進步的目的則顯而易見。主要表現為:
其一,試圖通過投入巨資加快新能源、電動汽車、智能電網等低碳技術的開發利用,占領國際技術制高點并實現對國際低碳技術市場的控制權,同時壓中國減排為其低碳技術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
其二,試圖通過其目前的國際金融控制能力,逐步建立一個其主導下的類似于國際原油期貨市場那樣的國際碳期貨市場,取得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控制權。
其三,試圖通過其金融和技術優勢抵消中國在電動汽車、燃料電車等重大低碳技術應用所必須的稀土資源和稀有金屬資源的控制力,使中國繼續成為其重要的技術設備輸出市場和原料地。
其四,通過中國的巨大低碳市場,加速消化其新能源技術研發成本,為其相關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商業動力。
同時,很多美國經濟學者還將新能源等低碳技術視為IT技術之后的,目前唯一看得見的能夠拉動美國經濟下一個騰飛的新的經濟增長點。美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已經完全反映出了其等待技術突破,以時間換空間的高明策略,和以期永遠維持為歐盟及日本兩倍人均能源消費水平下的奢侈生活方式的戰略目標,其2030和2040年比2005年減排25%與40%,2050年減排80%的目標則更加充分地暴露了這一戰略意圖。
日本則緊隨其后,也采取了典型的外松內緊、以退為進策略,雖然提出了2020年比1990年減排25%的積極目標,但卻將美國等發達國家做出大幅減排承諾作為前提。在國內則一貫秉承技術立國、人才立國戰略,其2009年8月公布的 《日本2010年經濟產業政策重點》中低碳技術占據了主要篇幅,充分反映出了其在技術開發方面試圖通過產業政策引導,在太陽能、核能等新能源、智能電網、電動汽車及電池等低碳技術開發方面進一步加大投入與技術創新,維持其在低碳技術領域優勢地位的意圖十分明顯。
相對于美國而言,歐盟可以說是發達國家中應對氣候變化態度最為積極的集團,不但提出了2020年比 1990年減排20-30%的目標,還積極推動全球的減排行動。盡管歐盟國家內部在減排問題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是其整體戰略意圖是相對清晰的,即通過加快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進一步強化丹麥、德國、西班牙等國在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技術優勢,擴大未來全球低碳技術市場并占有更大的份額。通過全球低碳技術市場,加速消化其新能源技術研發成本,為其相關企業的發展提供新動力的意圖也十分明顯。另外,依托歐盟碳交易市場等手段,在加強低碳技術設備輸出的同時,通過碳金融來強化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向碳本位替代金本位的方向努力,使其碳金融優勢和低碳技術優勢能夠密切結合起來,以達到其通過應對氣候變化重新占據全球金融和技術制高點的戰略目標。
低碳技術是我國擺脫氣候變化國際困境的主要出路
發達國家在提出相對較低的減排目標的同時,無一例外地均在低碳技術開發方面投入了極大的熱情,不僅將低碳經濟看作是克服危機、創造新的需求和就業的重要手段,也將其看作是確立未來技術優勢地位的一次重要機遇,這些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制訂,以及 “十二五”期間產業發展政策均有重要借鑒意義。
我國2007年的與能源相關的CO2排放量是61億噸,與美國相當。如果美國能夠實現其《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中提出的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17%的目標,屆時其與能源相關的CO2排放總量將下降到50億噸左右。根據國際能源署(IEA)估計,即使我國在延續“十一五”節能減排措施的前提下,2020年與能源相關的CO2排放量也將達到96億噸 (相當于單位GDP的CO2排放強度下降40.6%),為美國的近兩倍,屆時我國與美國在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的地位將發生逆轉,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盡管我國提出的40-45%的國內自主減緩目標,來對壓發達國家承諾嚴格的減排目標,以及避免2020年談判中的出現絕對減排承諾比較有利,但仍然避免不了屆時替代美國成為國際社會重點攻擊目標的命運。而低碳技術已經成為我國未來在不明顯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擺脫國際困境的主要出路, “十二五”期間能否確立低碳技術創新體系,也將決定2020年后的長遠經濟發展空間。
低碳技術:我國 “十二五”產業和技術發展的必然選擇
對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的我國來說, “十二五”時期將不僅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機遇期,加強低碳技術創興已經成為我國 “十二五”期間產業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這是因為:
其一,根據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的具體特征, “十二五”期間將成為我國產業內部結構的優化調整的關鍵時期,新興技術產業將逐步取代傳統高耗能產業,成為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因此,必須改變依靠傳統產業的老路,在與發達國家差距相對較小的新興技術產業方面獲得長足發展才是唯一的出路,而低碳技術正是新興技術的一個主要發展方向,也是我國減緩日趨嚴重的能源、環境、溫室氣體排放控制等巨大壓力的重要途徑。
其二, “十二五”時期也是我國向以新能源為重要增長點的新增發電結構轉型的重大機遇期,而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技術都是低碳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低碳技術也是實現2020年新能源和核能占一次能源比重提高到15%目標的重要前提。
其三, “十二五”期間還是我國能源消費和節能重點領域逐步從工業部門轉向交通和建筑部門的關鍵轉折期,電動汽車和相關蓄電池的產業,各種建筑節能產業、零排放建筑產業等領域的低碳技術創新,不僅引領低碳消費生活方式和創造需求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是實現GDP的CO2排放強度下降40-45%目標的主要手段。
其四,依托 “十二五”這一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的一個重要轉折期,制訂好 “十二五”科技發展戰略和人才發展戰略,以及新興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規劃將具有格外重要的意義。并據此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和科技創新力度,特別是低碳技術等新型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帶動人才培養、拉動相關基礎研究和研發產業發展,為工業化后期技術創新能力的不斷增強打下良好的基礎。
其五,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低碳技術所創造新的需求和就業機會也成為克服金融危機的重要手段,基于新能源等低碳技術對需求和就業的拉動要高于傳統能源產業的現實,將低碳技術創新與克服金融危機、以及擴大內需等宏觀經濟政策相結合,使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其六,加快相關制度建設進程,將社會保障事業與經濟和產業發展、以及技術創新結合起來,創造新的需求和就業,為我國步入老齡化階段探索相關經驗。
總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的我國來說,“十二五”時期將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也是一個重要的機遇期,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中所透露出的諸多重要信息,對我國制訂 “十二五”經濟和產業發展規劃,以及相關技術發展規劃均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借鑒作用。
相關政策建議
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技術需求必須建立在低碳技術的自主創新上,主要依賴國外技術的時代將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轉折期的到來而逐步改變,如果我們能夠牢牢把握住 “十二五”期間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由傳統高耗能工業拉動為主向高技術拉動轉變的重大歷史機遇,將低碳技術創新作為我國未來高新技術發展的重要基礎,掌握碳金融和低碳技術主動權,從而擺脫成為繼美國之后國際壓力主要目標的被動地位,這些也應當成為我國 “十二五”期間必須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考慮的重大決策問題。為此,我們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其一,依托上海、北京等地的技術創新和研發優勢,建立大型、復合前瞻型國家級低碳技術研發創新基地,并與相應的融資交易體系相銜接,實現快速滾動式發展,占領未來全球低碳技術制高點,并為未來氣候變化領域到國際談判工作奠定技術基礎。在加大科技投入的同時,采取進一步向低碳技術傾斜的政策,保證低碳技術研發和創新的資金需求。
其二,建立國內的低碳技術自主創新體系,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提高相關領域技術開發和創新能力,在進一步加快清潔能源、節能、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傳統能源技術進步的同時,強化新型蓄電池、電動汽車、智能電網、低排放建筑等低碳技術創新的市場環境,并將節能、新能源、電動汽車、清潔燃料等低碳技術研發與納米等新材料技術有機整合,在做好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技術 (CCS)儲備的同時,力爭在太陽能、核能等關鍵低碳技術領域率先取得重大突破。
其三,嚴格限制稀土和主要稀有金屬資源的出口,保留對未來低碳技術應用方面的重要資源的戰略控制力。
其四,依托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目標的統計、監測和考核制度體系,通過出臺全國統一的交易標準和規范,在國內建立相應的地區間或重點企業間碳交易體系,在碳交易領域積累相應的經驗的同時,進一步營造有利于低碳技術發展的市場環境。
其五,加強低碳技術創新領域的國際合作,特別是中美應對氣候變化技術合作研究機制,在充分吸取國際先進技術成果的基礎上,加快推進我國低碳技術創新步伐;基于我國目前在全球金融市場不占優勢的現實,及2020-2030年將建成1-2個世界金融中心的發展潛力,應立足長遠來考慮碳交易問題,爭取通過談判影響全球碳交易市場的發展進程,形成對我較為有利的國際碳金融格局,并實現與低碳技術發展的良性互動。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能源所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民革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委員/責編 張海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