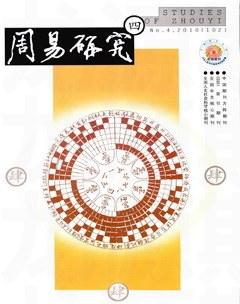試論來(lái)知德的像象觀與錯(cuò)綜說(shuō)
劉體勝
摘要:像象觀和錯(cuò)綜說(shuō)。是來(lái)氏易學(xué)中的兩大創(chuàng)見(jiàn)。來(lái)知德所謂的易象內(nèi)涵,包含“事理之彷佛近似”和“可以想像”兩個(gè)層面。這一像象觀,是對(duì)《系辭傳》以來(lái)的模寫(xiě)說(shuō)、特別是朱熹易象說(shuō)的一個(gè)重大發(fā)展和推進(jìn),其實(shí)質(zhì)是對(duì)易模寫(xiě)說(shuō)如何可能和如何建構(gòu)這一問(wèn)題所作的覃恩和論說(shuō)。錯(cuò),在形式上指的是爻性皆對(duì)整相反的兩個(gè)卦。綜的形式則有兩種:一足四正之卦在別卦中或上或下的變化;二是四隅之卦或一別卦與其顛倒后所得之卦之間的關(guān)系。而綜的第一種形式,似從來(lái)有學(xué)者注意到和發(fā)明過(guò)。錯(cuò)、綜雖形式各異,但二者得以確立的形上學(xué)理?yè)?jù)卻都是陰陽(yáng)之理:錯(cuò)實(shí)質(zhì)上是陰陽(yáng)的相互對(duì)待,綜則是陰陽(yáng)的上下流行。在來(lái)氏易學(xué)中,錯(cuò)綜不僅是取象條例,而且足卦序的內(nèi)在建構(gòu)原則。來(lái)知德的像象觀和錯(cuò)綜說(shuō),在易學(xué)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關(guān)鍵詞:來(lái)知德;像象;錯(cuò)綜
中圖分類號(hào):B248.99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3-3882(2010)04-0048-10
來(lái)知德(1525-604),字矣鮮,號(hào)瞿塘,夔州梁山人(今四川梁平縣人),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和易學(xué)家。《明史儒林傳》和《明儒學(xué)案·諸儒學(xué)案下》皆有其傳,《經(jīng)義考》、《續(xù)文獻(xiàn)通考》、《四川通志》、《讀禮通考》和《大清一統(tǒng)志》等書(shū)亦有相關(guān)述略。來(lái)知德的思想著作,主要有《人圣功夫字義》、《格物諸圖》、《大學(xué)古本》、《理學(xué)辨疑》、《四省錄》等。而“用功尤篤”、遠(yuǎn)客深山數(shù)十年以求易,凡二十九年而后成書(shū)的《周易集注》一書(shū),更是集中體現(xiàn)其易學(xué)思想、一舉奠定其在易學(xué)史上之重要地位的扛鼎之作,歷來(lái)評(píng)價(jià)較高。
來(lái)氏《易注》輯采、涵化了兩漢宋明多家易說(shuō),但又自成思想體系,頗注重象數(shù)和義理的融會(huì)貫通。據(jù)《易注·自序》中瞿塘自言數(shù)年苦心孤詣以發(fā)明易象諸文和來(lái)氏易在易學(xué)史上的影響觀之,瞿塘的一大學(xué)術(shù)貢獻(xiàn)是其易象學(xué)。而其中,竊以為又以像象觀和錯(cuò)綜說(shuō)最能體現(xiàn)來(lái)氏易的創(chuàng)見(jiàn)和發(fā)明。本文以《周易集注》為主要理?yè)?jù),試對(duì)來(lái)知德的像象觀和錯(cuò)綜說(shuō)作一探繹,錯(cuò)謬之處敬請(qǐng)方家教正。
一、“近似”和“想像”——來(lái)氏易的像象觀
《易》是一種特殊的符號(hào)系統(tǒng),由卦爻符號(hào)和文辭共同組成其結(jié)構(gòu)。而據(jù)《系辭傳》“圣人設(shè)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的說(shuō)法,《易》當(dāng)先有卦畫(huà)及易象而后才有卦爻辭。由是言之,易象更為根本,乃易之基礎(chǔ),此即所謂“易者,象也”之意。
正是易象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價(jià)值,故后世多有由象而解易者。據(jù)《易傳》和《左》《國(guó)》等傳世文獻(xiàn)所載,可知這至遲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即已有之。而對(duì)易象的探研至兩漢尤為興盛,諸家蜂起,一時(shí)蔚為大觀。從易象這個(gè)層面來(lái)說(shuō),漢易不但拓寬了《說(shuō)卦傳》中所設(shè)立的易象范圍(如“九家逸象”等),而且發(fā)明了諸多影響深遠(yuǎn)的取象條例。但漢代象學(xué)亦因執(zhí)泥于追求象辭嚴(yán)格相應(yīng)而日趨“繁雜瑣屈”(王夫之語(yǔ)),甚至相互矛盾,故日漸為后世所疑棄。至王弼奮起,振臂一呼,頓成百應(yīng)之勢(shì),摧枯拉朽,一掃漢象。自此至宋,象學(xué)一蹶不振,其間諸家注《易》多忽略、少言或不言象而徑言義理者。至朱子糾偏,始稍有起色,言象者才日漸眾多。
來(lái)瞿塘遠(yuǎn)紹由《易傳》開(kāi)顯、經(jīng)漢唐昌興的象學(xué)傳統(tǒng),近承朱子所創(chuàng)始的象數(shù)、義理融通一體的治易之理路,在汲取前人研討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自己具有創(chuàng)見(jiàn)性的像象觀。
(一)“事、理之彷佛近似”和“可以想像”——瞿塘論易象內(nèi)涵
首先,瞿塘認(rèn)為:易有天地自然之易、在人之易和《易》書(shū)之易三種。而《易》書(shū)之易,正源自圣人對(duì)天地自然之易的模寫(xiě):
蓋未畫(huà)易之前,一部易經(jīng)已列于兩間。故天尊地卑,未有易卦之乾坤而乾坤已定矣;卑高以陳,
未有易卦之貴賤而貴賤已位矣;動(dòng)靜有常,未有易卦之剛?cè)岫鴦側(cè)嵋褦嘁樱环揭灶惥郏镆匀悍郑?/p>
有易卦之吉兇而吉兇已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未有易卦之變化而變化已見(jiàn)矣。圣人之易,不過(guò)
模寫(xiě)其象數(shù)而已,非有心安排也。(《周易集注》(四庫(kù)全書(shū)本),北京:中國(guó)書(shū)店,第391-392頁(yè)。)這里,瞿塘實(shí)際上因襲了《系辭傳》以來(lái)的模寫(xiě)說(shuō)(特別是薛敬軒和蔡虛齋的相關(guān)說(shuō)法),認(rèn)為畫(huà)前之易實(shí)為易書(shū)之本源,即在圣人畫(huà)易之前,世界實(shí)已普遍存在尊卑貴賤、動(dòng)靜吉兇、運(yùn)動(dòng)變化等諸種自然的象數(shù),“天地之間,業(yè)已陳列一部活脫脫的易經(jīng)”。而圣人所作之易,不過(guò)是對(duì)這一部“活脫脫的易經(jīng)”的模寫(xiě)罷了。因此,《易》書(shū)中的象數(shù)廣悉該備而條理井然,并非圣人有心安排之,而是自然而然。
在形式結(jié)構(gòu)上,《易》書(shū)包括辭、變、象、占四個(gè)層面。瞿塘認(rèn)為,《易》書(shū)的這四個(gè)層面皆為圣人模寫(xiě)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相對(duì)應(yīng)的“四象”而來(lái):四象者,天生神物之象、天地變化之象、垂象吉兇之象、河圖洛書(shū)之象也。……故易有占,非圣人自立其占也,天生神物,有自然之占,圣人則之以立其占;易有變,非圣人自立其變也,天地變化,有自然之變,圣人效之以立在其變;易有象,非圣人自立其象也,天垂象見(jiàn)吉兇,有自然之象,圣人象之以立其象;易有辭,非圣人自立其辭也,河出圖、洛出書(shū),有自然之文章,圣人則之以立其辭。(《周易集注》,第419頁(yè))
《易》書(shū)之易既然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自然之易的模寫(xiě),那么,現(xiàn)在的問(wèn)題是:“天地萬(wàn)物之形象,千態(tài)萬(wàn)狀,至多而難見(jiàn)”,(《周易集注·系辭傳》,第423頁(yè))而易書(shū)不過(guò)僅具有限的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已,易象又如何能“窮究而形容之”(《周易集注·系辭傳》,第423頁(yè))、何以彌綸天地呢?
對(duì)這個(gè)問(wèn)題的回答,便涉及到瞿塘對(duì)易象內(nèi)涵的認(rèn)知和界定。
《易》所言之象,大體上分為三類。一是《易傳》所指的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可見(jiàn)可感之“象”(此即“見(jiàn)乃謂之象”之意),如“天垂象”之類。其二是陰陽(yáng)符號(hào)及八卦所表征之“象”,這在《說(shuō)卦傳》有集中論說(shuō)。其三是卦爻辭所言之象。前兩類,無(wú)論是象數(shù)派還是義理派,都是沒(méi)有多少爭(zhēng)議的。而對(duì)卦爻辭所言之象的看法和解說(shuō),則歷來(lái)是兩派的爭(zhēng)論焦點(diǎn)所在。本文所探討的來(lái)知德關(guān)于易象意涵的界定,主要在第三種意義上說(shuō)的。為行文方便,后文所言之象基本上都是此意義的易象。
易學(xué)家對(duì)象的關(guān)注和論說(shuō),很早就開(kāi)始了。而《系辭傳》中的相關(guān)論說(shuō),則成為后世研易者界定和闡揚(yáng)易象的重要基礎(chǔ)。如《系辭傳》云:“象也者,像也”,又云:“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瞿塘對(duì)易象內(nèi)涵的界定,即立足于《系辭傳》這些觀點(diǎn)之上的。瞿塘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日像者,乃事、理之仿佛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實(shí)事也,非真有實(shí)理也。若以事論,金豈可為車?玉豈可為鉉?若以理論,虎尾豈可履?左腹豈可入?(《周易集注·自序》)
筆者曾受流俗的影響,在碩士論文中誤認(rèn)為瞿塘此所言之象,其內(nèi)涵即是“象征”。而今觀之,此解實(shí)至謬。象征,乃以一具體的事物來(lái)表現(xiàn)某種抽象或神秘的意義,如火炬之象征光明、十字架之于基督之類。所以,“象征意味著感性現(xiàn)象與超感性意義的合一”,其實(shí)質(zhì)是具體與抽象意義、形象和概念的統(tǒng)一。而從瞿塘所舉之例觀之,潛龍、金車、玉鉉諸象雖是具體之物而可為象征,但其皆無(wú)與某種抽象意義聯(lián)系在一起的例子,其所指都是具體的事物或狀態(tài)。此外,作為象征的具體事物與其所表達(dá)的抽象意
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常常是確定的。如火炬之與光明。而在瞿塘那里,象并不如此。如“潛龍”就可表達(dá)人的多種狀態(tài)。總而言之,以瞿塘之“象”為“象征”之象,是錯(cuò)誤的。
由所引“仿佛近似”、“可以想像”和“非真有實(shí)事,非真有實(shí)理”諸文可見(jiàn),瞿塘認(rèn)為,《易》中卦爻辭所言之象,皆非“實(shí)指”、“非真有實(shí)事,非真有實(shí)理”,故易象并不實(shí)指現(xiàn)實(shí)的事物或狀態(tài),也不指向一個(gè)實(shí)際的道理。如“金車”、“玉鉉”、“履虎尾”、“人左腹”等例。
“金車”、“玉鉉”、“履虎尾”、“入左腹”分別出自《困卦》九四爻辭、《鼎卦》上九爻辭、《履卦》彖辭(及六三、九四爻辭)和《明夷》六四爻辭。《困卦》九四日:“來(lái)徐徐,困于金車。”瞿塘注曰:“金車指九二,坎車象,乾金當(dāng)中,金車之象也。”(《周易集注》,第319頁(yè))根據(jù)來(lái)氏《八卦正位圖,正位不可移動(dòng)》一文所論,坎卦中間一陽(yáng)爻為乾。《困卦》之貞卦為坎,所以九二有乾金之象;而坎象為車,所以來(lái)氏日金車指九二。但“金豈可為車”?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并無(wú)實(shí)存之“金車”之物。因此,所謂“金車”并非對(duì)現(xiàn)實(shí)之物的直接描摹,非實(shí)指,而是“近似之象”。乾陽(yáng)明純粹、剛健中正,有君子之象。瞿塘釋此卦九二日:“九二以剛中之德,當(dāng)困之時(shí),甘貧以守中德。”(《周易集注》,第318頁(yè))因此,所謂“金車”之象非實(shí)指現(xiàn)實(shí)中的“金車”之物,而是意指有剛中之德、當(dāng)困窮之時(shí)仍能甘貧以守之的君子。其他所舉之例皆仿此,如所謂玉鉉實(shí)指“有玉鉉之德”之人(《周易集注》,第335頁(yè))、“履虎尾有“履帝位之象”,(《周易集注》,第173頁(yè))等等,茲不具述。
所以,瞿塘認(rèn)為,《周易》雖然源自圣人對(duì)現(xiàn)實(shí)自然之易的模寫(xiě),易象系由對(duì)自然之象的擬法而成(“圣人象之以立其象”),但易象的這種模寫(xiě)和擬法,并非是一一對(duì)應(yīng)式的直接反映——“非真有實(shí)事,非真有實(shí)理”,易象和其所意指的現(xiàn)實(shí)事物或狀態(tài)、道理之間只存在一種“仿佛相似”(“像”)的關(guān)系。如此,則要求研易者或占卜者在觀象玩占的過(guò)程中,必須運(yùn)用知性的“想像”,把易象加以靈活轉(zhuǎn)換,此即所謂“可以想像者也”:如占得潛龍之象,在天子則當(dāng)傳位,在公卿則當(dāng)退休,在士子則當(dāng)精修,在賢人則當(dāng)隱逸,在商賈則當(dāng)待價(jià),在戰(zhàn)陣則當(dāng)左次,在女子則當(dāng)愆期,萬(wàn)事萬(wàn)物莫不皆然。(《周易集注》,第63頁(yè))綜上所述可見(jiàn),瞿塘所論之易象的內(nèi)涵包括“近似、像似”和“想像”兩個(gè)層面。這種意義的易象,我們可簡(jiǎn)稱為“像象”。瞿塘形象地把此“像象”比擬成“鏡子”:“故象猶鏡也,有鏡則萬(wàn)物畢照”。(《周易集注。自序》)世界萬(wàn)物雖紛繁復(fù)雜、千變?nèi)f化,但此種似鏡的像象皆可含括而照之。故在瞿塘看來(lái),易象實(shí)是易經(jīng)之所以能把世界萬(wàn)有及其變化反映、含括進(jìn)來(lái)的關(guān)鍵:“立象則大而天地,小而萬(wàn)物,精及無(wú)形,粗及有象,悉包括于其中矣”。(《周易集注》,第420-421頁(yè))天地萬(wàn)物及其變化既然被含括進(jìn)來(lái),那其背后所隱藏之“理”當(dāng)然亦通過(guò)易象而得以反映和寓藏:“有象,則大小、遠(yuǎn)近、精粗,千蹊萬(wàn)徑之理,咸寓乎其中”。(《周易集注‘自序》)與此相反,若把易象作實(shí)指,瞿塘則以為不知象,“若不知象,一爻止一事,則三百八十西爻止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矣,何以彌綸天地”?顯然,這實(shí)際上是瞿塘對(duì)史學(xué)宗解易理路之弊的批評(píng)。故瞿塘又云:“無(wú)象,則所言者止一理而已,何以彌綸?”(《周易集注,自序》)
這樣,瞿塘就回答了易之所以能對(duì)“千態(tài)萬(wàn)狀”之事物能“窮究而形容之”,“彌綸天地之道,,而“與天地準(zhǔn)”這一問(wèn)題。
既然易象是“窮究而形容”萬(wàn)物、“彌綸天地之道”的基礎(chǔ),則易象對(duì)《易經(jīng)》來(lái)說(shuō)就特別重要。瞿塘甚至宣稱:“不知其象,易不注可也”。(《周易集注·自序》)瞿塘進(jìn)而指出,易象的這一特點(diǎn),也決定了《易經(jīng)》和儒家其他諸經(jīng)在性質(zhì)上的差異:《易》不似別經(jīng),不可為典要。(《周易集注·乾》,第63頁(yè))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孔子之言也。曰像者,乃事、理之仿佛近似,可以想像者也,非真有實(shí)事也,非真有實(shí)理也。……易與諸經(jīng)不同者,全在于此也。(《周易集注,自序》)
瞿塘對(duì)易象的此種認(rèn)知和界定,在其注《易》的實(shí)踐中得以貫徹并有諸多體現(xiàn)。如其注《屯》之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無(wú)不利”云:本爻變,中爻成巽,則為長(zhǎng)女,震為長(zhǎng)男,婚媾之象也。非真婚媾也,求賢以濟(jì)難,有此象也。舊說(shuō)陰無(wú)求陽(yáng)之理,可謂不知象也。(《周易集注》,第148頁(yè))《屯》之六四爻辭言“婚媾”,瞿塘認(rèn)為,爻辭所言的“婚媾”之象于此并非實(shí)指,而實(shí)際上講的是“求賢以濟(jì)難”之事,并由此批評(píng)舊說(shuō)為謬。其他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茲不具舉。
(二)像象觀在易學(xué)史上的意義
竊以為,來(lái)氏對(duì)易象內(nèi)涵的此種認(rèn)知和界定,在易學(xué)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眾所周知,首先對(duì)易象作出覃思并展開(kāi)集中論釋的是《系辭傳》。其后歷代易學(xué)家大多以此為基據(jù)展開(kāi)相關(guān)論說(shuō)。這些論說(shuō),大體上可依據(jù)象理關(guān)系而劃分為義理和象數(shù)兩派觀點(diǎn)。朱熹對(duì)此曾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評(píng)論:《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茍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lái),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疏略而無(wú)據(jù)。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guò)也。(參見(jiàn)李光地《周易折中,綱領(lǐng)二》)
朱熹認(rèn)為,《易》所取之象必有其由來(lái)和體例;另外,易象也發(fā)揮著重要的功用。由此兩點(diǎn)言之,易象“非茍為寓言也”。但是,兩漢的象數(shù)學(xué)和魏王弼以來(lái)的義理派對(duì)此卻各執(zhí)其一端,皆不全面。具體而言之,漢儒總是力圖窮究易象之所從來(lái)而于義理有所忽略,“上無(wú)所關(guān)于義理之本原,下無(wú)所資于人事之訓(xùn)誡”,陷于“案文責(zé)卦”(如乾馬坤牛之類)而不拔,于是雖創(chuàng)出了諸多取象體例,但其大多是附會(huì)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shì)”的解說(shuō),故終致滯泥難通。而另一端,以王弼和《程傳》為代表的義理派卻從掃除漢象的思想運(yùn)動(dòng)中又走向兩漢象學(xué)的反面,或主張易象不過(guò)是為“顯意”而假設(shè)的筌蹄之物,或認(rèn)為易象僅類似于“《詩(shī)》之比興,孟子之譬喻”(《周易折中·綱領(lǐng)二》)而已,故于易象皆發(fā)明不夠,“疏略而無(wú)據(jù)”。因?yàn)閮膳山杂衅涫В手熳又鲝垼瑢?duì)待易象一方面“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從來(lái)”(只因“今不復(fù)考”),但另一方面“亦不可直謂假設(shè)而遽欲忘之”(《周易折中·綱領(lǐng)二》)。
朱熹之所以于此力破王弼、《程傳》之論而堅(jiān)決主張易象的重要性,這實(shí)際上基于其對(duì)《易經(jīng)》一書(shū)性質(zhì)的判斷——《易》本卜筮之書(shū)。而易象與此判斷又有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周易折中·乾初九·集說(shuō)》)所以,朱熹認(rèn)為,要探究易象,必須基于卜筮。
在卜筮活動(dòng)中,占卦者須因據(jù)并應(yīng)用所占得的卦爻辭所言之象來(lái)擬度自己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以決其行為舉動(dòng)之可否,以斷吉兇悔吝。如此,則在實(shí)際的卜筮活動(dòng)中,便會(huì)存在任何一個(gè)卦爻辭都可能要面臨“賢愚皆得其用”的要求。這就意味著,任何一個(gè)易象都要意指眾多占問(wèn)者的諸多現(xiàn)實(shí)情境。所以,易象不可能是某一個(gè)確定的實(shí)指。故朱熹指出,易雖是有定象,但象皆為“虛說(shuō)此個(gè)地頭”,“初不黏著物上”。正是因?yàn)槿绱耍捉?jīng)的“一卦一爻,足以包無(wú)窮之事”,“如所謂‘潛龍,只是有個(gè)‘潛龍之象,自
天子至于庶人,看甚人來(lái)都使得”。朱子由此對(duì)易象有一個(gè)基本的判定:易象,“須知得他是假托說(shuō),是包含說(shuō)。假托,謂不惹著那事。包含,是說(shuō)個(gè)影像在這里,無(wú)所不包”(《周易折中·綱領(lǐng)二》)。所以,朱子認(rèn)為,易象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假托”的“影像”。而這個(gè)影像,可意指萬(wàn)有,故“無(wú)所不包”。
此外,在《周易本義》中,朱子于《系辭》“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一句文下亦曾明確地注解說(shuō):“易卦之形,理之似也。”這與來(lái)知德所謂的易象乃“理之彷佛近似”之意頗為相近。
故瞿塘的“像象”之說(shuō),實(shí)源自朱熹但又有發(fā)展。瞿塘和朱熹在易象可以窮究而形容萬(wàn)物這一基本判斷上是一致的,但二人對(duì)易象內(nèi)涵的界定則有所差異。朱熹雖然反對(duì)把易象看成是“假設(shè)”之物,但卻又說(shuō)易象是“假托”。朱熹之言前后是否有矛盾,茲不論。而可以肯定的是,朱子所謂“不惹著那事”的理論立場(chǎng)則是瞿塘贊同的。其次,朱子所謂的“影像”和瞿塘所謂“像象”還是有別的。影像,實(shí)質(zhì)上仍然指向某一個(gè)實(shí)存的事物。而這便與朱子的“無(wú)所不包”之言是有內(nèi)在矛盾的。就“無(wú)所不包”的理論要求來(lái)說(shuō),瞿塘的“近似”說(shuō)似更優(yōu)。再者,瞿塘利用漢字多義的特點(diǎn),認(rèn)為易象的內(nèi)涵不僅有“像似”之義,還包含“想像”的義涵,此說(shuō)頗有新意。此說(shuō)把占卜者的主體因素納入易象中,就卜筮的角度來(lái)說(shuō),更貼合占筮活動(dòng)的實(shí)際。這是來(lái)知德對(duì)朱熹易象說(shuō)的發(fā)展。
二、“若無(wú)錯(cuò)綜,不成《易》矣”——來(lái)氏易的錯(cuò)綜說(shuō)
瞿塘不但對(duì)易象內(nèi)涵進(jìn)行了詳細(xì)地論說(shuō),而且通過(guò)遠(yuǎn)客深山、多年摸索易象的苦心研究及對(duì)前人相關(guān)成果的反思,創(chuàng)立了自己的一套取象條例。通過(guò)這些取象條例,易象得以蓬勃展開(kāi),其在易經(jīng)中的重要性和價(jià)值亦益加突顯出來(lái)。
瞿塘對(duì)立象條例的論釋,主要集中在他的《易經(jīng)字義》一文中。其言曰:《朱子語(yǔ)錄》云:卦要看得親切,須是兼象看,但象失傳了。殊不知圣人立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huà)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cuò)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爻變之象,有占中之象。(《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象》,第112頁(yè))
瞿塘認(rèn)為,朱子說(shuō)“象失傳了”那是誤解,是因?yàn)閷?duì)圣人立象條例的不知而導(dǎo)致的。而圣人所立的這些條例,包括因卦情而立象者、因卦畫(huà)而立象者、因大象而立象者、因中爻而立象者、因錯(cuò)卦而立象者、因綜卦而立象者、因爻變而立象者、因占而立象者等數(shù)種。所謂因卦情而立象者、因卦畫(huà)而立象者、因大象而立象者、因占而立象者諸條例,前儒實(shí)多已言之。所以,來(lái)氏于此并無(wú)太多新意。愚以為,在瞿塘所列的取象條例中,以錯(cuò)、綜、變、中爻等四種最為重要,而其中又以錯(cuò)和綜最為瞿塘所注重和強(qiáng)調(diào),在釋注《易經(jīng)》時(shí)應(yīng)用的亦最為廣泛,二者寓藏著瞿塘的諸多新見(jiàn)。故來(lái)氏曾明確地說(shuō):“若無(wú)錯(cuò)綜,不成《易》矣。”《周易集注》,第44頁(yè))在《易經(jīng)字義》中,瞿塘曾特別選出并詳加論釋。
(一)釋“錯(cuò)”
關(guān)于“錯(cuò)”,瞿塘釋曰:錯(cuò)者,陰與陽(yáng)相對(duì)也。父與母錯(cuò),長(zhǎng)男與長(zhǎng)女錯(cuò),中男與中女錯(cuò),少男與少女錯(cuò)。八卦相錯(cuò),六十四卦不外此錯(cuò)也。(《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3頁(yè))可見(jiàn),所謂“錯(cuò)”,指的就是陰陽(yáng)的相互對(duì)待,如父與母,長(zhǎng)男與長(zhǎng)女,中男與中女,少男與少女等。這是“錯(cuò)”的內(nèi)涵。具體到易經(jīng)中,則指的是兩個(gè)經(jīng)卦或別卦的爻性皆對(duì)整相反,如乾坤、坎離等。既有錯(cuò)卦,則錯(cuò)之象自然生成,寓于錯(cuò)之中:如乾錯(cuò)坤,乾為馬,坤即利牝馬之貞。履卦兌錯(cuò)艮,艮為虎,文王即以虎言之;革卦上體乃兌,周公九五爻亦以虎言之。又睽卦上九純用錯(cuò)卦,師卦王三錫命,純用天火同人之錯(cuò),皆其證也。(《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3頁(yè))按照《說(shuō)卦傳》,乾象為馬,而坤與乾相錯(cuò),故坤之錯(cuò)象為牝馬,所以《坤·彖辭》有“利牝馬之貞”之語(yǔ)。履卦之貞卦為兌,兌與艮相錯(cuò),而艮象為虎,所以《履·彖辭》日“履虎尾”。革卦外卦為兌,所以,此卦九五爻辭亦日“大人虎變”。此皆為錯(cuò)象之證。余卦仿此。
錯(cuò)之象還體現(xiàn)在一卦的中爻之錯(cuò)卦上:“又有以中爻之錯(cuò)言者。如小畜言云,因中爻離錯(cuò)坎故也;六四言血者,坎為血也;言惕者,坎為加尤也。”(《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3頁(yè))瞿塘所言中爻,在形式上實(shí)與互體類同。小畜卦中爻為離,而離錯(cuò)坎,又坎象為云,所以《小畜·彖辭》有“密云”之說(shuō)。本卦六四爻辭言血、言惕皆本于中爻錯(cuò)象坎。
瞿塘認(rèn)為,“錯(cuò)”和下文所言的“綜”皆本自伏羲、文王觀物設(shè)卦時(shí)的創(chuàng)立,其形而上的理?yè)?jù)在陰陽(yáng)。這兩則條例,實(shí)際上已隱藏于文王所定之序卦和孔子所作之雜卦中,而朱熹說(shuō)“象失傳不過(guò)是未能察知此罷了:"3L恐后學(xué)以《序卦》為定理,不知其中有錯(cuò)有綜、有此二體,故雜亂其卦,前者居于后,后者居于前,止將二體兩卦有錯(cuò)有綜者下釋其意。……使非有此《雜卦》,象必失其傳矣。”(《周易集注,雜卦傳》,第478頁(yè))
(二)釋“綜”
關(guān)于“綜”,瞿塘認(rèn)為:綜字之義,即織布帛之綜,或上或下,顛之倒之者也。如乾坤坎離四正之卦,則或上或下;巽兌艮震四隅之卦,則巽即為兌,艮即為震;其卦名則不同,如屯蒙相綜,在屯則為雷,在蒙則為山是也。(《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3頁(yè))
由上引文可見(jiàn),所謂“綜”,即是指陰陽(yáng)的上下、顛倒。具體到易卦中,綜則有兩種具體形式:一是四正之卦在別卦中位置上的或上或下的變化;二是四隅之卦或一別卦與其顛倒后所得之卦之間的關(guān)系。而就筆者目前所見(jiàn),似乎學(xué)者都看到了綜的第二個(gè)形式,但對(duì)綜的前一種形式并未注意到和發(fā)現(xiàn)過(guò)。
按照瞿塘之說(shuō),乾坤坎離四卦,即按照伏羲八卦圖所定的四正卦顛倒之后還是其本身,并不變,但此四卦在別卦中的位置可上可下。瞿塘認(rèn)為,這也是綜。巽兌艮震四隅之卦,顛倒之后亦形成“綜的關(guān)系。如巽顛倒之后得到的卦為兌,同樣,艮顛倒之后所得到的卦為震。反之亦然,兩兩相綜。從八卦擴(kuò)展到六十四卦,其例亦同,如屯蒙兩卦即是如此。但相對(duì)而言,這較為復(fù)雜,可參見(jiàn)來(lái)氏所著《伏羲文王錯(cuò)綜圖》諸篇,茲不具述。
瞿塘把“綜”又分為正綜和雜綜兩種:如乾初爻變姤,坤逆行、五爻變夬與始相綜。所以始綜央,屯綜大壯,否綜泰,觀綜臨,剝綜復(fù),所謂乾坤之正綜也。八卦通是初與五綜,二與四綜,三與三綜。雖一定之?dāng)?shù),不容安排。……若乾坤所屬尾兩卦,晉大有、需比之卦,類術(shù)家所謂游魂、歸魂,出于乾坤之外者,非乾坤五爻之正變,故謂之雜綜。(《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4頁(yè))
所謂正綜、雜綜,詳見(jiàn)來(lái)氏所作《八卦所屬相綜圖》,茲不具引。正綜,如果參照京房八宮卦圖便可以看得很清楚:兩兩相錯(cuò)的兩個(gè)本宮卦所屬的前五個(gè)世卦分別按照初與五綜、二與四綜、三與三綜的次序相互對(duì)應(yīng),是為正綜;而八個(gè)本宮卦所屬的游魂、歸魂卦亦按照一定次序相互對(duì)應(yīng),是為雜綜。而雜綜的規(guī)則是:四正與四正所屬相綜、四隅與四隅所屬相綜。如乾坤所屬之游魂、歸魂卦即分別與坎離所屬游魂、歸魂卦一一相應(yīng),同樣,艮巽、震兌四隅之卦所屬之游魂、歸魂亦分別一一相應(yīng)。如乾之晉雜綜坎之明夷,艮之中孚雜綜兌之小過(guò)之類。“綜”之條例既立,則易象即寓于“綜”之中:
八卦既相綜,所以象即寓于綜之中。如噬嗑利用獄,賁乃相綜之卦,亦以獄言之;旅豐二卦,亦以獄言之,皆以其相綜也。(《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4頁(yè))
《噬嗑》之彖辭曰“利用獄”,而《賁》之大象傳亦日“折獄”;二卦都以“獄”言之,這是因?yàn)槎弑緸橄嗑C之卦。旅豐二卦仿此。
綜上所述可見(jiàn),綜的一個(gè)形式是指一卦與其顛倒后所得之卦之間的關(guān)系。所以,嚴(yán)格說(shuō)來(lái),一別卦的初爻即對(duì)應(yīng)另一別卦的上爻、二爻對(duì)應(yīng)五爻、三爻對(duì)應(yīng)四爻等。如此,則從理論上說(shuō),構(gòu)成綜關(guān)系的任何兩別卦之爻象和爻辭之間應(yīng)有十分緊密的聯(lián)系。而在《易》中,確實(shí)有這方面的例子。誠(chéng)如瞿塘所言:“如損益相綜,損之六五即益之六二,特倒轉(zhuǎn)耳,故其象皆十朋之龜;夫姤相綜,夫之九四即姤之九三,故其象皆臀無(wú)膚。綜卦之妙如此,非山中研究三十年,安能知之?”(《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3-114頁(yè))這確實(shí)是解釋易中某兩卦之爻辭相類甚或相同的一個(gè)重要的條例。從經(jīng)文詮釋的角度言之,瞿塘的說(shuō)法是值得肯定的。
朱熹等宋明研易者頗推崇和喜用漢易的“卦變”條例,而瞿塘卻極力反對(duì)之:“數(shù)年而悟卦變之非。”(《周易集注·白序》)瞿塘之所以反對(duì)卦變,其中原因正是瞿塘對(duì)“綜”的發(fā)明和應(yīng)用:有以上六下初而綜者,則自外而為主于內(nèi)是也;有以二五而綜者,柔得中而上行是也。(《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4頁(yè))在《彖辭》及《彖傳》中有不少含“剛?cè)醿?nèi)外”、“上下”、“往來(lái)”等文辭,故有人認(rèn)為卦變思想即發(fā)軔于此,而一些易學(xué)家則反對(duì)此論。所以,關(guān)于卦變,歷來(lái)的注解就存有爭(zhēng)議。而瞿塘認(rèn)為,《彖傳》中的這些文辭并非源于卦變而來(lái),而實(shí)為因據(jù)綜之條例而得出:如一卦的上六是其綜卦的初爻,則對(duì)其綜卦而言,這便是“自外而為主于內(nèi)”;而如果是以二五為綜,則即有“柔得中而上行”。如瞿塘注釋《訟·彖傳》之“剛來(lái)而得中”即用“綜”條例:“剛來(lái)得中者,需訟相綜,需上卦之坎來(lái)居訟之下卦,九二得中也。前儒不知序卦、雜卦,所以依虞翻以為卦變。”(《周易集注·訟·彖傳》,第157頁(yè))
前文業(yè)已言之,瞿塘把錯(cuò)、綜立象條例溯源至伏羲及文王之序卦和孔子之雜卦。基于錯(cuò)、綜在自己易學(xué)體系中的重要性和價(jià)值,瞿塘對(duì)此兩條例甚是注重并大力肯揚(yáng),認(rèn)為不知錯(cuò)、綜是入易之門:“故讀易者不能悟文王序卦之妙,則易不得其門而入。”(《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4頁(yè))由此可見(jiàn)這兩個(gè)條例在來(lái)氏易中的重要地位。
(三)陰陽(yáng)之理:錯(cuò)與綜得以確立的形上學(xué)理?yè)?jù)
表面上看,錯(cuò)、綜這兩大立象條例各不相同,而實(shí)質(zhì)上,二者得以確立的理?yè)?jù)則是共通的——皆根源于陰陽(yáng),本于陰陽(yáng)之理。因此,在來(lái)氏易中,二者根本不是相互疏離而毫無(wú)關(guān)聯(lián)的,相反,二者構(gòu)成了以陰陽(yáng)之理為統(tǒng)攝的一個(gè)整體。從更深一層的意義言之,這實(shí)際上反映了瞿塘一貫主張的象理一體不分的觀點(diǎn):大抵錯(cuò)者,陰陽(yáng)橫相對(duì)也;綜者,陰陽(yáng)上下相顛倒也。(《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中爻》,第116頁(yè))故錯(cuò)、綜雖形式各異,但皆為陰陽(yáng)二元組合和變化而成,其立象之根都在陰陽(yáng):錯(cuò)實(shí)質(zhì)上是陰陽(yáng)相對(duì)待,綜實(shí)質(zhì)上是陰陽(yáng)的上下流行。《易》曰“一陰一陽(yáng)之謂道”,瞿塘認(rèn)為,此兩大條例實(shí)皆本于此陰陽(yáng)之理:天地造化之理,獨(dú)陰獨(dú)陽(yáng)不能生成。故有剛必有柔,有男必有女,所以八卦相錯(cuò)。(《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3頁(yè))蓋易以道陰陽(yáng)。陰陽(yáng)之理,流行不常,原非死物、膠固一定者。故顛之倒之,可上可下者,以其流行不常耳。(《周易集注·易經(jīng)字義·錯(cuò)》,第114頁(yè))陰陽(yáng)之理,非交易則變易。(《周易集注》,第119頁(yè))從瞿塘和朱熹之間的思想關(guān)聯(lián)言之,此處交易、變易之說(shuō),蓋直接源自朱子《周易本義》(雖然《易緯》和鄭玄早有此說(shuō))。瞿塘認(rèn)為,天地造化,陽(yáng)主生而陰主成,陰陽(yáng)和合而后有萬(wàn)物。因此,天地造化之理。獨(dú)陰獨(dú)陽(yáng)皆不能生成萬(wàn)物,故有陰必有陽(yáng),陰陽(yáng)相互對(duì)待而依存。此即為錯(cuò)之條例得以立取的深沉理?yè)?jù)。同樣,綜之條例立取的理?yè)?jù)是陰陽(yáng)“流行不常”之理。因此,錯(cuò)和綜實(shí)皆為陰陽(yáng)之理所統(tǒng)攝,二者有共同的形上學(xué)根源。
職是之故,在瞿塘那里,錯(cuò)和綜又構(gòu)成了辯證的關(guān)系:“蓋有對(duì)待,其氣運(yùn)必流行不已。有流行,其象數(shù)必對(duì)待而不移。”(《周易集注》,第4頁(yè))所以,有錯(cuò)即有綜,有綜也必含錯(cuò),二者實(shí)一體而不分。錯(cuò),是一種靜態(tài)的陰陽(yáng)平衡;綜,則是動(dòng)態(tài)的陰陽(yáng)流行。
(四)錯(cuò)綜和卦序結(jié)構(gòu)
作為取象的重要體例,錯(cuò)綜說(shuō)在瞿塘注易的實(shí)踐中得到了極為廣泛的應(yīng)用,成為《集注》解釋卦爻辭的重要理?yè)?jù)。限于篇幅,茲不具述之。但錯(cuò)綜之于來(lái)氏易的意義并不局限于此,它還體現(xiàn)在瞿塘對(duì)易上下經(jīng)分篇問(wèn)題和卦序結(jié)構(gòu)的看法上。
對(duì)易的上下經(jīng)分篇問(wèn)題展開(kāi)探討,這實(shí)際上源起很早。其中,比較著名的是經(jīng)京房提出而為《乾鑿度》所發(fā)揮的“陽(yáng)三陰四說(shuō)”。它根據(jù)“陽(yáng)三陰四,位之正也”之說(shuō),認(rèn)為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三十而下為三十四,正是法象陰陽(yáng),是陽(yáng)三陰四之理的體現(xiàn)。具體來(lái)說(shuō),陽(yáng)道純而奇,所以上經(jīng)三十以象陽(yáng);而下經(jīng)三十四,則是法陰不純而偶之象。這個(gè)說(shuō)法,后來(lái)被孔穎達(dá)所接受,在《周易正義,序》中基本上抄錄下來(lái)。對(duì)易之上下經(jīng)分篇問(wèn)題的這一論釋,在其后的影響很大。
這里必須指出的是,孔穎達(dá)雖然在《序卦傳》的“正義”中提出著名的“非覆即變”說(shuō),但他并沒(méi)有據(jù)此說(shuō)而對(duì)經(jīng)之分篇問(wèn)題進(jìn)行相關(guān)探討,而是仍然采用了陽(yáng)三陰四說(shuō)來(lái)解釋此問(wèn)題。而開(kāi)始真正把“非覆即變”原則應(yīng)用到易的上下經(jīng)分篇這一問(wèn)題上的,要首推邵雍和張行成。此外,稍早于朱熹的楊甲、毛邦翰則根據(jù)邵雍的觀點(diǎn),直接畫(huà)出了“序卦圖”。但對(duì)此問(wèn)題詳加論辯、并對(duì)后世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的。則是朱熹:卦有正對(duì),有反對(duì)。……正對(duì)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余五十六卦,反對(duì)也。反對(duì)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其在上經(jīng),不變卦凡六……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為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jīng),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guò)》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為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dāng)?shù),則未嘗不均也。(《周易折中·序卦傳·集說(shuō)》)
朱熹此處所謂正對(duì)和反對(duì),實(shí)際上即是孔穎達(dá)提出的變和覆。顯然,在上下經(jīng)分篇問(wèn)題的解釋上,朱熹的這一說(shuō)法更讓人信服。瞿塘在易經(jīng)分篇問(wèn)題上的論說(shuō),即直接建立在朱熹這一解釋基礎(chǔ)上:文王序卦,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大過(guò)、頤、小過(guò)、中孚八個(gè)卦相錯(cuò),其余五十六卦皆相綜。雖四正之卦如否、泰、既濟(jì)、未濟(jì)四卦,四隅之卦如歸妹、漸、隨、蠱四卦,此八卦可錯(cuò)可綜,然文王皆以為綜也。故五十六卦,止有二十八卦。向上成一卦,向下成一卦,共相錯(cuò)之卦三十六卦。所以,上經(jīng)分十八卦,下經(jīng)分十八卦。(《周易集注》,第5-6頁(yè))
不難看出,這里瞿塘實(shí)際上補(bǔ)正了上文所引朱熹之說(shuō)的一點(diǎn)錯(cuò)誤,即綜卦數(shù)目五十六的規(guī)定。而更重要的是,由上引文可見(jiàn),錯(cuò)綜之說(shuō)實(shí)際上也成為瞿塘分析易經(jīng)分篇的內(nèi)在理?yè)?jù)。從易學(xué)史觀之,瞿塘以錯(cuò)綜來(lái)解釋易經(jīng)的分篇問(wèn)題,則直接為其后的王夫之所采錄。關(guān)于此點(diǎn),詳見(jiàn)王夫之的《周易內(nèi)傳》,
茲不具述。
易經(jīng)分篇問(wèn)題,實(shí)際上即暗含著卦序結(jié)構(gòu)問(wèn)題。而瞿塘對(duì)卦序的分析,就建立在其錯(cuò)綜說(shuō)之上:上經(jīng)首乾坤者,陰陽(yáng)之定位、萬(wàn)物之男女也,易之?dāng)?shù)也,對(duì)待不移者也。……下經(jīng)首咸恒者,陰陽(yáng)之交感,一物之乾坤也,易之氣也,流行不已者也。(《周易集注》,第109頁(yè))由上引文可見(jiàn),瞿塘認(rèn)為易經(jīng)之所以分別擇取乾坤和咸恒作為上下經(jīng)的端首兩卦,乃是錯(cuò)綜原則的內(nèi)在要求:上經(jīng)乾坤體現(xiàn)了“錯(cuò)”的原則,而下經(jīng)咸恒則體現(xiàn)了“綜”的原則。
瞿塘進(jìn)一步認(rèn)為,乾坤、咸恒在按照錯(cuò)綜的原則排定了在上下經(jīng)的位序之后,各自統(tǒng)領(lǐng)上下經(jīng)中的其余諸卦。具體而言之,自乾坤歷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十卦,陰陽(yáng)爻畫(huà)的數(shù)目正好各三十,其總數(shù)共六十。而根據(jù)來(lái)氏“陰陽(yáng)極于六必變”的原則,陰陽(yáng)至此困窮必變——此時(shí)錯(cuò)的原則退位,而須由綜來(lái)補(bǔ)充,故坤綜乾而為泰,乾綜坤為否。否和泰都是乾坤上下相綜而所成之卦。故乾坤等十卦之后,接以泰否兩卦。乾坤本相錯(cuò)而此時(shí)上下相綜成否泰,這正體現(xiàn)了前文已言之的錯(cuò)綜之間存在的辨證關(guān)系。在瞿塘看來(lái),“自同人以下至大畜,無(wú)非否泰之相推”。(《周易集注》,第109頁(yè))錯(cuò)綜既是辨證的,則乾坤必然要流行、相交感。這不但顯現(xiàn)于否泰,也體現(xiàn)在“乾坤之水火可交”這一點(diǎn)上。而根據(jù)伏羲方位圖,在乾坤和作為水火的坎離之間,又有艮兌震巽四卦,所以瞿塘說(shuō)“無(wú)水火則乾坤為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fēng)相薄,而后乾坤之水火可交。頤、大過(guò)者,山澤雷風(fēng)之卦也。頤有離象,大過(guò)有坎象。故上經(jīng)首乾坤,必乾坤歷否泰至頤大過(guò),而后終之以坎離。”(《周易集注》,第109頁(yè))這是錯(cuò)綜原則在上經(jīng)卦序中的具體統(tǒng)攝。
瞿塘對(duì)下經(jīng)卦序的分析亦類此。下經(jīng)以綜為首要原則,故以咸恒為始。咸和恒,分別由八經(jīng)卦兌和艮、震和巽構(gòu)成,據(jù)前所述可知這實(shí)質(zhì)上體現(xiàn)了陰陽(yáng)流行的綜原則。咸恒二卦統(tǒng)合其下的遁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諸卦,這十卦的陰陽(yáng)爻各三十畫(huà)又達(dá)六十之?dāng)?shù)。故值此又要變,即咸、恒根據(jù)綜的原則又分別演變?yōu)閾p卦和益卦。損、益兩卦則統(tǒng)領(lǐng)著自夬至節(jié)諸卦,“自?shī)A以下至節(jié),無(wú)非損益之相推”。瞿塘認(rèn)為,上經(jīng)主講天道、為體,下經(jīng)主講的則是人道、為用,故下經(jīng)多講男女。而根據(jù)錯(cuò)綜原則,男女不但相互對(duì)待,還要相互交感。所以,“無(wú)既濟(jì)未濟(jì),則男女為死物。故必山澤通氣,雷風(fēng)相薄,而后男女之水火可交。中孚、小過(guò)者,山澤雷風(fēng)之卦也。中孚有離象,小過(guò)有坎象。故下經(jīng)首咸恒,必咸恒歷損益至中孚小過(guò),而后終之以既濟(jì)未濟(jì)。”
由上可見(jiàn),瞿塘對(duì)卦序結(jié)構(gòu)的析辯難說(shuō)明詳,特別是對(duì)除乾坤、否泰、頤大過(guò)、坎離、咸恒、損益、中孚小過(guò)、既濟(jì)未濟(jì)諸卦之外的其他卦的論說(shuō)更是粗略。但其中亦有可貴者存焉:錯(cuò)綜原則始終一以貫之。而由此原則統(tǒng)攝下的卦序,整體上也顯得結(jié)構(gòu)井然,甚是嚴(yán)整、簡(jiǎn)明。前已言之,錯(cuò)綜的實(shí)質(zhì)是陰陽(yáng)之理。故瞿塘以錯(cuò)綜來(lái)析辯卦序結(jié)構(gòu),這實(shí)際上正合乎“《易》以道陰陽(yáng)”的本質(zhì)。來(lái)氏把錯(cuò)綜視為六十四卦排列次序所循的內(nèi)在建構(gòu)原則,無(wú)疑是合理的。對(duì)《易》之卦序有精詳考辯的李尚信先生,亦把錯(cuò)綜確定為今本卦序的一大排列原則,可見(jiàn)來(lái)氏錯(cuò)綜說(shuō)對(duì)我們今天在卦序問(wèn)題上的探討所具有的啟發(fā)意義。總而言之,錯(cuò)綜說(shuō)對(duì)來(lái)氏易非常重要,實(shí)為瞿塘建構(gòu)其易學(xué)的重要根基之一。
三、結(jié)語(yǔ)
瞿塘在《易注·自序》中嘗言:“自孔子沒(méi)而《易》已亡至今日矣。四圣之易,如長(zhǎng)夜者兩千余年。”顯然,此言頗有自負(fù)之氣。但竊以為,來(lái)氏易亦多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其中確有真切的重大發(fā)明。如在易學(xué)史上,對(duì)《序卦》的看法就一直頗有爭(zhēng)議,先儒多從“理”的角度懷疑此篇非圣人之書(shū)。即使如程《傳》、朱熹,亦明言此篇“非圣人之蘊(yùn)”、“非圣人之精”。而來(lái)知德慎思明辨,并不迷信程朱易學(xué)的權(quán)威,而是從中悟出了錯(cuò)綜說(shuō),認(rèn)為《序卦》實(shí)“有功于易”、“非為理設(shè),乃為象設(shè)也”。(《周易集注》,第471頁(yè))這個(gè)依據(jù)錯(cuò)綜說(shuō)而提出的觀點(diǎn),即頗有見(jiàn)焉。
自《系辭傳》提出“觀物立象”的模寫(xiě)說(shuō)之后,接受此說(shuō)者頗眾。但另一方面,對(duì)這個(gè)模寫(xiě)是如何可能和如何建構(gòu)這一難題作理論深思并詳加論說(shuō)的則一直少有人問(wèn)津。所以,來(lái)知德把這一重要問(wèn)題明確地提出來(lái)并加以詳論,提出自己系統(tǒng)的像象觀,這是對(duì)《系辭傳》以來(lái)的易象說(shuō)、特別是朱熹的易象說(shuō)的一個(gè)重大發(fā)展和推進(jìn),在易學(xué)史上無(wú)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
從形式上看,瞿塘的錯(cuò)綜和虞翻的旁通、反卦及孔穎達(dá)所言的變、覆似乎并沒(méi)有什么區(qū)別。這一點(diǎn),古今學(xué)者們似都認(rèn)同,權(quán)威的如黃宗羲和四庫(kù)館臣早就這樣說(shuō)過(guò)。但大家似乎都忽略了其中的兩個(gè)非常重要的分辯。其一,在形式上,來(lái)知德的錯(cuò)綜和虞翻的旁通反卦、孔穎達(dá)的變覆,實(shí)際上并不完全相同,其間有一些差異。如虞翻和孔氏的此條例,基本上都是就別卦而提出的。而來(lái)知德的錯(cuò)綜則是兼經(jīng)、別卦合而言之的。更重要的是,來(lái)氏易的綜的第一個(gè)形式,后兩者就都沒(méi)有。所以,二者是有重大區(qū)別的。其二,虞翻的旁通、反卦條例(特別是旁通),雖在其注解易經(jīng)卦爻辭中得到了應(yīng)用(這一點(diǎn)和瞿塘很相似),但由前文可見(jiàn),瞿塘應(yīng)用錯(cuò)綜的范圍實(shí)比虞翻要廣得多,而虞翻也沒(méi)有把旁通和反卦應(yīng)用到卦序的分析上。更為重要的是,從《周易集解》所引錄的虞氏之言觀之,虞翻的旁通說(shuō)亦缺乏來(lái)氏易那樣的形上學(xué)覃思和建構(gòu)。而孔穎達(dá)雖然發(fā)現(xiàn)并明確地提出了“兩兩相耦,非覆即變”的卦序排列原則,但他并沒(méi)有就此展開(kāi)論說(shuō),而在其注解易經(jīng)的實(shí)踐中也沒(méi)有加以應(yīng)用。因此,我們既不能從形式上把來(lái)氏易的錯(cuò)綜和虞翻的旁通反卦、孔穎達(dá)的變覆相混同,更不能因?yàn)槿叩南嗨贫?jiǎn)單地質(zhì)疑瞿塘錯(cuò)綜說(shuō)在易學(xué)史上的重要價(jià)值。
責(zé)任編輯:林忠軍劉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