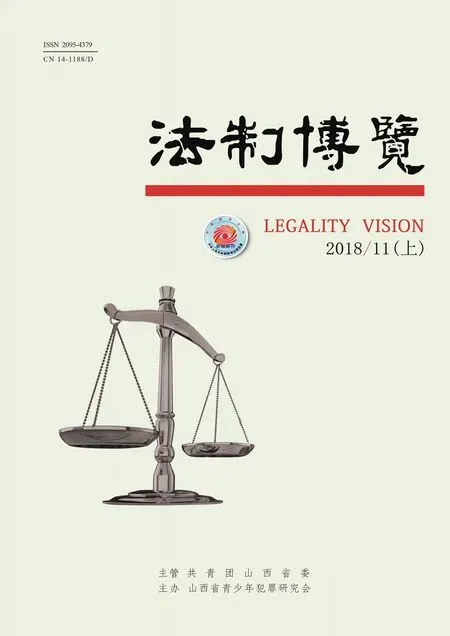關于正義的三個維度的解讀
胡 堯
重慶工商大學法學院,重慶 400067
一、對正義的一般理解
正義是人類社會所普遍認同和追求的價值目標,一般意義上是指具有公平、合理、合乎道義的屬性的思想、行為和制度等。正義在筆者看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社會關系中的不同階級有著不同的正義觀,在同一社會關系中的不同階級有著不同的正義觀,甚至在同一社會關系中的同一階級也有著不同的正義觀。而衡量正義的客觀標準是:這種正義所表現的行為方式和相關制度能否推動其所依存的社會關系向前發展,能否符合其所依存社會關系的一般規律,能否滿足此社會關系中主要階層的客觀利益需要。正義的最低要求是:正義所要求的劃分社會利益和承擔社會義務的規則不是任意的,而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和標準,即根據相應的規范進行分配或是按人的貢獻程度來進行分配亦或是按身份來分配社會利益和義務,但值得強調的是作為社會利益和義務的分配者要保持一定的中立。
在人類所存在的社會關系中都無例外的保持著對正義的熱忱。正義正如太陽一樣總是能引導著人類在創造理想社會的道路上不斷前行。盡管作為單個的人而言,對正義的向往不一定會大于對物質需求或者其他事物的渴望。但對于一個社會整體來說,正義在與人類在物質上的需求或者在對其他欲望的追求上相比,有著更大的價值。從最普遍的意義來說,正義作為人類社會生活中所追求的一種價值目標,其實質是要求確認和捍衛所在社會關系中個體的權利和利益的公平性、合理性和正當性。正義是社會制度得以建立的前提。
廣義的正義是屬于倫理學、政治學、法律學的范疇,正義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進行解讀。
二、道德的正義
道德正義就是道德認可和保障的正義。道德維度上的正義本質上是以品性和道義的形式來表現的社會關系的規則性,它通過倫理德行的方式來確定和保護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道德正義是社會正義的基礎。
我國倫理學界一般認為,道德正義是對一定社會關系中的法律、道德和政治等領域中關于善惡是非的價值評價和公義認識,即是指符合當下社會道德觀念的行為,而且還是主要用于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社會利益分配問題的一種標準。如果我們贊同這種觀點,那就需要確認的是:道德正義的根本思想在于社會整體應該公平、中立地對待每一社會個體,在道德權利及其義務、適用的評價尺度和行為規則上,都應該等閑視之,一視同仁。從中國傳承千年的悠久傳統來看,在社會發展的歷史中,儒家的道德觀是對中國封建傳統社會道德的最佳詮釋。儒家的道德觀讓我們了解到其所提倡“仁”觀念的尊人愛人,但也不可忽視其“親親尊尊”觀念中對親屬包庇犯罪的懲處不嚴甚至不處罰的弊病。
據此可以將西方近代以來所出現的法律思想進行對比,從資產階級文藝復興運動中那些啟蒙家所呼吁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來看,對于人權的重視和保護在逐漸加大,但另一方面對于人權及道德的評價采取雙重標準甚至多重標準,卻很讓人詫異。筆者十分認同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所提出的:“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夠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聯合起來的愛,則表現在戰爭、爭吵、訴訟、家庭糾紛、離婚以及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剝削中。”在恩格斯看來,正是由于階級對立的普遍存在,不同階級所代表的利益主體之間矛盾難以消除,道德正義所表現的也就只能是其所代表的階級道德的正義。綜上所述,每一國家之利益、每一階級之利益或是每一團體之利益的范圍之內,才有可能讓道德正義成為現實。這樣來看要想實現整個社會一致的道德正義,我們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三、法律的正義
法律維度上的正義就是法律認可和保障的正義。法律正義是社會正義的前提和保障。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法律歷來都會被看作是正義外化于行的存在,人們一般認為法律是國家意志的具體體現,法律應扮演中立者,公平合理的對社會關系做出裁判。但法律是否能夠完美的維護社會的正義,且法律正維度的正義能否與社會正義劃上等號,這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定論。
筆者很認同馬克思主義所認為,法律是“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正是如此,哪一個階級占領導地位,這一國家的法律所表現出的生產和生活關系就與這一階級所代表的利益相一致。因此,法律正義是相對于不同階級而言的。就算是依照西方一直倡導的主權在民的觀點來理解,在與此相應的社會條件下,也很難讓人去信服法律正義與社會正義是可以劃上等號的;恰恰相反,它們總會在某些方面相抵觸。
法律正義在形態上來說是動態的,作為上層建筑會隨著社會關系的發展而進步。法律正義在根源上來說是為了自身階級所代表的經濟基礎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得到認可。而且當經濟基礎發生改變時,之前所確認的法律正義也就成了無源之水,這時的正義往往就有可能是不正義的。因此,法律正義具有時間性和空間性,法律只能在其所扎根的經濟基礎保有合理和正當的時間和空間內才能夠維護其代表的階級的正義。
法律正義亦是將正義進行法規化和合法化的一種體現,是通過創立和執行法律法規等對人際關系進行規制而形成的社會關系。法律正義大大提升了法律的實際效果,即適用法律一律平等。正是如此,法律正義實現所能達到的最大限度和與社會正義的同化的速率,這與從事立法、司法和執法工作的法律隊伍素質緊密相連。這樣的法律隊伍所擁有的素質越高,就越有利于法律正義的實現,反之亦然。法律對正義的實現作用主要體現為。
第一,分配權利以確立正義。這是法律表現在對社會資源和利益進行公平分配上的作用,其中包含了對于分配標準的法定化、標準化,在此基礎上將權利和義務進行量化,實現對資源和利益公平公正的分配。這種對于權利義務的處理方式,對于資源和利益的分配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當這一法定的標準被不特定的社會個體所違反時,這時法律上的正義就開始發揮作用,就會對違反標準的個體進行懲罰,并對被損害方進行救濟補償,從而達到正義的目的。
第二,懲罰罪惡以伸張正義。這是法律實現正義的另一方面。以刑法為例,刑法對于違法犯罪的犯罪個體進行懲罰,其目的在于維護社會秩序和犯罪預防。當然同時也通過懲罰犯罪來發揚善良正義,引導良好的社會風氣。犯罪不僅是違反法律對社會造成危害的不良行為,同時也違反了正義的理念,是邪惡的。正是基于正義的基本理念,就應該懲惡揚善,打擊犯罪和邪惡行為。這是宣揚正義觀念的必經之路,也是弘揚社會主義道德的應有之義。
第三,補償損失以恢復正義。依據前文所述,懲罰犯罪和補償損失是始終聯系在一起的。懲罰犯罪是在法律和道德上去伸張正義,發揚正氣;而補償損失則是對被損害方在利益上進行救濟,也是正義的客觀要求。法律也正是基于此項考慮,除了懲罰犯罪打擊邪惡之外,在民法等部門法上對合同違約之類的案件,通常表現為去救濟被損害方的經濟損失等。這種方式一般主要以經濟補償為主,其他方式為補充。看起來這種方式有些不足以抵消損害方的全部傷害,但其實是法律對于社會整體的考慮,是為了恢復正義。
“正義只有通過良好的法律才能實現”,“法是善良和正義的藝術”,這些古老的法學格言表明法與正義是不可分的,法是實現正義的手段,法的價值之一在于實現正義。
四、個體的正義
個體維度上的正義就是個體認可和保障的正義。正義作為倫理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其具有很強的主體性。任何形式的正義,無論是其施動者還是受動者都具有現實性,是現實中實實在在存在的。故而正義,究其根源來說都是人的正義。可以這樣說,只要離開了現實中的人,所有的正義就會馬上喪失了其依存的前提與基礎,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故而正義的前提是現實中的人,不包括那種隱居山林的隱士等處于固定不變狀態的人,而是在不斷變化的現實中的、且在當今條件下不斷發展的人。現實中存在的人,也就是筆者要討論的正義問題的基礎。也正是基于此,正義作為一種和人的行為息息相關,且為人類社會的道德評價標準之一,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也正是正義的本質屬性。正是如此,人不僅僅是為正義所反映的主體,也是去評價正義的主體。
所謂的個人正義問題是指對個人存在及其行為是否正義的追問。在這種認識形式中,個人成為對象,就會表現為主體。毋庸置疑的是,社會對于作為社會個體的個人的認知、評價以及管理措施是要通過基數十分龐大個體,也就是個人來實現的。但是,這種追問所由之出發的立場、所運用的尺度都是社會的。當一個人或一個群體評價某個人是否正義的時候,他或他們是在代表社會說話,社會的利益、秩序、要求永遠是個人正義與否的客觀尺度。個人的道德自省實質上是代表社會的個人對于個體化的個人的審美。個人的責任、義務、良心只不過是社會秩序、要求的內在化。一個人在道德上越是獨立、自由、高尚,他就越是一個社會化的存在。在絕對高尚的意義上,他就是社會秩序、利益、要求的化身。無論是自我還是他人的利益需要都不能成為個人正義與否的尺度。
如果以自我需要為標準,恐怕沒有人是非正義的;如果以他人的利益為標準,正義或非正義就流入純粹的相對之中。從正義的目的上來看,個人維度上的正義問題的討論其根本是為了規范作為社會個體的個人的行為,要使個人適合于社會的整體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