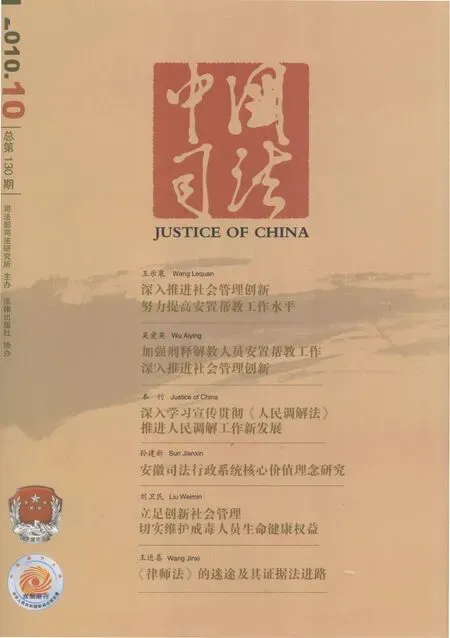“大調解”視野下完善非訴訟調解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
盛紅斌 (重慶市法律援助中心 重慶 401147) ■文
“大調解”視野下完善非訴訟調解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
Im p roving the A pp lica tion of N on-litiga tion M ed ia tion M easu res in L ega lA id in the Perspec tive of‘G rand M ed ia tion’
盛紅斌 (重慶市法律援助中心 重慶 401147) ■文
一、將調解引入非訴訟法律援助的背景探究
(一)中國的調解傳統
在儒家 “無訟”觀念及道家 “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基礎上,形成了中國民間調解的歷史傳統。調解作為一種糾紛解決方式,已經被實踐了數千年。經過研究和實踐,大家越來越認識到:調解工作既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又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協調,符合當前多元化、多途徑解決民事糾紛的世界潮流,符合先進的訴訟理念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因此,有人認為,一定程度上考量,“調解在中國絕不僅僅是一種糾紛解決的技術或方式,而是社會治理的一種制度性或體制性存在”①湯維建:《論解決民事糾紛的系統工程》。。
(二)國外關于訴訟外調解的立法
舉目世界,調解已不再是中國的“專利”。歐美法治國家ADR (A lternative D ispu te Reso lu tion)運動正日益高漲。ADR,我國通譯為“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或“訴訟外糾紛解決手段”。該概念源于美國,現系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程序或機制的總稱。世界各國關于訴訟外調解的立法也得到了蓬勃發展,形成了與民事訴訟機制相互銜接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日本、英國、澳大利亞、挪威、菲律賓等國也將其納入法制化軌道。可以說,調解制度正在全世界范圍內得到發展和重視。
(三)調解機制引入法律援助工作的現實意義
當前,伴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社會矛盾日趨多樣化和復雜化,并以案件的形式大量表現出來。而由于社會誠信缺失、執行難等問題的出現,部分法院的裁判成為法律白條,訴訟成為馬拉松式長跑,使裁判既判力、終局性等司法權威受到損害,訴訟效率和效益不能實現。在此情況下,將調解機制引入法律援助工作,形成了非訴訟調解這一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形式。不僅有效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并且有利于把大量糾紛及時化解在基層和萌芽狀態,有效緩解和減少社會矛盾,有利于節約訴訟成本和人力資源。
二、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的概念
調解,是指雙方當事人以外的第三者,以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以及社會公德為依據,對糾紛雙方進行疏導、勸說,促使他們相互諒解,進行協商,自愿達成協議,解決糾紛的活動。在我國,調解的種類很多。因調解的主題不同,調解有人民調解、行政調解、法院調解、仲裁調解、以及律師調解等。在這幾種調解中,法院調解屬于訴訟調解,其他都屬于非訴訟調解。
本文所指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指法律援助人員將調解運用于非訴訟代理,通過代理受援人一方運用調解方式,促成與爭議對方和解,從而解決案件糾紛的法律援助行為。法律援助人員不應作為調解主持人或者調解員,應當以受援人代理人的身份參與調解。
三、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運行現狀
據統計,2008年,全國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 54.6萬件,比 2007年增加 30.2%;受援人數達到 67萬人,比 2007年增加 27.9%。2008年全國共辦理農民工案件 19.1萬件、殘疾人案件 4.5萬件、婦女案件 12.4萬件、未成年人案件 8.9萬件。擬繼續加大以非訴訟方式盡快實現受援人合法權益的工作力度,以期非訴訟調解結案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僅農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調解結案率就已超過 10%②賈午光:《在全國法律援助處長 (主任)會議上的講話》。。
以重慶市法律援助中心為例,2008全年共辦理法律援助案件 3015件,其中民事案件 2516件,受援人總數 2528人,占案件總數的 83.4%。民事案件主要類型為:用人單位解除勞動關系引發的勞動爭議 1643件,農民工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爭議為 393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 50件,工傷待遇 26件。從上述已辦結案件的情況來看,通過非訴訟調解的案件達1263件,占民事案件的 50%。包括重慶在內的全國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在代理非訴訟調解案件過程中,通過不斷實踐,探索出了其辦案原則,受理范圍,辦理程序及規范要求。
(一)辦理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案件原則
1、優先調解原則。接受案件后,先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再引導當事人進行訴訟。
2、當事人自愿原則。受援人和爭議對方自愿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調解,當事人基于真實的意思表示,達成調解協議。
3、依法調解原則。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調解,不得違反法律的禁止性規定。
4、最大限度保護受援人合法權益原則。僅代理受援人一方參與調解,不得進行居中調解,不得損害受援人的合法權益。
5、方便快捷原則。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且適用調解解決的案件,一般應在 30日內辦結。
在此,想說明的是為何沒采納《民事訴訟法》第 85條規定“事實清楚責任明確”的調解原則,因為一是調解不需要“事實清楚”,因為當事人只要申請調解或接受調解,并達成調解協議,就應該推定為“事實清楚”,調解對事實的要求遠不如判決那么嚴格和全面,其本身也應包括對某些難以查清的事實進行互諒互讓的調和,以達成定分止爭之目的。二是調解不需要“責任明確”,因為訴訟中只要當事人自愿要求調解,并達成調解的,完全是其對民事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處分,只要不侵犯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就應允許和認可。
不將“事實清楚,責任明確”作為調解的處理原則,主要是從受援人方面進行思考,而法律援助人員卻需要查證事實,明確責任,比如調解之前評殘,比如調解之前證明工傷事實的成立,因為調解一旦不成功,后期的訴訟需要“事實清楚,責任明確”這一基本條件。
(二)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案件受理范圍
非訴訟調解幾乎適用于所有的民事法律援助事項,如依法請求國家賠償,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請求發給撫恤金或者救濟金,請求給付贍養費、教育費、撫養費,請求支付勞動報酬,請求殘疾侵權賠償,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等。刑事法律援助事項由于其特殊性不適用非訴訟代理,但是,刑事附帶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民事賠償部分以及刑事案件的當事人單獨就民事賠償提起民事訴訟除外。
根據我市實際情況,目前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除上述事項外,還包括困難農民土地、林地經營權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中權益受到損害請求賠償的事項,困難群眾因交通事故和醫療事故權益受到損害請求賠償的事項;農民因假冒偽劣生產資料 (假種子、假農藥假化肥)權益受到損害請求賠償的事項。
雖然幾乎所有民事法律援助案件都可以進行非訴訟調解,但是以下案件調解成功機率要高得多,所占比例也要大得多:一是法律關系明確、爭議不大,雙方都同意訴前調解的一般民事案件,比如已評殘的人身損害案、工傷案。二是贍養、撫養、扶養案件。三是涉及面廣,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案件,如農民工集體討薪案件。同時,必須看到,有部分群體性案件,比如勞動者對原國有、集體企業在改制過程中按安置方案支付的安置補償費用等發生的糾紛,由于涉及到相關政策因素,調解成功機率則大大降低。
(三)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案件的辦理程序和規范要求
民事糾紛在法律援助機構受理、指派后,進入訴訟或仲裁前,一般由法律援助人員代表受援人的利益進行調查取證,分析是非,并在此基礎上與對方當事人依法協商調解,受援人與爭議對方同意和解并就和解意見達成一致的,應當制作并簽署調解協議書。調解協議書主要包括以下內容:(1)爭議各方當事人的基本情況和調解代理人姓名; (2)爭議的基本事實;(3)調解結果; (4)調解協議書的生效時間和協議履行期限;(5)爭議各方當事人和調解代理人簽名蓋章,注明簽署日期。調解協議書分別由爭議各方當事人和法律援助機構收存。
(四)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案件的優越性
1、縮短辦案周期,提高辦案效率。訴訟法律援助案件需經法院立案、一審、二審、直至強制執行等程序,辦案周期較長。而通過非訴訟調解的法律援助案件,從案件受理到辦結,最快的只用了幾個工作日,周期短,效率高,及時化解矛盾,維護了受援人的合法權益。
2、降低維權成本,減輕受援人負擔。與訴訟案件相比,非訴訟調解案件可以大大降低受援人的維權成本。訴訟程序中的訴訟費、保全費、司法鑒定費、公告費、執行費等費用在非訴訟調解案件中基本上都可以省卻,自然減輕了受援人的經濟及精神負擔。
3、社會效果良好,與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相適應。非訴訟調解與訴訟相比,更有利于家庭、社會、鄰里的和諧。以工傷法律援助案件為例,承辦律師堅持調解優先原則,在調查取證的基礎上,對當事人進行引導、勸誡,可以有效消除誤會,避免農民工在先予執行很難得到支持的情況下,解決了急需的醫療費問題。
四、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非訴訟調解代理人的地位、作用定位不準
目前,有部分法律援助人員對法律援助非訴訟調解與行政調解、人民調解、訴訟調解最本質的區別把握不準。法律援助非訴訟調解除具有前述幾種調解形式的共性之外,就是法律援助非訴訟調解不是居中調解,而是代理困難群眾一方為維護其合法權益而進行的代理活動,代理人立場和觀點有著明顯的傾向性,其主張的是受援人正當的、合法的權益。
有觀點認為,法律援助人員可以作為調解人主持調解,只須把握調解人和代理人的角色轉換,在不損害受援人合法權益的前提下,可以充分發揮調解人的作用,并調解成功。理由是,法律援助人員履行的是政府對公民的法律援助職能,法律援助人員與受援人之間沒有報酬關系,能比較客觀公正地提出解決紛爭的意見和方案,法律援助人員的這一特殊角色地位,也容易得到對方當事人的接受和信任③王振鐸:《最新法律援助條例與法律援助案例分析實用手冊》。。
對上述觀點,筆者并不認同。法律援助律師接受糾紛一方當事人委托解決糾紛時,進行居間調解或主持調解,雖是現階段法律援助工作的常態,但是這有悖于民法基本原理,有違公平公正原則。代理人的職能應是最大限度為當事人爭取利益,調解人則應在合法范圍內,平衡各方利益,公平、迅速解決糾紛。為糾紛解決者應處于中立地位,英國的自然正義中就有“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說法,美國的戈爾丁也在《法律哲學》中解釋道:“沖突的任何解決方案都不能包含有沖突解決者自己的利益。”既是調解人,又身兼代理人,無法體現調解者的中立地位,混淆了二者之間的職能差別。
同時又必須看到,這是現實無奈的選擇。比如一般賠償案中,在與對方調解過程中,對方往往沒有律師代理,又不熟悉法律,作為受援人的律師,不得不既作為一方代理人,又作為調解主持人,“運動員裁判一身挑”。這樣的直接后果是,受援人律師提出的調解方案往往很難取得對方認可,因為缺少中立第三方,難以在調解過程中建立平衡和制約機制。
(二)簽訂調解協議后隨意反悔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人民調解協議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一條規定,“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的有民事權利義務內容,并由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者蓋章的調解協議,具有民事合同性質。當事人應當按照約定履行自己的義務,不得擅自變更或者解除調解協議。”這一規定將人民調解協議確定為具有民事合同性質。
參照這一規定,法律援助非訴訟調解協議也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但沒有強制執行力,一方當事人對調解協議反悔的,另一方當事人只能就糾紛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這就導致非訴訟調解協議如不當場支付賠償金,自動履行率并不高,反悔情況比較突出。
(三)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人員思想上的畏難情緒和實踐中的經驗缺乏
1、思想上的畏難情緒。雖然非訴訟調解有諸多優點,但與法律援助人員代理訴訟相比較,工作量并未得到減少,有時甚至增加了,比如一般調解都需要在調解前做好調查取證固定證據等工作,一方面是調解的需要,一方面也考慮到一旦調解不成,則為訴訟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除了法律方面的準備,還必須了解掌握調解雙方當事人的基本情況,背景資料,以利于知已知彼。因此,面對增加的工作量,部分律師認為非訴訟調解羅嗦麻煩,不如讓法院裁判來得直接。
2、實踐中的經驗缺乏。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和人生閱歷,對糾紛解決的合理性和效果把握得當,對當事人具有親和力,而不是拘泥于法律本身的規定,調解就會駕輕就熟,既能提高效率,又能獲得好評。然而現實生活中,一個具有深厚法律專業知識的律師往往會對一個很小的民事糾紛調解案束手無策的現象屢見不鮮,問題關鍵是對于非訴訟調解案件受援人權益保護的尺度把握不準,導致久調不決。
還比如部分法律援助人員在受援人傷情未得到確診的情況下進行調解,導致賠償方案沒有相應的依據和標準,不能得到對方當事人的確認,也不能打消受援人自己利益可能受損的顧慮,從而使調解陷入僵局。
五、完善法律援助非訴訟調解的建議
(一)探索 “大調解”格局,成立矛盾調處中心,建立非訴訟調解與其他形式調解的銜接機制
現實生活中法律援助案件呈群體性、跨社區性、調解方式的多重性等特點,單一的非訴訟調解已難以化解復雜的社會矛盾。因此,有必要發展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政法綜治牽頭協調、社會矛盾調處中心具體負責、司法部門業務指導、職能部門共同參與、社會各方整體聯動的“大調解”機制,實行共同調解、聯合調解等跨地區、跨行業、跨單位的調解機制,整合各類調解資源和手段,使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有機結合,形成多種調解方式多管齊下,多種調解主體協同作戰的新格局。
為此,建議推廣各地經驗,成立省、市、縣級社會矛盾調處中心,仿照行政服務中心運作模式。該中心由總工會、信訪局、公安局、法院、勞動與社會保障局、司法局等成員單位組成,以第三方名義獨立開展專業化“一站式”調解服務,如一起普通的勞資糾紛案,如果調解不成,當事人可以選擇勞動仲裁,就在調處中心開庭;對不服勞動仲裁需要訴訟的,由設在中心內的勞動爭議庭審理;對受理的糾紛如屬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中心提供全程法律援助;調處、仲裁、審理的糾紛最終需要強制執行的,法院開辟“綠色通道”,專門設立勞資糾紛案件執行小組等。
上述形式,不僅形成法律援助非訴訟調解、人民調解、行政調解、訴訟調解之間的銜接聯動,也解決了單一非訴訟調解法律援助中援助律師多重身份問題,法律援助人員即可以代理人身份進入各類調解案件中。
(二)賦予非訴訟調解協議強制執行效力
鑒于非訴訟調解協議簽訂后當事人隨意反悔的情況,筆者認為可以通過大力推行非訴訟調解協議公證來實現。除當事人即時履行完畢和無給付內容之外,援助律師應積極引導雙方當事人對調解協議中給付內容進行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公證,負有義務的一方當事人不履行經過公證的調解協議時,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由于對調解協議進行公證無須進行實體審理,僅須進行書面審查即可,程序相對簡單,而且我國《公證法》對公證員的任職資格也作出較高的規定,因此公證機構完全有能力勝任該項工作。
(三)借鑒訴訟調解及人民調解經驗,不斷創新非訴訟調解的方式和方法
法院訴訟調解的三個“切入點”方式具有借鑒意義:一是找準案件爭議的焦點。對當事人之間的訴爭矛盾追根溯源、把握準矛盾癥結所在,有針對性地做好當事人的思想工作。二是找準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點。因為調解的本質是協調當事人自行處分民事權利,調解人的作用就體現在斡旋和疏導的作用上,幫其找到平衡點,引導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三是找準法理與情理的融合點。大力宣傳相關法律及社會主義良好道德風尚,綜合發揮法律與道德規范的雙重作用。
同時,選擇采用下列方式進行調解:一是闡釋法律;二是提供相關標準和數據,如殘疾賠償金的賠償標準;三是對案情的了解和分析;四是提供與預測判決結果最相近的調解方案,并說明其根據;五是選擇類似的判例提供給雙方當事人作為引導;六是與雙方當事人就案件的證據、事實、法律適用發表意見。
調解的方式方法只是實現解決糾紛的一種手段,只要能有利于實現平息糾紛、維護人民內部的團結和合法權益,各種方法均可以嘗試,在實踐中不斷創新非訴訟調解的方式和方法。
(責任編輯 趙海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