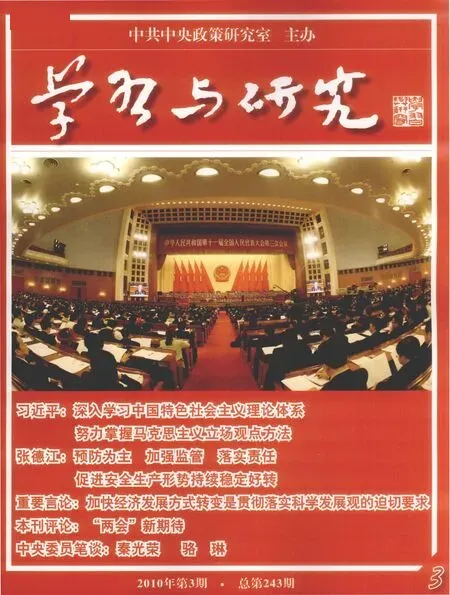王陽明“實心實學”思想初探(下)
葛榮晉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0872)
王陽明“實心實學”思想初探(下)
葛榮晉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00872)
王陽明心學體系中所蘊涵的“實心實學”思想,可以概括為:“本體工夫合一”的“實心”論,“實地用功”的“實功”論,“踐履之實”的“實行”論,以及“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的“明德親民”論。王陽明“實心實學”思想,是明清之際“實學”社會思潮的理論源頭之一。
王陽明;心學;實心實學;明清社會思潮
三、“踐履之實”的“實行”論
通過在“在良知上用工”的“實地用功”,只是停留在獲得道德觀念(知)的階段,要想真正成為賢人或圣人,還必須將道德之知轉化為道德之行,方可達到“知行合一”的圣賢境界。“踐履之實”是王陽明“實心實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王陽明全集》中,共檢索出“實踐”范疇7條,“實行”概念3條。從“實踐”、“實行”條目看,王陽明強調在“格致實功”論的基礎上,要求“反身實踐”。如果只知不行,則是“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傳習錄》上》)王陽明在談到與朱、陸之辯時,告誡他的朋友和學生,不重言辯,要重“身體實踐”。他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議論我者,茍能取以為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傳習錄中·啟問道通書》)在《教約》一文中,王陽明“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凊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飾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傳習錄》中》)王陽明針對他的學生知而不行的弊端,指出:“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譜三》)故王陽明“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譜一》)徐愛在《傳習錄序》中指出:成圣之道“不能專求圣人于言語之間”,必須“使之實體諸心”。如果“吾儕于先生(指王陽明)之言,茍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序說.序跋》)錢德洪在《答論年譜書》中亦指出:如果“真能盡性盡仁,以務求于自謙矣”(《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七年譜附錄二),即可得圣人真諦。可見,王陽明及其弟子皆重視“實踐”、“實行”在成賢成圣中的作用。
王陽明的“踐履之實”的“實行”論,是針對當時的社會弊端而提出的“對病的藥”。王陽明在理論上認為程、朱的“知先行后”說,必然會造成“將知行分作兩截”的弊病,可能在實踐上造成“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傳習錄》下)從歷史上看,“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糜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傳習錄》上)從現實上看,“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夸詡其先世以為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四外集六《竹江劉氏族譜跋》)在閹宦專權的明王朝,貪官污吏橫行,到處魚肉百姓,綱常敗壞,言行不一,不少學者滿口“仁義道德”,實際上是“男盜女倡”。王陽明認為,要想補救當時社會弊端,必須提出強調“踐履”、“實行”的“知行合一”之說。他在《與道通周沖書五.四》信中指出:“知行合一之說,專為近世學者分知行為兩事,必欲先用知之之功而后行,遂致終身不行,故不得已而為此補偏救弊之言。學者不能著體履,而又牽制纏繞于言語之間,愈失而愈遠矣。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足下但以此語細思之,當自見,無徒為此紛紛也”。(《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二,補錄)足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一劑救治“假道學”、“偽君子”的良藥。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是以“踐履之實”為核心的實行之說。它包括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什么是知?他把知分成“真知”與“未知”。“真知”是未被私欲隔斷的“知行本體”之知,故它是知而即行的真切之知;“未知”是被私欲隔斷的“知行工夫”之知,故它是知而不行的未知。王陽明指出:一些學者所以知而不行,是因為“此已為私欲隔斷,不是知行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錄》上)在他看來,“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王陽明全集》卷六《答友人問》)所以,“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
(二)什么是行?由于知有“真知”與“未知”之分,故行也有“意行”與“踐行”(“實行”)之別。王陽明指出:“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須要徹底徹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一念發動處即是行,如是不善之“意行”,應當將其不善之念徹底克倒,把“私欲”消滅於“意行”之中,決不能將其變成現實的“踐行”;如果是善之“意行”,自然會變成善的“踐行”。那么,什么是“行”呢?王陽明除了“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以知代行,把意念之知等同于“行”的“意行”外,還承認有客觀存在的“踐行”。他說:“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王陽明全集》卷六《答友人問》)他進一步論證說:“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不管是“凡謂之行者,著實去做這件事”還是“履其實而言謂之行”,都是“身親履歷”的意思。王陽明認為,不管是道德之知還是自然之知,都是源于“身親履歷而后知”,肯定“行”是“知”的基礎和來源。他具體而生動地論證說:“食味之美,必待入口而后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先知食味美惡者耶?……路歧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后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歧之險夷者邪?”(《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又說:“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吃。”(《傳習錄》上)他還進一步把“為學”解讀為兼行之學,充分肯定親履實踐對街修德、求知的重要價值。他說:“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身孝道,然后謂之學,豈有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箭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同時,知是行之始,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在某種意念、動機和欲望指導下進行的。他論證說:“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傳習錄》中)
(三)“知行合一并進之說”。王陽明在解讀了知與行的內涵后,把知與行的關系摡括成“知行合一并進”,認為二者本是一個工夫,彼此不可分離。什么是“知行合一并進”呢?一是“知行互涵”,即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陽明從正面釋曰:“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傳習錄》上)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從負面釋曰:“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元來只是一個工夫。”(《王陽明全集》卷六《答友人問》)二是知行并進。知與行是不分先后的。他認為“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傳習錄》下),“如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看見好色時己自好了,不是見好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聞到惡臭時己自惡了,不是聞惡后別立個心去惡。”根據“知行合一并進之說”,他在批評“行而不能明覺精察”的“冥行”的同時,更著力于批評“知而不能真切篤實”的“妄想”。他指出:“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為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己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王陽明全集》卷五《與陸原靜》)在這里,既批評了“從冊子上鉆研,名物上考察”造成只空講而不力行的程朱學派,也批評了受其影響的“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未嘗體諸其身,名浮于實,行不掩言”的空談者。
明清之際的實心實學派在否定王陽明“知行合一說”中的先驗論成分外,還積極地吸取了它的“踐履之實”的“實行”論思想。東林學派顧憲成指出:“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這個知作光景玩弄,便走玄虛去。故就上面點出一個致字,此意最為精密。”(《小心齋劄記》卷四)他還針對當時“一切求靜”的歸寂派,強調“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也。”強調“學問必須躬行實踐方有益。”(《高子遺書》卷五《會語》)王夫之在批評王陽明的“銷行入知”的“意行”論的同時,對王陽明的“實踐”論或“實行”予以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行可兼知而知不可以兼行”(《尚書引義·說命中二》)的光輝思想。王學殿軍劉宗周晚年吸取王陽明“踐履之實”的實行論思想,大力提倡“力行”哲學。崇禎十五年(1642)三月在《答錢生欽之》的一封信中指出:“‘力行’二字甚佳,而所該亦詳以盡。如體認是力行第一義,存養是力行第二義,省察是力行第三義,踐履是力行第四義,應事接物是力行第五義。善反之,則應事接物正是踐履之實,踐履正是省察之實,省察正是存養之實,存養正是體認之實。歸到“體認”二字,只致良知足以盡之,此正所謂力行之實也。今人以致知為一項,以力行為一項。所以便有病痛。又就其中每事都逐件看,或后先錯雜,或支離紛解,愈遠而愈不合矣。”(《劉宗周全集》第三冊《文編三》)在劉宗周看來,“力行”二字涵攝“五義”:體認、存養、省察、踐履、應事接物,以是“力行之實”。劉宗周在晚年開講的“證人之社”第九會,曾經提到:“我輩倡良知,正為力行地耳。要之,知與行總不得分。”(《劉宗周全集》第二冊《語類十五》)劉宗周之所以提倡“力行之實”,是為了糾正陽明后學王龍溪、周海門一派“舍工夫談本體”的“病痛”。劉宗周的“力行”哲學,上承王陽明“致良知”宗旨,下啟黃宗羲“致字即是行字”的哲學思想,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理論價值。漸東學派黃宗羲在劉宗周的“力行”哲學的基礎上,指出陽明后學“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象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明儒學案》卷六十)提出了“致字即是行字”的力行哲學命題。他說:王陽明“‘致良知’一語,發自晚年,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后來門下各以意見攙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復立言之本意。先生之格物,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以圣人教人只是一個行,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是行也。篤行之者,行此數者不已是也”。先生致之於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窮理。’”(《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
四、“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的“明德親民”論
“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這一經世思想,是王陽明在《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一文中提出的。王陽明在此文中,依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為鄉約事,指出:“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為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修業,下民焉有不歸於厚道乎!”。(《王陽明全集》卷十八《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王陽明推行十家牌諭本是為了“息盜安民”,如果在推行中“一暴十寒”或者“虛文搪塞”或者“生事擾眾”,都不是“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而揭陽縣主簿季本“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為有司者,皆能以是實心修業,下民焉有不歸於厚道乎!”。(《王陽明全集》卷十八)在王陽明看來,揭陽縣主簿季本是“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的典范。
“明德親民”論是王陽明在同朱熹的辯論中提出來的。王陽明根據“知行合一”論和“致良知”說,對《大學》一書作出了新的詮釋。他反對朱熹將《大學》中的“親民”改成“新民”,因為“新民”是從效果言,而“親民”則是從心性言;指出朱喜將《大學》中的“物有本末”釋為“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是分人己為二、“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他批評道:“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可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干,謂之本;本之稍,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也。”(《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續編一《大學問》)在王陽明看來,“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明明德”是己之“心上工夫”,而“親民”則是心本體的外在作用,即在“事上磨練”工夫,二者雖有體用、本末之分,但“不得不分為兩物也。”
王陽明在《大學古本序》中,從“體用相涵”的高度,闡釋了“明德親民之本為一事”命題。他說:“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下之間,則備矣。”(《王陽明全集》卷七《文錄四》)在這里,“體用相涵”有兩層涵義:一是心體身用。格物以誠意的“事上磨練”工夫,就事上盡心而言,即是正心復其體的工夫;就事為實踐而言,即是修身著其用的工夫。故從一身來說,則正心為體,修身為用。他論證說:“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為善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后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續編一《大學問》)又說:“《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個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王陽明全集》卷三《傳習錄》下)二是從天下而言,明德為體,親民為用,明德與親民不可分為兩物,我之身心與親天下之民是息息相關的。他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又說:“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王陽明全集》卷一《傳習錄》上)明明德是修己以仁德,而修己以仁德必兼有親親、仁民、愛物之意,二者是不可分的。
王陽明以“仁者以天下萬物為一體”之說重新詮釋了“明德親民”論。王陽明將佛、道的“本體”觀念引入哲學,吸取了墨家的“兼愛”、莊子的“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以及惠施的“泛愛萬物,天地一體”的觀點,并在孔、孟的“親親、仁民、愛物”和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的基礎上,“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旨”(《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七),從本體論和境界說相結合的高度,提出了“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哲學命題。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從境界論看,就是一種無私的“大我”的天地境界。在這種“大我”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只覺悟到自己是整個社會的一員,“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傳習錄》中),從而能夠為社會做好事,所做之事皆具有道德意義;而且更覺悟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員,“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草木鬼神鳥獸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我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續編一》《大學問》)所做之事,不只有益于社會,也有益于“天地萬物”。如果說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人被“間形骸、分爾我”的自私自利的“小我”所蔽、遂滋生出各種罪惡現象的話,那么在天地境界中,“我”已不再是功利境界中的“小我”,而是“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的“大我”,我之身即天地萬物,我之意識即是大我之意識,最終實現“天地萬物一體”的人生理想。從本體論看,王陽明立足于他的心性學說,將人心固有的仁愛之性擴展到家庭、社會再到宇宙萬物,把人與天地萬物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認為“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大人“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同上)“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于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后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后悌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王陽明全集》卷二十六續編一《大學問》)由此可見,王陽明的“天地萬物一體”之說,是建立在“心之仁本若是”的基礎之上,都是由“父子兄弟之愛”的仁愛本性中推衍出“不忍之心”、“憫恤之心”和“顧惜之心”的生態倫理思想。王陽明提出的“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哲學命題,不僅承認植物、動物乃至整個自然界都有內在的價值和生存權利,而且也自覺地把人的天賦愛心由傳統的人際道德向生態倫理擴展,從而構成了現代生態倫理學的最主要的內容,成為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基石,其功偉矣!
王陽明從“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經世思想出發,對佛、老的“虛無寂滅之教”與俗儒的“記誦詞章之習”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夫禪之學,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王陽明全集》卷七《文錄四》《象山文集序》)在王陽明看來,“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物,把心看成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傳習錄》下)佛、老只講“虛空圓寂心”,“只說明明德,不說親民”,“棄人倫,遺物理”,就是逃避人生的社會責任,所以,不可治天下國家。又說:“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圣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所以,“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王陽明全集》卷七《文錄四》《別湛甘泉序》)
“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的經世思想,王陽明作為“為世之師”在理論層面作出了全面闡述,作為“為君之臣”在實踐層面也為世人作出了榜樣。王陽明面對明中葉的政治腐敗、土地兼并、士風日偷,無論在民族矛盾還是階級矛盾方面,都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愛人”與“親民”的具體措施。根據《年譜》簡要述之:
十五歲,寓京師。“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策,胡人不敢犯。”
二十六歲,寓京師。邊事告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是年,先生學兵法,“每遇賓宴,當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二十八歲,會試,賜二甲進士,觀政工部,邊虜猖獗,遂向明孝宗疏陳邊務八事:“一曰蓄財以備急,二四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
三十九歲,升廬陵縣知縣。他根據“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的理念,“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社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
四十七歲,在贛南鎮壓農民暴動的同時,為了“掃蕩心腹之寇”,他立社學以移民風,舉鄉約以格心。再請疏通鹽法,建議“開復廣鹽”。如此,“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于貧民”,軍民皆受其利。
四十八歲,在江西,寧王朱宸濠謀反。王陽明督兵討賊,朱濠就擒。疏免江西稅。
四十九歲,在江西,面對天災人禍,為民請命,疏請寬租。“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王陽明升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鎮壓廣西田州、思恩少數民族暴動。心懷“愛人之誠心”,上疏曰:“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五十七歲,思恩、田州暴動平。王陽明反對“專有恃于甲兵”,主張“撫柔之道”:興學校,倡鄉約,撫新民,“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推選酋長,清查侵占土地,使其“實心向化”。在政權上,認為“凡為經略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
由上可知,王陽明無論在“破心中賊”的理論創新上,還是“破山中賊”的“廓清平定”上,都為明王朝建立了不世之偉績。在中國封建社會中,他是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的典范。
注釋:
(責任編輯 梁一群)
B248.2
A
1008-4479(2010)03-0100-06
2010-01-18
葛榮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