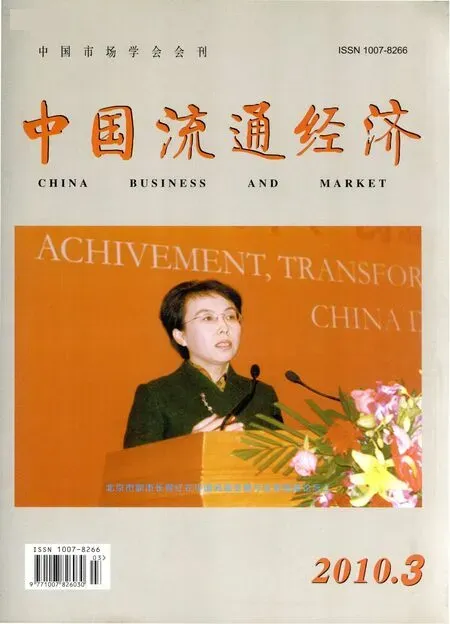中國政府采購范圍制度及其制度協調
劉小川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市 200433)
中國政府采購范圍制度及其制度協調
劉小川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市 200433)
我國《政府采購法》在采購資金、采購主體及采購對象范圍制度方面,由于相關概念界定不清,導致實際操作中出現了很多困惑。本文認為,應根據我國國情,借鑒發達國家政府采購范圍制度經驗,調整政府采購資金范圍,對財政性資金、混合型資金、地方債務及捐贈資金進行明確界定;合理劃分政府采購主體范圍,將國家機關、非營利事業單位、非法人團體組織列為一級采購主體,將營利性事業單位、法人團體組織、公共企業及委托一級主體的中介機構列為二級采購主體;對政府采購對象范圍進行明確界定,以避免實際操作中出現歧義;對政府采購資金、主體、對象范圍相互交叉的現象作出制度安排,并在《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中進行規范。
政府采購法;采購范圍制度;國際經驗;采購制度協調
一、現行政府采購范圍制度描述
一般而言,政府采購范圍包括三個層次的分類標準,即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主體范圍與對象范圍。我國現行政府采購范圍制度界定如下:
1.政府采購資金范圍指采購的資金來源、資金渠道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以下簡稱《政府采購法》),我國政府采購資金范圍是財政性資金。①對于中央單位的采購資金范圍,《財政部關于中央單位政府采購工作中有關執行問題的通知》②(以下簡稱《通知》)進一步明確:“財政性資金由財政預算資金和預算外資金組成,財政預算資金是指國家財政以各種形式劃撥的資金;預算外資金是指單位通過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采購性基金、政府間捐贈資金等獲得的收入,不包括單位各種其他事業收入。”
2.政府采購的主體范圍(或稱采購人范圍)指采購方的組織性質、組織類別等。我國《政府采購法》規定的政府采購主體是“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③《政府采購法》對采購人延伸范圍也進行了相應的界定。對于同質主體轉移的政府采購主體的規定是:“采購人的采購納入集中采購目錄的政府采購項目,必須委托集中采購機構代理采購;采購未納入集中采購目錄的政府采購項目,可以自行采購,也可以委托集中采購機構在委托的范圍內代理采購”。④對于非同質主體轉移的規定是:“采購人可以委托經國務院有關部門或者省級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認定資格的采購代理機構,在委托的范圍內辦理政府采購事宜。采購人有權自行選擇采購代理機構,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為采購人指定采購代理機構”。⑤
3.政府采購的對象范圍指采購目的物的屬性、形式等。我國政府采購的對象范圍指:“以合同方式有償取得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包括購買、租賃、委托、雇用等。其中,貨物是指各種形態和種類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設備、產品等;工程是指建設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構筑物的新建、改建、擴建、裝修、拆除、修繕等;服務是指除貨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購對象”。⑥
二、政府采購范圍制度存在的問題分析
現行政府采購實際操作中出現的眾多困惑,在很大程度上與政府采購范圍制度的法律規定過于寬泛和不甚嚴謹有關。
1.關于采購的資金范圍
(1)對財政性資金的界定過于籠統。從理論角度而言,財政性資金有廣義、中義、狹義之分。廣義的財政性資金不僅包括預算內資金、預算外資金,還包括與財政性資金相配套的單位自籌資金;中義的財政性資金指預算內資金和預算外資金;狹義的財政性資金僅包括預算內資金。我國《政府采購法》規定的資金范圍是財政性資金,而這個財政性資金的確切內涵僅在《通知》中提及,規定財政性資金由財政預算資金和預算外資金組成,而且這一規定僅適用于中央部門,對中央部門以外的政府采購資金并沒有約束作用,中央部門以外的政府采購資金范圍依然相當模糊,執行中隨意性很強。
(2)購買同一目的物的混合型資金界定模糊。混合型資金即采購資金中既包含財政性資金又包含非財政性資金。對于混合型資金是否應納入政府采購資金范圍,我國《政府采購法》沒有相應規定。《通知》規定,只要含有財政性資金就應實行政府采購,即我國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包括混合型資金。但由于《通知》沒有涉及財政性資金所占的比例,加之此規定僅適用于中央部門,對中央部門以外用于政府采購的混合型資金是否應納入政府采購資金范圍依然沒有進行規定。
(3)地方政府的債務資金是否納入政府采購范圍。我國《政府采購法》規定的采購資金范圍是財政性資金,而現實中地方政府用于興建大量公共項目的資金可能是通過銀行借款、向公眾發行債券或其他融資方式取得的,如果把這些地方政府的債務資金劃為非財政性資金,自然就不應屬于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但盡管這些資金不是來源于政府財政,卻需要政府財政對這些債務資金承擔最終責任,說到底就是要由納稅人來承擔,這與狹義的財政性資金并無本質區別。因此,對于地方政府的債務資金是否應納入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應當有一個明確的法律界定。
(4)各類捐贈資金的屬性界定不明確。以政府名義獲得的捐贈資金屬于預算外資金,我國對財政性資金界定籠統,并未明確這部分捐贈資金是否應納入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所接受的捐贈資金屬于非財政性資金,根據我國《政府采購法》相關規定的釋義,這部分捐贈資金可以不納入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但由于這部分捐贈資金屬于公共資金,與私人資金存在明顯區別,將之排除在政府采購資金范圍之外是否合理值得探討。
2.關于采購的主體范圍
(1)對事業單位的營利性與非營利性沒有界定。事業單位指國家出于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事業單位的范圍很廣,從社會功能看,可分為三種類型,即承擔行政職能的事業單位、從事公益服務的事業單位、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事業單位;從資金來源看,也可分為三種類型,即全額撥款型、差額撥款型、自負盈虧型。我國《政府采購法》僅僅規定政府采購的主體包括事業單位,卻沒有考慮事業單位的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導致實際操作中出現了困惑。例如,將營利性事業單位列入政府采購主體,其合理性就值得懷疑。
(2)團體組織界定模糊。我國《政府采購法》規定政府采購主體包括團體組織,而團體組織是一個內涵極廣的概念,包括社會團體、群眾團體、法人團體等多種類型,每種類型又包括很多種形式。因此,籠統地把所有團體組織都并入政府采購主體范圍的規定過于模糊,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團體組織的具體內涵。
(3)延伸采購主體的權責范圍不清楚。延伸采購主體(或稱二級主體)指政府采購的集中采購機構與有資格的采購代理機構。我國《政府采購法》規定,延伸采購主體也屬于政府采購主體范圍,但并沒有對延伸采購主體的權責范圍作出相應規定。
(4)接受財政性資金的非采購主體組織是否納入政府采購范圍。我國《政府采購法》僅僅規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為政府采購主體,而對于接受財政性資金的其他非政府采購組織,其采購主體地位如何界定并沒有相應的規定。如果不納入政府采購范圍,必將有一筆巨大的財政性資金長期游離于政府采購范圍之外,形成逃避行政監督的“避風港”;而如果納入政府采購范圍,又與現行法規相抵觸。
3.關于采購的對象范圍
(1)對貨物范圍的界定不全面。我國《政府采購法》對貨物的界定并不全面,沒有涵蓋技術、專利和以知識產權為標志的一系列無形資產以及新興的金融及其衍生產品等,而這些形態的產品在政府采購貨物中占有一定比例,并且其地位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
(2)對服務的界定模糊。我國《政府采購法》對服務采用了與貨物和工程不一樣的界定方式:對貨物和工程的界定采用的是概括、例舉法,而對服務的界定則采用了排除法。其表述為,除貨物和工程之外的采購即為服務采購。可見,這樣的界定并沒有實質性含義。
(3)工程的范圍標準不明確。我國《政府采購法》對工程的界定為“建筑物和構筑物”。一般來講,建筑物指供人們進行生產、生活或其他活動的房屋或場所;構筑物指人們不直接在內進行生產和生活活動的場所,所包括的范圍極廣。我國《政府采購法》對建筑物和構筑物的內涵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因此政府采購中工程的范圍標準是不明確的。
(4)混合型采購對象基本無界定。對于包含貨物、工程、服務中兩項以上的混合型采購對象,我國《政府采購法》中沒有明確的界定與劃分,所以在實際操作中無章可循。
三、有關國外政府采購范圍制度的規定
盡管國外政府采購范圍制度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但考慮到國際組織及西方國家的體制和采購形式與我國存在一定差距,對于這些制度,我們應當有鑒別地加以學習和吸收。
1.國外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
西方發達國家對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通常沒有明確的規定,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采購資金與政府采購主體的聯系非常緊密,只要界定采購主體,其主體的資金必然是財政性資金。也就是說,政府部門不存在持有非財政性資金的可能性。從財政理論來看,西方國家強調公共財政,政府采購作為公共支出的一個重要方面,其資金來源偏向于公共資金概念,而不是僅僅局限于狹義的財政性資金。因此,可以認為西方國家對政府采購資金范圍采用的是廣義的財政性資金概念。
由于西方國家政府采購資金范圍采用的是公共資金概念,其資金主要來源于財政預算,政府的自有收入很少。由此可見,西方國家的政府采購不存在我國政府部門所謂的預算外資金和混合型資金,因此中外有關政府采購資金范圍制度的界定必然存在差異。
2.國外政府采購的主體范圍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貨物、工程和服務采購示范法》第一章第二條對政府采購主體提供了兩種選擇方案:(1)采購實體指本國從事采購的任何政府部門、機構、機關或其他單位或其任何專屬機構,但……除外;(2)采購實體是指政府(或代表頒布國中央政府的其他詞語)中從事采購的任何部門、機構、機關或其他單位或其任何下屬機構,但……除外,另外頒布國可在必要時列入擬包括在采購實體定義之內的其他實體或企業或其類別。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在附錄中對政府采購主體進行了列舉,具體如下:中央政府、次中央政府(含聯邦制國家中的州和地方政府)和包括公用設施單位在內的其他采購單位(如供水、供電等公用事業單位,含受成員方直接或實質控制的單位及其指定單位),其中包括代理機構。
歐洲聯盟《公共采購指令》對政府采購主體的規定是:中央、地方和地方政府機關以及公法所管理的團體(如水、能源、交通、通信等領域內提供公用事業服務的私營公司)或由指令所規定的其他公共機關。其中,受公法管轄的團體應具備以下特征:(1)為滿足公眾利益這一特定目的而建立的,不具有工業或商業性質的組織;(2)具有法律人格的機構;(3)大部分受到國家、地區或地方政府資助的單位;(4)受國家、地區或地方政府管理監督的組織,或設有政府行政管理或監督委員會且其半數以上領導成員由其任命的組織。
3.國外政府采購的對象范圍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貨物、工程和服務采購示范法》規定,政府采購的對象范圍是:“以任何方式獲取貨物、工程或服務。”其中,貨物指各種各樣的物品(包括原料、產品、設備以及固態、液態、氣態物體和電力)還有貨物供應的附帶服務,條件是這些附帶服務的價值不超過貨物本身的價值;工程指與樓房、結構或建筑物的建造、改建、拆除、修繕或翻新有關的一切工作(如工地平整、挖掘、架設、建造、設備或材料安裝、裝飾、最后修整)以及根據采購合同隨工程附帶的服務(如鉆挖繪圖、衛星攝影、地震調查和其他類似服務),條件是這些服務的價值不超過工程本身的價值;服務指貨物和工程以外的任何采購對象。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第一條第二款規定了政府采購的對象范圍:“本協議適用于任何契約形式的采購,包括購買、租賃、分期付款購買、有無期權購買以及產品與服務聯合的采購。”另外,其附錄1中有5個附件,其中附件4為以肯定或否定方式列明的服務業,附件5專指建筑服務業。
歐洲聯盟《公共采購指令》認為,政府采購的對象范圍包括服務、貨物和工程,其具體范圍主要是從合同的角度對這三種采購對象進行界定。其中《服務指令》規定:公共服務合同指以金錢為對價,在服務提供者與公共當局之間簽訂的,以聯合國關于政府采購產品標準和服務分類術語所界定的服務提供為目的的書面合同;公共貨物供應合同指以金錢為對價,在供應者與公共當局之間簽訂的,涉及產品購買、租賃或分期付款購買(無論是否具有購買選擇權)的書面合同;公共工程合同指以金錢為對價,在承包者與公共當局之間簽訂的,以工程或建設項目的完成為目的的書面合同,工程指建筑或土木工程的成果,整個工程本身足以履行一項經濟或技術功能。可見,歐洲聯盟《公共采購指令》所界定的政府采購對象的特點在于:首先,界定了受指令調整的合同的定義;其次,指出了某些排除適用的具體情形和某些應當適用的特殊情形;最后,對相應的合同估價作出了規定。
四、我國政府采購制度范圍的協調思路
1.政府采購資金范圍的調整
(1)明確界定財政性資金。我國《政府采購法》僅僅規定了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是財政性資金,但由于財政性資金含義籠統,需要進一步對財政性資金的范圍加以明確界定,以免由于理解上的不同而產生歧義。根據前面的討論,我國政府采購中的財政性資金取中性概念較合理,即包括預算內和預算外資金。為確保具體執行中的準確性,有必要在《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中進一步對預算內和預算外資金加以界定,明確規定預算內和預算外資金具體包括的資金項目。
(2)混合型資金的界定。對于既含有財政性資金又含有非財政性資金的混合型資金,如果全部納入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那么當財政性資金所占比例很低時,顯然會違背《政府采購法》所規定的財政性資金的本質體現;如果不納入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那么當財政性資金所占比例較高時,大量財政性資金將游離出政府采購的范圍,不僅不利于財政性資金的監管,而且會給政府官員預留出巨大的“尋租”空間。從管理的便利性與操作的可行性來看,可以按照政府采購資金中財政性資金所占的比例,規定一個財政性資金占比的最低比例指標,對混合型資金作出量化界定。如果超出這個指標,混合型資金的項目應全部納入政府采購范圍;反之,是否納入政府采購范圍,可由采購人自主決定。
(3)地方債務及捐贈資金的界定。對于地方債務資金是否納入政府采購資金范圍,應視債權人的性質決定,如果債務最終由財政性資金來償還,則債務資金理應納入政府采購資金范圍。對于捐贈資金是否納入政府采購資金范圍,應視受贈人性質決定,如果受贈人納入了政府采購主體范圍,則其所接受的捐贈資金理應納入政府采購的資金范圍。因此,地方采購主體單位的債務資金均應納入政府采購資金范圍,地方公共企業與營利性事業單位之外主體的捐贈資金也應納入政府采購資金范圍。
2.政府采購主體范圍的合理劃分
根據我國國情,政府采購的主體范圍可分為一級主體和二級主體。可將國家機關、非營利事業單位、非法人團體組織列為一級采購主體,而將營利性事業單位、法人團體組織、公共企業以及受托一級主體的中介機構等列為二級采購主體。一級政府采購主體的采購活動,應全部納入政府采購系統;二級政府采購主體的采購活動,可視其財政性資金占比及采購對象的情況,決定是否納入政府采購系統。例如,公共企業采購主體地位的歸屬可視其財政性資金份額及社會影響程度決定,對于財政性資金所占份額較大和壟斷性較強的公共企業可部分或全部納入政府采購主體范圍。
3.政府采購對象范圍的明確界定
《政府采購法》明確規定政府采購對象為貨物、服務、工程,但對其具體內涵的規定比較概括,為了在實際操作中不出現歧義,有必要在《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中對貨物、服務、工程進一步加以細化,明確界定這些對象所包括的具體范圍。關于政府采購具體的對象范圍宜采用列舉法界定,特別是服務的采購范圍,可利用列舉法明確其具體包括的類別,使其內涵變得更加清晰,并與貨物和工程的范圍界定方式統一起來。
對于混合型采購對象,有必要在《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中制定分類標準,以明確混合型采購對象所屬的類別。分類標準可采用主輔功能標準、資金性質比例標準、產品行業分類標準等,或采用兩種及以上標準進行綜合判斷。
4.政府采購范圍交叉的制度安排
政府采購實踐中經常會出現政府采購范圍資金、主體及對象相互交叉的現象。對此,我們可以在《政府采購法實施條例》中予以規范。
(1)資金與主體的采購范圍交叉。當財政性資金與非采購主體交融時,宜按資金比例標準納入采購范圍,即設定一個財政性資金占比的底線,只要超過底線均應納入政府采購范圍;當采購主體與非財政性資金交融時,原則上應全部納入政府采購范圍。
(2)資金與對象的采購范圍交叉。當政府采購資金與對象交叉時,是否應納入政府采購范圍,其判斷相對簡單,即當財政性資金與非列舉采購對象交融時,必須納入政府采購范圍;當列舉采購對象與非財政性資金交融時,無需納入采購范圍。
(3)資金、主體和對象采購范圍的交叉。對于資金、主體和對象采購范圍三者交叉的情況,其政府采購范圍制度協調的原則應該是:資金屬性為首要考量因素,即只要使用財政性資金,原則上就需要納入政府采購范圍;主體屬性為次要考量因素,即在資金屬性確定的前提下,對于是否應納入采購范圍可進行適當的局部調整;對象屬性為從屬要素,可視政府采購資金屬性與主體屬性的情況進行歸類。
注釋:
①、⑥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第一章第二條。
②參見財政部辦公廳財辦庫[2003]56號文件。
③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
④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第二章第十八條。
⑤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第二章第十九條。
China'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cope System and the System Coordiantion
LIUXiao-chua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because of the unclear identification in the PRC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in terms of procurement capital,mainbody and object,there are so much misunderstanding in practice.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in the light the current situation,first,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cope system,adjust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apital,and clearly identify the fiscal capital,mixed capital,local debt and donation capital.Second,we should rationally identify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mainbody,make the state organs,NPOs and other entity without legal personality to be the first level procurement mainbodies and FPOs,legal entity,public entity and the intermediaries authorized by the first level entities to be the second level.Third,we should clearly identify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object.Forth,we should make system arrangement for the overlap scope of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apital,mainbody and object,and standardize that in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procurement scope system;international experience;procurement system coordination
F251.1
A
1007-8266(2010)03-0018-04
*本文受上海財經大學“211工程”三期重點學科建設項目資助。
劉小川(1956-),男,重慶市人,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財政理論、稅收制度。
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