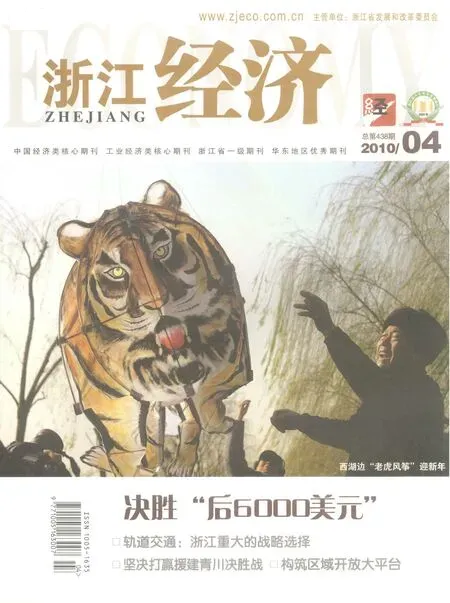“治大國如烹小鮮”
管仲,史稱管子,公元前725年出生于潁上(今安徽潁上縣)一個社會地位不高的家庭。年輕時三次求官被逐,經過商當過軍士。齊是一個位于山東半島上的小國,“區區之齊在海濱”,方圓百里封地,遠離周王室,開始建國,與戎狄為鄰。齊桓公之前的300多年間,“國小民窮諸侯多”。管仲當了國相以后,協助齊桓公理財治國安邦稱霸,立下了不世之功。
管仲在農業生產方面推行“均地分力”的政策。他在轄區內廢除了西周以來勞役地租形式的井田制,實行土地出租,把土地分給一家一戶的農民進行個體經營。這樣一來,不僅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民知時也——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其實質相當于今日我國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因為那時的土地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公有制。同時管仲還規定不準在農忙時節讓農民服勞役,征調牲畜,這樣既保證了農民不誤農時,又保證了農忙季節所需的畜力。
在賦稅政策上,管仲主張公平稅負,“相地而衰征”,按土地等級實行差別稅率,即“地均以實數”。把全國土地按不同土質和不同出產分“百而當一”、“十而當一”、“五而當一”等幾級,折成標準耕地面積征收土地租稅。在封建制度下,實物地租是直接生產者的全部剩余勞動和剩余產品,直接生產者在不同等級的土地上所創造的剩余產品量是有差別的。實行差別稅率,比不分土地等級一律征收相同租稅要合理得多,能激發直接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這種差別稅率可以說是管仲的創造。如果我們把“均地分力”與“相地而衰征”兩項政策結合起來看,便容易窺見管仲改革土地賦稅制度的獨具匠心,直至今日我們丈量土地和估算常年產量都還沒有超越他的政策框架。
在中國歷史上,管仲更是政策的創新者。“官山海”政策首創了鹽的專賣,寓稅于價,大幅度地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對于其他手工業,管仲還設計出一個“同業聚居,父子相承”的管理方案。換句話說,就是把行政管理、戶口編制和專業技術的發展結合起來。由于同一行業聚居在一起和子承父業,能夠耳濡目染,互補短長,“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智”,既保證各個專業后繼有人,又促進了同一行業之間的互相競爭和發展。今日國內之“金融一條街”、“電子一條街”即是當年管仲專業聚居思想的翻版,就是美國的硅谷也與兩千多年前管仲的思路有雷同之處。
管仲還非常重視財富分配與社會治理的關系。他說:“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分之”,即是說,天下不怕沒有財富,怕的是沒有人能使人民各專所業。他認為,分配關系要依禮義節制,“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背,貧富無度則失”。所謂“貧富有度”,就是要求貧富之間要有法度,若“貧富無度”就會造成混亂。他認為,民不可太富,但也不可太貧,太富、太貧都對國家不好。人若富了,就不受利祿的驅使;人若窮了,就不怕刑罰懲治,國家法令不能貫徹,人民所以難治,都源于貧富之不齊。怎樣才使貧富有度呢?國家要起主導作用,實行限制和調節政策。關于“貧富有度”的思想,在我國封建社會一直被稱為革命的口號,管仲在封建社會初期就具有這種思想是難能可貴的。這對于基尼系數已從0.31上升到0.45的中國現代社會來說,或許是一句振聾發聵的話語。
作為有文字記載的大理財家,管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人。他不但有實踐,有績效,而且還有比較系統的理論著作《管子》。管仲理財富國安民的歷史功績,得到了以一貫倡導“施仁政,反霸道”著稱的“大成至圣先師”孔子的充分肯定,更是一個極大的例外。孔子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