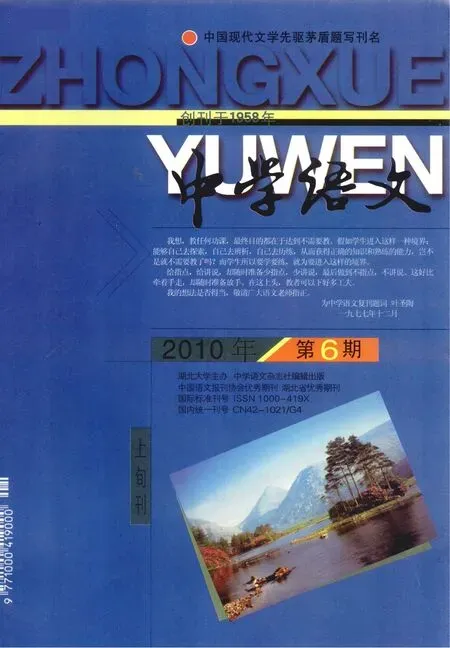人文的語文 生活的語文
劉 紅
一直以來,語文界都在進行關于語文學科的工具性還是人文性的爭論。雖然這場爭論至今仍在繼續,并且還不能有個結論,但語文學科的人文性這一理念卻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所接受,在語文教育教學實踐中得以逐漸推行。然而,到底什么是語文學科的人文性?站在語文學科人文性的立場上又該如何看待語文教育教學中的相關問題?在此就作些初步的探討。
一
人文主義,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代表新興資產階級文化的主要思潮。有兩方面的涵義:①指與中世紀神學不同的、以人與自然為對象的世俗文化的研究;②指貫穿于資產階級文化中的一種基本的價值理想和哲學觀念,即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它強調以人為“主體”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質、人的利益、人的需要、人的多種創造和發展的可能性。
什么是語文學科的人文性?
人文,①指詩書禮樂等,今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②指人事。
人學,以整體的人的本質及其生活世界為研究對象的學問。人學的主要內容有兩方面:人的本質,包括人的地位和人的發展問題;人的生活世界,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的歷史、人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問題。人學的分支學科有:人的自然科學、人的社會科學、人的精神科學。
人文科學,原指因人類利益相關的學問,以別于在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神學。狹義指拉丁文、希臘文、古典文學的研究;廣義一般指對社會現象和文化藝術的研究,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學、史學、法學、文藝學、倫理學、語言學等。
人道主義,關于人的本質、使命、地位、價值和個性發展等等的思潮和理論。
人文主義教育,亦稱“人道主義”教育。從人道主義出發,反對中世紀封建的、經院主義的教育,主張以“人”為中心,把人的思想感情從神學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強調尊重兒童個性。近代以來,或指追求個性發展的教育理想,或指相對于科學主義教育的人文主義教育思潮。人文學派,人與主義之一派,以養成高尚之趣味及優美之情操為目的。
從上面材料中,我們分析得知,沒有可以照搬照抄的有關“語文學科人文性”以解說或定義。但只要認真研究就可以看出,這些概念定義與“人文性”都有相關之處,它們大致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以整體的人的本質及其生活世界為研究對象的學問,即人文學科。二是關于人的本質、使命、地位、價值和個性發展等等的思潮和理論。前者更多的是指客觀的外在的事物,后者更多的是指對人的人文關懷,是一種認識和實踐。由此,我們可以為語文學科的人文性作出如下的解釋:
語文學科的人文性是指以富有人文精神、人文思想的語文教材為藍本,以富有人文氛圍的課堂為主陣地,以學生為主體,教師、學生積極參與的一種實踐活動。
二
前面我們對語文學科的人文性作了一個解釋,那么站在人文性的立場上又如何看語文教學實踐的相關問題呢?
1.人文性的教材觀
語文教材是我們進行語文教學,培養學生人文精神,提高學生人文素養的藍本。但我國幾十年一貫制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卻禁錮了師生的手足。教材的陳舊、落后已是有目共睹的問題了。有人曾經指出,在高一第一學期的語文課本中,真正從語文的角度來編選的篇目大約只有一半,其余一半則大體上是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來考慮的,而且還是五六十年代那種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即便是寫景抒情也是如此。更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總共28篇課文中,竟沒有一篇反映當代社會生活、議論精辟、文字精彩的作品。仿佛使用這本教材的老師和學生不是生活在21世紀初,而是生活在五六十年代的人。
這里所說的是高中語文舊教材的情況,而我們現在所用的新教材盡管有了很大的改觀,但仍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如果我們的教材都缺乏人文性,遠離蓬勃的社會生活,遠離充滿朝氣的學生,那我們又如何去完成人文精神培養的任務?我們的教材必須是語言精粹、與社會現實息息相關、適合學生生活、心理、生理實際的中外的典范文。正如北師大教授童慶炳所說:“我認為教材應該選那些風流蘊藉的作品。”(《不要錯過歷史機遇》)
另外,也要讓學生接觸一些非主流性文化、通俗文化。“保持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的適當張力,恰恰可以折射和補充主流文化、高雅文化的單一性,從而共同構成學校生動活潑、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態環境”(黃書光:《論中國基礎教育改革的文化使命與人格理想》)。
2.人文性的學生觀
學生是人,是活生生的人。我們的教育首先就是要還學生是人這一根本。楊叔子先生說:“大學的主旋律應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養高級人材,而非制造高檔器材。”(楊叔子:《是“育人”非“制器”——再談人文教育的基礎地位》)我們的中學的主旋律不也是“育人”嗎?既是“育人”就應先把人認識清楚。楊叔子先生指出:“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個性、有精神世界的,何況是高級人材;器是物,物是死呆呆的,再高級的器材,即使是高檔的智能化機器人,也不過只能具有人所賦予的復雜而精巧的功能或程序,其一切都不可能越過人所賦予的可能界限這一雷池半步。我們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記了人有思想、有感情、有個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人就是不器的君子,材就是不器的大道,這種人材就是不拘一格去創新的人材。”(楊叔子:《是“育人”非“制器”——再談人文教育的基礎地位》)
正確認識面向全體。面向全體不是用統一的標準、統一的模式培養學生達到相同的水平,而要讓每個學生都受到最適合他自身發展的教育。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前者講的是所有的人受教育的機會均等,后者講的是每個人所受的教育都要適合自身的特點,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優勢和特長。沒有針對個體的因材施教就談不上面向全體,而要使所有的個體都受到適合自身最佳發展的教育,就必須對學生分層、分類,以多樣化的教育模式供學生根據自身的特點來選擇。
重新認識全面發展。全面發展應該是,能促進學生特長發揮的各方面協調發展,允許有一定的短處,但各方面的因素最終組合成對學生本人而言是最有利于潛能發揮的綜合素質。一是各層、各類、各種專長的孩子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都能得到與之相適應的教育;二是對學生個體而言,應在德智體美等各方面都得到與其特長和優勢相應的發展,成為一個有健全人格、有發展潛能的人才。
3.人文性的課堂觀
(1)語文課堂是學生樂學善學的快樂天地。弗萊蕾曾把那種舊模式的課堂稱為“儲蓄的教學”。她認為這種教學是建立在這樣一些基本信條上的:“教師教學而學生被教導;教師無所不知而學生一無所知;教師思考一切而學生被(訓練)思考;教師侃侃而談,學生靜心聆聽;教師規訓,學生被規訓;教師決策并行使他的選擇,而學生只是服從;教師的行為成為學生行為的樣板;教師選擇進程與內容,學生不斷地適應;教師肆意鋪張其知識威信與專業權威,并站在解放學生的對立面;教師是學習進程的主體,而學生僅僅是客體。”(劉云杉:《課堂教學的“麥當勞”——一個社會學視角的檢討》)這些信條的實踐孕育并強化了一個富有壓迫色彩的小世界——課堂教學的小世界。這樣的小世界,學生會樂學、善學嗎?學生是否樂學、善學的關鍵在于教師,只要教師樹立大學習觀,把學生的學習看作是學生認識規律的形成過程,看作是學生智力、能力各因素協調發展的過程,看作是學生對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認識過程,那么教師就會設法激活學生的思維,調動學生的主動性,促使所有學生都能在原有的水平上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從而使他們感受到成功的喜悅。
(2)語文課堂是師生對話、交流、思想撞擊的平臺。學生是一棵有活力的、能夠自己主動吸納知識的小樹,而不是一個被動接受知識的容器。深入學生、了解學生、關心學生、把握學生,進而啟迪學生,點燃學生的智慧的火花。與學生建立動態的合作關系,讓以情感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師生關系,取代以知識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師生關系,與學生建立親密無間的師生關系,讓學生自覺、自主參與到教學過程中,從而把教育教學過程變成學生與自己共同獵求知識、發現真理的過程,使學生掌握人類認識事物的規律。
(3)語文課堂也是教師熱情參與、盡情投入、充分展現其生命活力的生活場所。學生不是工具,教師也不是工具;學生不是“器”,老師也不是制器的“匠”。老師這生命的主體,也不應在這毫無生命活力的地方長久地耗費青春和熱血。課堂是一方生命的園地,應有足夠的空間,足夠的自由度讓老師們去揮灑青春的熱情,把課堂變成有生命、有活力的生活場所。我們是語文教師,手持的是人類文化的瑰寶——文學。我們應能領會文學的大精神,應有文學的大精神。“要使人與人的心靠近一點,一個要飯婆子在雪地里的死亡,某個角落里的嬰孩的眼淚,都不應該漠視。‘外面進行著的夜,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不能將他人的生死攔在窗外,不能將一個人的孤苦無援當作笑話……”,要借助文學“使人的心靈得到溝通,使我們體會到他人有不幸,有苦惱,有無奈,有希望和絕望,有欲求和矛盾,有奮進和退縮,有歡喜和惆悵,那都是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氣息”(薛毅:《文學教育的悲哀——一次演講》)。就在這文學的大精神下,在這心靈的溝通中,語文老師得到了心靈的提升,課堂成了老師們生命的舞臺。
可見,語文學科的人文性一是指具有人文精神的教材,二是指具有人文關懷的教學。語文課堂是學生樂學善學的天地,是師生對話、交流、思想撞擊的舞臺,是教師熱情參與、盡情投入、展現其生命活力的生活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