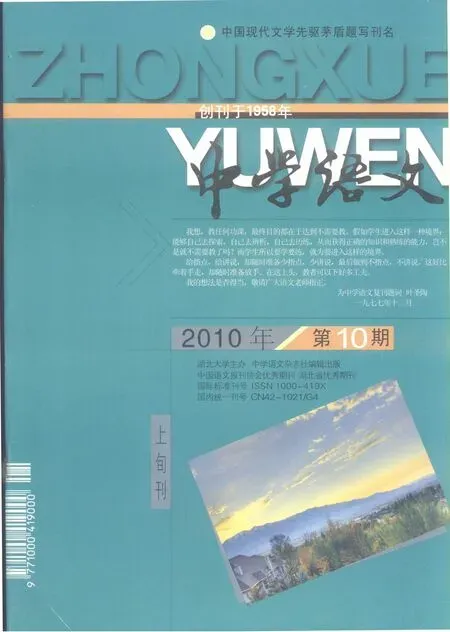試析語文選修教學探究性學習的探究角度
徐 靜
[作者通聯:江蘇揚州大學附屬中學]
試析語文選修教學探究性學習的探究角度
徐 靜
《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指出:應當讓學生“學習從習以為常的事實和過程中發現問題,培養探究意識和發現問題的敏感性。學習多角度多層次地閱讀,對優秀作品能夠常讀常新,獲得新的體驗和發現。學習用歷史眼光和現代觀念審視古代作品的內容和思想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明確指出了探究性學習的重要性。
選修教材作為重要的學習資源,為探究性學習提供了鮮活生動的素材。在實際教學中,教師應致力于合理開發和利用選修教材,盡可能地挖掘具有探究價值的內容,為學生開展探究性學習提供有價值的探究角度,讓學生既能關注教材,從教材中學習知識,又能培養自主意識和創新能力,逐漸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形成探究能力,落實選修課程的教學目標。
下面以蘇教版《〈史記〉選讀》為例,試析選修課教學中探究性學習的幾種探究角度。
一、平視教材——把教材當作研究對象
以往的學習,基本上是由教師誘導學生去理解教材,學生的認識都“統一”到教材的高度,學生很少有自我意識的活動空間。探究性學習就是要讓學生從被動地接受灌輸轉變為主動地探索研究,從知識的記憶,文章內容的再現轉變為問題的自主發現與解決。在選修教學中,教師要引導學生平等地審視教材,把教材當作學習研究,甚至批判的對象,敢于提出異議。有了平等審視的眼光,教材就更有研究的價值,探究能力才能得到更好的提高。
1.在矛盾處質疑
教材中常常有一些看似矛盾其實合理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教師應引導學生自己去發現矛盾所在,圍繞矛盾大膽質疑,并嘗試尋找解決矛盾的方法。如在教學《魏公子列傳》時有學生提出疑問:當侯嬴提出在信陵君到達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時,信陵君為何不加勸阻?這似乎和信陵君的“仁而下士”有矛盾。對于這種課堂上的即興生成,筆者及時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風尚、道德觀念來分析。學生通過探究了解到,在當時,守信用、踐諾言是人們的行為規范,“士為知己者死”,以死報知遇之恩是他們堅守不渝的信條。如果對以死相報知己的行動加以勸阻,就會被認為是不以知己相待的表現,是對人格的蔑視,是極不禮貌的行為。作為“仁而下士”、有三千余賓客的信陵君,對“士”的這些特點是一清二楚的,所以他不能勸阻侯嬴輕生死、重信諾的行動。相反,他認為侯嬴的以死相報將會進一步堅定自己在奪軍救趙的斗爭中必須成功、不能失敗的決心,也只有這樣,才對得起侯嬴。顯然,這樣的處理完全符合當時的社會風氣和人物的性格特征。這樣的探究,在解決了矛盾的同時,更拓寬了學生的視野,培養了學生的探究能力。
2.抓定勢點創新
要想擁有創新能力,必須先打破思維定勢。在探究性學習中,教師應引導學生挖掘教材中的思維定勢點,并對其中的問題進行反向思考,拓展時空,引導創造。如《趙世家》中屠岸賈這個人物歷來被認為是奸佞、惡魔的小人,學生基本上也是這種定勢的思維認識。教師可以從這個問題入手,引導學生去思考:能不能從歷史的角度去分析這個人物的行為?他的行為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一問激起千層浪,學生的好奇心和研究熱情被充分調動了起來。通過主動研讀課文、自主探究,學生認識到:從歷史的角度去看,這個人物掀起血腥屠殺的動機實際上是站在舊勢力立場上,對舊秩序的一種挽救,對“禮崩樂壞”的一次撥亂反正,因而他的殘暴行為不再令人匪夷所思,從這樣的角度去引導學生探究,打破了思維定勢,收到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3.于空白處延伸
閱讀文本因其“描寫性語言”存在某種程度的“意義不確定性”、“意義空白”,這種“意義不確定性”及“意義空白”在客觀上形成了文本的“空白點”,使作品充滿無限張力。在教學中,引導學生捕捉這些啟人深思、促人發展的“空白點”是尋找探究問題的最好切入點。如《項羽本紀》中項羽面對劉邦的圍追堵截,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劉邦安葬項羽后則是“泣之而去”。自古以來就是成王敗寇,緣何項羽在窮途末路時會大笑,而劉邦在安葬項羽后卻哭泣呢?教師可以從這里入手,引導學生展開聯想,探討這一“笑”一“哭”背后的心理狀態,甚至可以引導學生寫成小論文來展示探究結果。通過對這些空白點的挖掘,讓學生聯系上下文自讀自悟,想象思考,促進學生自身的感悟。
二、提供參照——增加教材的可研究性
作為探究性學習的載體,每一篇課文都有其獨特的價值。但是,在教學過程中,單篇課文可提供的研究要素有時會不夠充足,這就需要教師將與教材選文密切相關的內容引入課堂教學進行探究,或把一篇課文放到一個更大的參照系中,通過比較、分析,來探討普遍規律。這樣不僅有益于補充學習內容,更重要的是拓寬了學生的閱讀視野,激發了學生的閱讀興趣,引發其對學習材料進行有個性的思考與解讀。
1.提供與選文有關的文段進行探究
由于選修文本選文的限制,《〈史記〉選讀》遠遠不能涵蓋作為“史家之絕唱”的《史記》的精髓要義。所以,在很好地利用教材的同時,必須適當將教材沒有入選但與選文密切相關的文段引入課堂教學,通過適時的內容補充,拓寬學生的閱讀視野,啟發有個性的思考。在教授《淮陰侯列傳》時,我們發現教材選文選入韓信事跡的文字為服從專題要求,只是有側重地節選了“早年屈辱”、“井陘之戰”、“謀反被誅”這幾段,而對于想要全面了解韓信的為人,尤其是想要了解司馬遷對韓信之死的看法的讀者來說,這些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在教學中,筆者向學生補充《淮陰侯列傳》記述的其它相關內容,提供了關于“蒯通游說”選段供學生思考探究,拓展了學生的視野,引發了學生積極的思考。
2.提供與選文有關的評論進行探究
前人對《史記》各方面成就的研究非常廣泛,利用這些前人的評論來指導學生進行深入探究,讓他們自己去嘗試理解、評價,是非常有效的。比如在教學《刺客列傳》時,筆者就補充歷史上對荊軻的評價:北宋蘇洵非議荊軻之行曰:“始速禍焉。”南宋鮑彪為《戰國策》作注說:“軻不足道也。”朱熹更認為“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而《史記·刺客列傳》結尾云:“其立意皎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左思的《詠荊軻》稱頌他“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陶潛說荊軻“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有了這些補充內容,學生嘗試評說前人的意見,并對“荊軻刺秦王”作出了不少頗有見地的評價。
3.提供其他選文進行比較探究
在文本閱讀中,可以提供另外幾篇選文,把課文放到一個更大的參照系中,通過比較,就某一方面進行探究,領會相互特點,尋找規律性的東西。問題的探究可以多層面展開,如從作者思想入手,讓學生比較《太史公自序》、《屈原列傳》、《項羽本紀》三篇文章,通過對司馬遷的忍辱偷生,屈原的以死明志,項羽的末路悲歌來探究司馬遷的生死觀;從人物形象入手,《史記》中的很多篇目都涉及到悲劇命運的人物,有近一半的傳記是專為悲劇命運的人物而立的,一部《史記》大約寫了一百二十多個重要而又具有不同悲劇命運的人物,讓學生比較《屈原列傳》、《李將軍列傳》、《項羽本紀》三篇選文,探究司馬遷悲劇性人物的特點;又如從藝術特色入手,《史記》向來以“善序事理”見稱,善于在敘事中把事物的內在聯系和屬于事物規律性的東西——即事物之“理”給揭示出來,讓學生把《項羽本紀》、《刺客列傳》放在一起比較,探究它們在敘事藝術上共有的“善敘事理”的特點;再如從語言風格入手,司馬遷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語來表現人物性格,讓學生結合《高祖本紀》、《項羽本紀》和《淮陰侯列傳》中高祖的語言,體會其性格特點。
三、引申延展——重視教材的可延續性
上面兩類探究角度,都是用研究的眼光和意識研究教材本身,也即主要通過研究手段更好地理解教材,提高學科素養。我們可以讓學生嘗試由課內向課外擴展,由課文理解向課題研究延伸。比如在學習《廉頗藺相如列傳》時,可以讓學生研究“《史記》中保留下來的成語及特點”、“《史記》精彩對白賞析”等話題;在學完《高祖本紀》和《項羽本紀》后,可讓學生圍繞“性格影響命運”進行寫作,有助于引導學生追求人格的完善;在進行專題教學時,可設計一些探究性的話題:如“從《史記》描寫的人物形象談史家‘實錄’精神”、“唐代傳奇與《史記》的淵源關系”、“探尋司馬遷的理想人格”等。
上面提出的三種不同層次的探究,教學中要循序漸進地展開。應當注意,這三種探究角度之間也不是孤立的,彼此間存在交叉。在教學中,何時采用何種探究角度,教師應當深思熟慮,盡量為探究性學習鋪設更多、更廣闊的道路,使學生在“主動”中發展,在“探究”中創新,培養發現、探究、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開創語文選修教學新局面。
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制訂:《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版。
②丁帆、楊九俊主編:《〈史記〉選讀》,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
③丁帆、楊九俊主編:《〈史記〉選讀教學參考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版。
④可永雪:《〈史記〉文學成就論說》,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湯正康:《對探究性學習的探討》,《吉林教育科學(普教研究版)》,2001年第2期。
[作者通聯:江蘇揚州大學附屬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