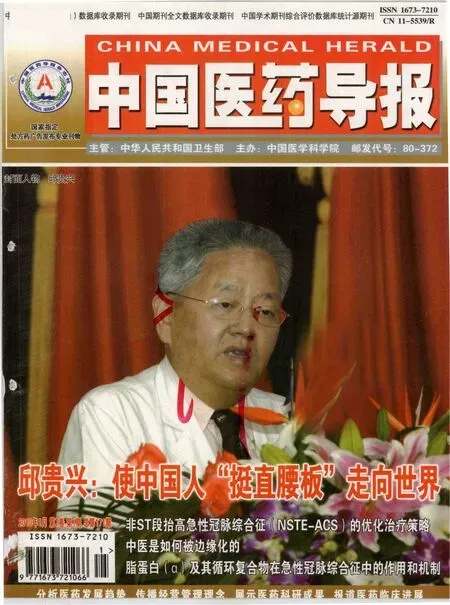中醫是如何被邊緣化的
梁華龍
(河南中醫學院,河南鄭州 450008)
中醫學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科技文化,已經歷時2000余年,在歷史的長河中,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數度輝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曾幾何時,中醫學就成了“玄學”、“偽科學”,一門有著悠久歷史、系統理論、明顯療效的無創或微創的綠色醫學,在西學東漸的一個多世紀時間里,讓創造了中醫學的先賢們的子孫給邊緣化了,那么,中醫學是如何被邊緣化了呢?
1 政策規定的行政邊緣化
執業醫師資格考試是醫生執業的通行證,沒有執業資格的人的所有醫療活動,都屬于非法行醫,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執業醫師資格要通過國家統一組織的資格考試來獲取。西醫的醫師資格考試全部考西醫內容而不涉及中醫,中西結合醫師資格考試要考一半西醫知識一半中醫知識,而在中醫師資格考試中西醫內容也占據了40%,但在臨床中規定不能跨范圍執業,即中醫執業醫師不能從事西醫的臨床工作。偉人毛澤東很早就倡導中西醫結合,要西醫學習中醫,而我國的執業醫師資格考試政策則規定中醫必須學習西醫,而西醫可不必學習中醫。醫師資格考試是威力極強的指揮棒,這種考試規定,就決定了中醫要同時學好兩套醫學理論,無形中降低了中醫理論知識在中醫界的重點地位。既然提到中西醫并重,為什么規定中醫執業醫師要考西醫內容,而西醫執業醫師不考試中醫內容,為什么中醫職業醫師不能只考試中醫內容呢?考了西醫內容又不能使用,為什么要考呢?
新藥的評定和審批,是保證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的關鍵,必要的研究手段和指標檢測是體現安全性、有效性的基礎,但中藥和化學藥品不論其藥源、理論都是截然不同的,以臨床療效為基礎的中藥方劑,是經過長期經驗積累并經過反復驗證的,新藥審批中要求中藥也必須在實驗室中進行藥理藥效實驗,大量的臨床資料必須采用小白鼠實驗,而中醫的證候多是綜合性的,是無法在小白鼠身上進行復制的,在小白鼠身上有效的未必在人身上就一定有效,所以實驗室中的藥效實驗的規定本身就是對中醫理論和中藥療效的否定。對于成分的檢測,也是從另一角度否定中藥的療效,中藥是按照其四氣五味,性味歸經來使用的,每一單味中藥,都有非常多的成分,而這些成分之間是相互協調而起治療作用的,更何況復方,是講究配伍的,相須相使,相輔相承。單一成分的測定,并不能確定該藥或該方的療效,甚至所測定的成分在該藥中恰恰是次要的甚或是無用的。將臨床驗證有效的藥物再用動物實驗去證實,測定整體性作用的藥物中的某一成分,否則就是無效或是假藥,這正是相關規定將中醫邊緣化的例證。
高等院校在發展中盛行一種被稱作“五子登科”的風氣,即“改名子、擴院子、爭位子、調班子、借票子”,名字響、院子大、位子高、貸款多就會成為同行業的龍頭老大,中醫院校也不例外。在改名大學和申博過程中,SCI、EI等收錄論文的數量占著較大比重,而中醫學論文基本不在收錄之列;國際刊物發表的論文比國內權威刊物發表的論文所占的比重要大得多;國外原版教材的編寫、使用也可以積分。根在中國的中醫學,卻使用國外非母語語種的教材,筆者不知道某些連中文版中醫理論都弄不懂的專家、學者,用非母語中醫教材,其結果將會如何。由于客觀條件和學科特性,中醫學的這些方面的積分很難達到標準,這些政策規定一定程度上導致中醫學邊緣化。
2 中醫教育的自我邊緣化
中醫院校自建立之初,就院校的名稱而言,即是對中醫的邊緣認識。中醫學是醫學,西醫學也是醫學,而院校的建立將西醫院校稱為“醫學院”或“醫科大學”,而中醫學的院校就加上“中”字,其實中醫也是醫學,也是世界性的醫學,只不過她的發展重點是在東方,除中國之外,還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大部分的東亞和南亞國家。“中醫學院”這種稱謂就已經把中醫學排斥在主流醫學之外,可以說從中醫院校教育的一開始,中醫就隱含著被邊緣化的危險。
中醫院校大多設立了中藥系(或學院),而此中藥系(或學院)與中醫學中的中藥基本不相干,中藥之所以稱為中藥,必須在中醫理論指導下栽培、采收、整修、炮制、配伍、煎服,調護,方可稱之為中藥,否則只能是天然藥,而天然藥在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存在。現在的中藥專業除了 《中藥栽培學》、《中藥炮制學》和《中藥學》等極少的課程與中醫中藥有關外,其他的課程基本與“中藥”風馬牛不相及。而從事中藥教學的大部分專業人員,基本成為化學專業,有的甚至附和一些攻擊中醫的觀點,對中醫頗有微辭。其實隸屬于中醫的中藥學,是和中醫理論血脈相連的混合體,現狀中的中藥專業從課程設置到研究內容,從教學計劃到師資配備,從理論教學到實驗教學,已非中藥原貌,而是天然與化學的混血兒了,中藥概念的偷換,給一些攻擊中醫的人以口實,“廢醫存藥”的論調難道中醫藥界自身沒有責任嗎?
在《中國中醫藥報》教育科技專欄中,筆者為中醫教育算了幾筆賬,其中,關于中醫院校的課程設置和中西醫學時比例,依據“中醫本科教育規范(標準)”規定中醫專業要進行的課程設置,除了思想品德教育、人文素質教育、行為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以及醫學倫理學等課程外,尚有5大類30余門課程,均不屬于中醫學科的專業課程,但這是跟著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考試規定的指揮棒轉的,由不得院校自己做主。
況且中西醫本就是兩套不同的理論體系,從其理論的建構形成到思維方法,尤其是臨床運用截然不同。作為宏觀的、統一的、整體的中醫學理論,是治療患病的人,調整活動的人體生命;而作為微觀的、割裂的、單一的西醫學理論,所治療的是人的病,修理靜止的組織器官,兩套本應花費等同時間學習的理論,合而為一在五年中學完,豈不是煮夾生飯嗎?
近年來,中醫院校的高層次教育發展迅速,若從數據上看,形勢喜人,但從實際上考察其教育質量,尤其是對中醫理論及臨床技能的掌握,不能不讓人擔心,社會上流傳的“碩士不碩,博士不博”,從中醫專業上看,“博士不如碩士,碩士不如學士”,盡管這些說法有些未免矯枉過正,但中醫高層次教育的現實也確實不容樂觀,碩士和博士教育的課程設置大多以外語課、計算機課、統計學以及西醫課程和實驗占據了大量時間。粗略統計,中醫碩士用于學習以上課程和實驗需三年中的兩年半,而中醫博士幾乎用到三年,對于中醫的基本理論和知識,雖然在某方面有所深入,但其他的知識基本被忽略,甚至忘記,所以還不如本科期間的全面學習,碩士、博士不會望聞問切,尤其不會診脈的大有人在,這就給社會傳遞了一個錯誤的信息,即高層次中醫教育尚且以西醫和實驗為主,可見中醫的本科教育現狀如何,這也是中醫教育自我邊緣化的一剪縮影。
3 中醫科研的人為邊緣化
中醫科研從一開始,就定位在非“中醫研究”的錯誤方向上,因而也成為了部分人非難中醫的口實,是人為地將中醫邊緣化的一個主要方面。
3.1 判斷標準錯誤
用西醫生物醫學的觀念、理論、方法,把中醫作為研究對象,在“西化”中對其進行改造,是近半個世紀中醫科研工作的主流。而在當代,把自然科學中物質的特殊屬性、結構和形態的學說,作為生命科學領域的絕對信條和唯一標準,是造成這一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中醫科研的判定標準,基本上遵從西醫藥的科研規范和要求,一切均按現代醫學的生化、生理、病理等具體實驗室量化指標來執行,始終未能形成真正符合中醫科研自身發展規律的標準體系,這一點在中藥的研究中尤為突出。然而,中、西醫學間存在的巨大差異,決定了西醫學的科研方法并不適用于中醫學的科研。
3.2 科研方法不當
中醫的科研,尤其是一些大項目,大多采用如下流程:摘錄文獻,斷章取義,自設跳板,為自己科研找依據;歪曲觀點,肢解學說,閹割在先,以期古為我用;制作模型,設定指標,棄中就西,為求社會認可。由于動物模型與中醫證候的不相符,檢測指標與癥狀表現的無對接,提取成分與臨床療效的相背離,終于出現了實驗不“實”、假設更“假”,結果是欲西非西,遺人笑柄。大部分對中藥的研究是分析單味藥的化學作用,基本是用西藥研究的辦法去研究中藥,這種用現代技術研究、分析和證實中醫藥的正確性,從根本上忽視了中醫藥學的基本規律,抹殺了中醫藥與西醫藥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醫療體系的本質區別,尋找中藥“有效成分”的實驗,導致純正的中醫藥科研很難拿到國家科研課題。中醫藥科研走上了一條“中醫西化”的不歸路,采用西方唯科學主義的實踐研究中醫發展,盲目改造中醫傳統,簡單模仿西藥,用西醫驗證中醫理論的正確性,誤以為中醫理論就是從實驗室里產生的,導致中醫科研嚴重脫離臨床實踐,作為國粹的中醫藥日漸式微。
3.3 學術認同偏差
據了解,2005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173個中醫藥項目中,理論研究占24%,臨床研究占57%,有效成分研究占18%,其他占1%。在1998~2004年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的25項中醫藥成果中,多為天然藥成分提取或鑒定,有的屬西藥成果,有的屬中西醫結合研究成果,真正按中醫藥規律進行的臨床研究極少。學術界對中醫藥現代化的認識較為片面,即過分強調研究中醫藥的所謂“實體本質”、探求天然藥的有效成分,過分強調對微觀結構的認識、注重分離提取,從而忽視了中醫藥學的基本規律,注重用西醫藥學的分析還原的方法研究中醫藥。這種對現代化的片面認識,缺乏發展性和創造性,并把研究重點放在物質的研究上,忽視了中醫自身的研究,存在著方向上的偏差,因而很難取得突破。如果真能夠按照國家科技部原副部長程津培所說:“加強中醫基礎理論研究,要樹立發展的觀點,重視中醫理論的整理、歸納與提升,重視從中醫臨床實踐中總結規律,重視中醫療效評估標準、規范的研究”,中醫研究也許會有所突破。
4 中醫醫療的社會邊緣化
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都是為了治病救人,在臨床實踐中采用兩種診斷和治療方式,發揮中西醫各自的優勢,相互取長補短,這才是中西并重的原意。中醫西化主要還是中醫院的辦院方向出現偏差,服務方式偏離中醫服務的軌道,導致這種結果主要是經濟利益的驅動。經營強調市場化,利益追求最大化,評價強調效益化,年底看誰收入高,所以收益高但并不一定療效好的西醫化傾向,自然而然就成了大部分中醫院的建設目標。
4.1 中醫醫院西醫化
1994年國家衛生部頒布的《醫療機構基本標準(試行)》中,“一級中醫醫院標準”規定基本設備18種,除中藥煎藥設備與針麻儀兩種外,其余16種全是開展西醫必備的設備,計有心電圖機、洗胃機、呼吸球囊、吸引器、必備的手術刀包、顯微鏡、離心機、分光光度計、高壓滅菌設備、X光機、婦科檢查臺、給氧裝置、紫外線滅菌燈、電冰箱、各類針具、蒸餾水裝置。一級中醫醫院標準如此,二級、三級中醫醫院的設備配置標準就更可想而知。很多中醫院以引進國外大型診療儀器設備為驕傲,而中醫僅作為點綴性的象征,其臨床收入中,也是西藥和中成藥的收入占70%以上。以至于招聘人才時,寧肯要西醫學院的本科生,也不要中醫院校的研究生。疾病的西化處置和西藥的競相應用,雖然給醫院能夠帶來不菲的效益,但中醫院的辦院宗旨和服務方向都偏離了應有的軌道,將中醫院辦成了以西醫為主中醫點綴的中西醫聯合醫院或者辦成了三流的西醫院。導致中醫西化,偏離中醫辦院方向,脫離中醫服務軌道的原因,主要是經濟方面的,醫院強調市場化,而在利益的驅動下,什么獲益醫院就愿意做什么,而西醫的獲利一般要高于中醫很多。
4.2 特色特長不相符
大部分中醫院存在有三個“難見”,即“難見中醫特色、難見中醫特長、難見中醫大家”,總之中醫院不姓“中”。其不姓“中”的程度,已經嚴重到了即使是在中醫藥特色保持最好的中醫院,只有少數的中醫醫生能運用中醫思維來進行辨證論治,一部分中醫醫生不會診脈,甚至連中醫的望聞問切等基本診治手段都不熟練,也不會辨證施治,甚至不會開湯藥處方。代表中醫人“神、圣、工、巧”智慧的望、聞、問、切診法就用進廢退,只剩下一個西醫化的“問診”,中醫醫院以能夠開展先進的手術引以自豪,以“搭橋”、“移植”“開顱”作為“特長”。而中醫在療法和療效上的特長難以發揮,沒有了中醫的特長,又哪來中醫的特色呢,沒有了中醫的特色,中醫院還能姓“中”嗎?中醫院不姓“中”了,那中醫學自然就被邊緣化了,有為才有位,中醫連在中醫院都成了配角,在社會上的位置就可想而知了。
5 宣傳媒體的炒作邊緣化
個別媒體,包括報刊、廣播、電視、尤其是網絡都存在追求利潤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問題;媒體自律意識差,追求時效性,損害真實性;監督管理機制不完善,對違規行為只批評不處理等。若把媒體的目標建立在名、利的基礎上,其失實、歪曲、作假就會油然而生,從“貝加爾湖水要引入北京”到“廢紙箱做包子餡”,從“告別中醫”到“韓醫申遺”,不同版本的虛假新聞之所以頻頻出現,難以禁絕,源于市場利益的驅動“蒙住”了部分媒體及其從業人員的眼睛。
5.1 夸大事實,推波助瀾
“新聞失實”的實質不是媒體從業者的水平問題,而是態度問題。在媒體上轟動一時的“告別中醫”簽名活動,最終也不過只有區區200余人,可一開始媒體就揚言達“萬人”,后經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公開辟謠。而所謂“韓醫申遺”的報道,也被證實為“失實”,事實是韓國將《東醫寶鑒》申報世界記憶工程。“告別中醫”的虛假新聞,正是“唯眼球論”指導下媒體“制造熱點”的典型案例。由于中醫與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加之目前中醫藥發展步履維艱,“中醫廢存之爭”確是讀者關注的熱點。個別媒體為讓熱點更熱,人為夸大簽名人數以及申報事件的性質,制造轟動效應。更多的媒體則對這樣“抓人”的新聞也是“寧信其有”,推波助瀾。因此,“告別中醫”的謠傳才成為“新聞報道”四處流布。
5.2 崇洋媚外,衷西非中
個別媒體對于外國哪怕是很小的事件也會大肆吹捧,而中國的事件則不愿多費一點筆墨。20世紀90年代,美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對1988年上海以中醫藥為主治療乙肝重疊甲肝與1983~1988年美國本土西醫藥治療同類疾病的死亡率進行了統計對比,結果中美的死亡率之比是“1∶234”,顯示了中醫藥在該病治療中的作用,可見于社會媒體的報道卻寥寥無幾。“喝雞湯可預防感冒”這個被中國沿用了多少年的單方,最近卻有多種媒體報道說美國學者研究發現“喝雞湯可預防感冒”。僅青霉素過敏導致死亡的人數每年就有成千上萬,可除了醫學雜志有過專業性報道外,社會媒體極少見到相關報道。可因服用龍膽瀉肝丸不當而導致腎衰的個案,卻引來了多種媒體的爭相報道。中醫藥只要稍微出現一些事故,媒體就會狂轟濫炸,而西醫藥諸多的毒副作用,媒體卻見怪不怪。
5.3 指鹿為馬,張冠李戴
中醫藥的毒副作用從有記載的那天起,就一直在提醒著人們,從最早的《周禮·天官》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到俗語中的“是藥三分毒”,中醫自始至終就將中藥稱作“毒藥”,從未否認過中藥的毒副作用,真正的中醫何時說過“中藥無毒副作用”?筆者1994年就出版了《中藥的毒副作用及其處理》一書,并在《健康報》掀起了中藥毒副作用的大討論。“中藥無毒副作用”是媒體自己說的,反過來又以此攻擊中醫。一些無照行醫、鼓吹秘方祖傳,甚至一些退休的西醫或對中醫一知半解的人濫用中藥,出了醫療事故就歸罪于中醫,歸罪于中醫學的古老、歸罪于中醫學不能落入西方科學的窠臼,歸罪于院士讀不懂的中醫,這是對祖國醫學的歧視,是數典忘祖,是媚外和自殘的一種病理心態。有了這些欲加的莫須有之罪,中醫學被邊緣化,已在情理之中了。
總之,針對中醫邊緣化的問題,筆者希望社會各界廣泛關注,正確評價中醫。中醫藥系統更要加強自律,正確地傳承;教學機構要建立完善的中醫教育機制,加強中醫人才培養。政府更應重視中醫的發展,應將其作為國粹發揚光大,為其發展開拓一條廣闊、深遠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