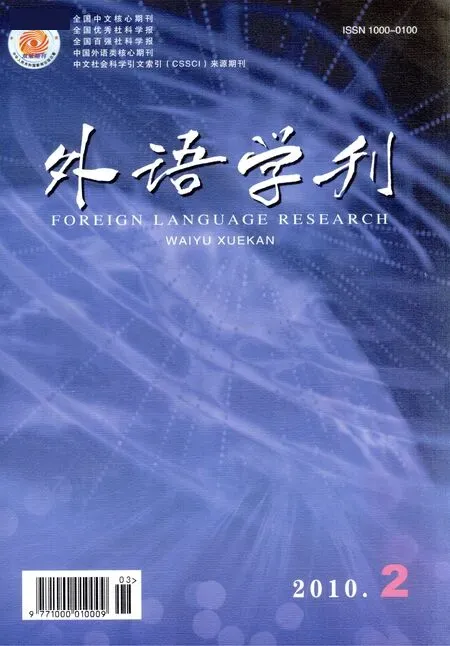人自稱、人被稱與物被稱*
錢冠連
(廣東外語外貿(mào)大學(xué),廣州510420)
1 理論取向
說哲學(xué)的分析潮流早已結(jié)束,說“形而上學(xué)已經(jīng)恢復(fù)了它(在哲學(xué)中)的中心地位”(蘇珊·哈克2004),都威脅不了本文的研究進(jìn)路,因為它是后語言哲學(xué)的思路。后語言哲學(xué)與經(jīng)典語言哲學(xué)的相同之處在于:(1)從語句入(in linguistic terms);(2)從世界出(達(dá)至世界與思想)。后語言哲學(xué)區(qū)別于經(jīng)典語言哲學(xué)的特點在于:(1)吸取西方語言哲學(xué)(包括分析傳統(tǒng)和歐洲傳統(tǒng)兩部分)的營養(yǎng),不炒作它的老問題,而是節(jié)外生新枝;(2)生出什么新枝呢?從日常社會生活中尋找一個一個具體的語言問題,從詞語分析(形而下)找入口,從世界與人的道理(形而上)找出口,管住入口與出口,同時讓選題與風(fēng)格多樣化;(3)重視漢語語境,實現(xiàn)西方語言哲學(xué)的本土化。
2 相關(guān)論證
針對同一性(identity)a=b(the Morning Star is the Evening Star)同a=a之間的不同,Frege指出了呈現(xiàn)方式(the mode of representation)與認(rèn)知內(nèi)容(cognitive content)的不同。尋此不同,他認(rèn)為,涵意并不就是指稱(Frege 1952);可以解釋一物兩名甚至三名現(xiàn)象,但不能解釋本文所發(fā)現(xiàn)的人自稱的(超)多名(多變體)現(xiàn)象。補(bǔ)上這個漏洞,是生成本文的直接推動力之一。
一則流傳在海外華人中的笑話——“洋人求學(xué)記”是本文的主要語料:有一個老外為了學(xué)好漢語,不遠(yuǎn)萬里,來到中國,拜師于一位國學(xué)教授門下。第一天老外想挑一個簡單詞匯學(xué)習(xí),便向老師請教英語I在漢語中應(yīng)該如何說。
老師解釋道:
(在)中國……當(dāng)你處在不同的級別、地位,“I”也有不同的變化,就像你們英語中的形容詞有原級、比較級、最高級一樣。
比如,你剛來中國,沒有地位,對普通人可以說 :“我、咱 、俺 、余 、吾、予 、儂 、某 、咱家、灑家 、俺咱 、本人、個人、人家、吾儂 、我儂 。”
如果見到老師、長輩和上級,則應(yīng)該說:“區(qū)區(qū) 、仆 、鄙、愚 、鄙人、卑人、敝人 、鄙夫 、鄙軀 、鄙愚、貧身、小子、小可 、在下 、末學(xué)、小生、不佞、不才 、不材 、小材、不肖、不孝、不類 、走狗 、牛馬走、愚小子、鄙生、貧生 、學(xué)生 、后學(xué) 、晚生、晩學(xué)、后生晚學(xué)、予末小子、予小子、余小子。”
等到你當(dāng)了官以后,見到上級和皇帝,則應(yīng)該說 :“卑職、下官、臣、臣子 、小臣 、鄙臣、愚臣、奴婢 、奴才、小人、老奴、小的 、小底 。”
見到平級,則可以說:“愚兄、為兄、小弟、兄弟 、愚弟 、哥們 。”
見到下級,則可以說:“爺們、老子、大老子、你老子、乃公。”
如果你混得好,當(dāng)上了皇帝或王爺,則可以說 :“朕 、孤、孤王 、孤家 、寡人、不轂。”
如果你不愿意當(dāng)官,只好去當(dāng)和尚、道士,則應(yīng)該說 :“貧道 、小道、貧僧、貧衲 、不慧、小僧 、野僧 、老衲 、老僧 。”
最后一點必須注意,一旦你退休了,便一下子失去了權(quán)利和地位,見人也矮了三分,只好說:“老朽、老拙 、老夫、愚老 、老叟 、小老、小老兒 、老漢 、老可、老軀、老仆、老物 、朽人 、老我 、老骨頭 。”
上面一百零八種“I”,僅僅是男性的常用說法。更多的“I”明天講解。
老外聽了老師一席話,頓覺冷水澆頭,一個晚上沒有睡好覺。第二天一大早便向老師辭行:“學(xué)生、愚、不材 、末學(xué) ,走 。”退了房間 ,訂了機(jī)票,回國去了。
在分析之前,須要說明,上述笑語作者以漢語“我”與英語形容詞的三級比較,不妥。
任何一個說話人都可以用第一人稱“我”指稱自己,即把自己當(dāng)做一個世界對象來指稱。這便是人自稱。物被人稱叫做物被稱,結(jié)果出現(xiàn)事物的名字,與人自稱形成對立。既然是任何一個說話人,“我”的指稱對象就是暫時的、變動不居的(Quine 1960:173)。每換一個人自用“我”于己,指稱對象就換一次。這種“自我中心特稱詞”(egocentric particulars)(Russell 1940:116)的外延與說話人及其時空位置有著相對性,并有賴于說出它們時的語境。“它們會影響包含有它們的命題的真,因為這樣的命題不能有恒常的真值。可以說它們有外延而無內(nèi)涵。”(尼·布寧 余紀(jì)元2001:286)但是,我們會發(fā)現(xiàn),漢語“我”的每一個變體除了有所指(外延)外,還有內(nèi)涵。正是因為“我”的每一個變體都有內(nèi)涵,才有這篇論文所討論的問題。
漢語從古到今出現(xiàn)了大量的“我”的替換詞(變體,以下簡稱“‘我’變體”),它們可能嚇退一個現(xiàn)代初學(xué)漢語的外國人,卻大受幾千年漢語母語使用者的歡迎。這說明一個問題:在稱呼我自己時,僅“我”這一基本詞(字)不足以介紹我。猜想其原因,恐怕是“我”還不足以張揚(yáng)人性,不能給出社會身份與身價、社會地位與等級的種種附加信息。
以上語料表明,人自稱(本文只涉及漢語使用中的男性)怎樣使用豐富多彩的“我”變體,同語境密切聯(lián)系:面對普通人的時候;見到老師、長輩和上級時;自己當(dāng)了官以后見到上級和皇帝時;見到平級時;見到下級時;自己當(dāng)上了皇帝或王爺時;自己當(dāng)了和尚、道士時;一旦我失去了權(quán)利和地位時;等等。這一切都是為了增加“我”出場(我存在)的凸顯度。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需要對自身生存狀態(tài)的自關(guān)心。
漢語“我”變體是支持英美語言哲學(xué)家所謂“第一人稱優(yōu)先性”(preferentianl first person)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jù)。從認(rèn)識論角度來說,人自稱相對于物被稱所具有的優(yōu)先性,普及到一切人稱對(一切)物稱的優(yōu)先性,反映出人類在認(rèn)識世界的過程中基本上都遵循著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循序漸進(jìn)的認(rèn)知路徑。
在使用“我”之前,我只是不被人注意地存在著。“我”名我,我便出場與現(xiàn)身了。“我”才能使我自己出場與現(xiàn)身。筆者曾經(jīng)指出,“我們以言說使世界中的一物(實體或虛體)現(xiàn)身的同時,也使自己在世上出場或現(xiàn)身……人在世上的出場比物的出場更具有意義。只有人的出場才使物的出場成為可能”(錢冠連2005卷首語)。這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運(yùn)用“我”變體,我的出場便獲得種種凸顯度。超大量的“我”變體將原來隱匿的人性需求(張揚(yáng)出社會身份與地位)凸顯地、隆重地公開出來。
本文對漢語人自稱的高度凸顯與張揚(yáng)的觀察結(jié)果,與海德格爾“關(guān)注人的現(xiàn)實性,即“一個真實的人的存在或生存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具有哲學(xué)優(yōu)先性”(Heidegger 1999,1962)不謀而合。在漢語人自稱超豐富的表達(dá)里,我們讀出海德格爾所謂“一個真實的人的存在或生存”狀況。海德格爾的詳細(xì)解釋是:“對自己存在(Beingone’s-Self)的解說使我們得以看見我們或者可以稱為日常生活(everydayness)的‘主體’那樣的東西 ,即常人(the “they”)”(Heidegger 1999,1962:149-150,著重號為本文作者所加)。他說的“常人”不是本真生存而是非本真生存的人。但是,我們這里的人自稱正是在進(jìn)行“對自己存在的解說”!他又說,“這個誰是用我自己、用‘主體’、用‘自我’來回答的”(Heidegger 1999,1962:150)。請注意,“我自己”、“主體”及“自我”都可以回答“誰”,“我自己”、“主體”及“自我 ”在日常用語里便是本文強(qiáng)調(diào)的人自稱的種種變體。其實,人自稱就是反省的“我”的意識,用海德格爾的話說,便是 reflective awareness of the “I”(Heidegger 1999,1962:151);“‘我’這個詞只可領(lǐng)會為某種東西的不具約束力的形式標(biāo)記”(Heidegger 1999,1962:151-152)。
可見,研究“我”變體的重大意義在于能與海德格爾的“此在”相呼應(yīng),“我”是此在的本質(zhì)規(guī)定性。海德格爾不無暗示地說,“如果‘我’確實是此在的本質(zhì)規(guī)定性之一,那就必須從生存論上來解釋這一規(guī)定性”(Heidegger 1999,1962:152)。他意在提示,“我”是此在的本質(zhì)規(guī)定性。在Being and Time里,人的優(yōu)先地位以海德格爾式的闡釋方式實現(xiàn)。在漢語里,則以人自稱的方式實現(xiàn)。人自稱正是在進(jìn)行“對自己存在的解說”!
人自稱的情況因時因地因文化不同。當(dāng)它與張揚(yáng)人性的種種附加信息相交時,變得高度復(fù)雜起來,不同的附加信息用于不同的“我”變體。
這與物被稱的情況不同。最明顯的不同在于,同人自稱并列的名稱非常多,然而同物被稱并列的名稱則少很多。一物一名,這是非常普遍的情況。一物兩名者較少,如“蕃茄”與“西紅柿”。一物三名者,也較少(參見下文)。那么,物被稱為什么少很多?
一物兩名或三名之間,正如Frege所指出,其表達(dá)方式與認(rèn)知內(nèi)容彼此有別(Frege 1952)。一物如 Venus,清晨出現(xiàn),人們叫它 The Morning Star;晚間出現(xiàn),人們稱它為The Evening Star.Frege指出了這兩個名稱(后來羅素稱為“摹狀語”)的極為重要的兩點區(qū)別:一是這兩個名稱的呈現(xiàn)方式不同,二是認(rèn)知內(nèi)容有別。我們增加的例子是一物三名,如有一物,它是塊狀粗根植物,漢語使用者可以根據(jù)形狀像掛在馬脖子上的鈴鐺叫“馬鈴薯”,根據(jù)它從南美洲引進(jìn)中國這一淵源叫“洋芋”,根據(jù)它形如黃豆且埋在土里故叫“土豆”。這三個詞體現(xiàn)出三種不同呈現(xiàn)方式與認(rèn)知內(nèi)容。我們以為,一物兩名與三名的區(qū)別是不同地域的人根據(jù)指稱對象的物理性狀的不同感知而定名的,也只需要物理性狀就可以完成對物的區(qū)分性指稱。然而,物理定性是外在的、固定的,根據(jù)物理性狀定名與定多少名相對容易把握。
也就是說,一物多稱的低概率是源于對事物物理性狀的認(rèn)知脫離語境的可能性較大,或者說語境依賴性較小,即語境敏感度(context-sensitivity)低(這一思想得益于梁爽提醒)。然而,以“我”變體稱名我時,我的物理性狀不變也無須涉及,但我作為人,其人性張揚(yáng)與社會性狀卻必須細(xì)微涉及。“我”的種種變稱傳達(dá)出不同的社會性狀(社會身份,如級別與地位)。“在下”、“卑職 ”,“為兄 ”、“哥們 ”,“爺們 ”,“朕 ”,“貧道 ”,“老朽”以不同呈現(xiàn)方式與認(rèn)知內(nèi)容顯示出不同的社會身份的貴賤與色彩。人性與社會性狀是內(nèi)在的,多樣的。據(jù)此定名與定多少名,不容易把握。也就是說,人自稱的眾多變體源于語境敏感度高,即語境依賴性大,可脫離語境性為零。這是人自稱超多名現(xiàn)象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之一。
我自稱對人性張揚(yáng)與社會性狀的要求的無限性與模糊性、物被稱對物理性狀的要求的有限性與精確性,是前者復(fù)雜多變與后者簡單少變的原因。這是兩者一多一少的內(nèi)在驅(qū)動力之二。
上述內(nèi)在驅(qū)動力之三是,人們?yōu)榱藴p少稱呼的記憶負(fù)擔(dān),盡量減少物體與事物的名字,這才符合語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如果物被稱之名也像人自稱那樣多,語言體系就會膨脹到人們無法承受的程度。這一點和梁瑞清(2008)提出的語言地圖說有相通之處。這是物被稱時并列之名在競爭中淘汰多、存活少的重要原因。可是,為了凸顯人性與社會性狀,在人自稱這一個項目上(畢竟是少數(shù)),即使?fàn)奚Z言的經(jīng)濟(jì)原則也是值得的,因為一個項目上膨脹,總量不會大到人們承受不了的程度。這是人自稱時并列之名在競爭中淘汰少、存活多的重要原因。
內(nèi)在驅(qū)動力之四是,并列稱呼或名字之間的競爭與淘汰,取決于一個稱呼與名字體現(xiàn)出來的呈現(xiàn)方式與認(rèn)知內(nèi)容是否能被另一個稱呼與名字取代。“中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存,“馬鈴薯”、“洋芋”與“土豆”共存,它們誰也沒有淘汰誰,原因就在于各自凸顯出競爭方無法取代的呈現(xiàn)方式與認(rèn)知內(nèi)容。但是,畢竟物被稱的多名之間決定競爭的優(yōu)勝劣敗的因素少而明確,容易導(dǎo)致凡是能被取代的名字都被淘汰的結(jié)果。
物體并列名稱被淘汰的第五個原因是,對物體的認(rèn)知修改或糾正(不是取代)進(jìn)程快(這一思想得益于王愛華),而人自稱涉及自身的利益,因此不愿修。而在人自稱并列名稱之間,各種競爭方無法取代的因素多到難以算計,只好讓許多變體共同存活。不過,漢語人自稱(如前所引語料)隨著時代的推進(jìn),既淘汰了一批舊稱呼,也產(chǎn)生了一些新稱呼。對此,本文不予討論。貴稱、自抬、抬高自己是為了獲取盡量多的利益與名聲,賤稱、自謙、自貶、自揶也是為了最終保護(hù)自己的利益與名聲,這或許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道德上的自謙觀的生長與發(fā)展的理由。人的天性傾向于斤斤計較于社會地位與等級,于是加在名字上的隱匿信息隨之增加,并列的稱呼減不了多少,只能接受。
人自稱的超多名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5種驅(qū)動力,都不是呈現(xiàn)方式不同與認(rèn)知內(nèi)容不同所能解釋的。以上分析大致上可以適用于 “你”或者 you,“他”、“她”或者第三人稱 he/she的情形。這種情形恰好就是“人被稱”。在 “人自稱”與“物被稱”之間插入一個‘人被稱’(這一思想得益于梁爽),形成“三元并存范疇”,即“人自稱 -人被稱-物被稱”。該范疇分三方但不對立,可以應(yīng)和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循序漸進(jìn)的認(rèn)知路徑。這個三元并存范疇體現(xiàn)人對自身生存狀態(tài)的自關(guān)心、對他人生存狀態(tài)的他關(guān)心、對物的他關(guān)心之間的差異。
但是,在各種語言,特別是漢語中,人被稱(第二、第三人稱)的社會身份的隱匿性信息變體似乎沒有“我”名我時那樣多。原因在于,(1)人自我膨脹之心總是多于膨脹別人,(2)可能在于我更了解、更能認(rèn)知自我,對他人的了解和認(rèn)知是間接的與后一歩的,所以稱呼方式相對少一些(這一思想得益于王愛華)。
必須對物被稱的情況作一重要補(bǔ)充:用以指稱一個對象的語詞,其變體越豐富,其(主動或被動)凸顯度就越高。這可能是一條對人自稱、人被稱和物被稱都適宜的規(guī)律:假如某物在特定語言中的指稱方式有許多變體,該物的“存在和出場”比他物得到更多張揚(yáng)。
最后,漢語“我”變體的豐富與強(qiáng)烈的自關(guān)心是否具有普適性?西語的“自關(guān)心”如果有,應(yīng)該以什么為標(biāo)記?須知,西方人也跟我們一樣十分復(fù)雜。但是,如果這個東西不具有普適性,那么導(dǎo)致漢語“自關(guān)心”的特殊根源在哪兒?我們以為,這個問題可以變換成如下的問題:如果漢語“我”變體的豐富與強(qiáng)烈的自關(guān)心不具有普適性,可不可以斷言它是一個文化問題而不是一個真正的哲學(xué)問題呢?我們的回答是:不可以。(1)“我”眾多變體是指稱,我自身是指稱的對象;(2)這一切都是為了增加“我”出場(我存在)的凸顯度;(3)漢語人自稱的特別豐富與物被稱的相對少量,無疑體現(xiàn)人的認(rèn)知規(guī)律:先識已后識物。根據(jù)這三點,足以斷言:漢語“我”變體的豐富與強(qiáng)烈的自關(guān)心是一個真正的哲學(xué)問題,但其中雜有地域文化現(xiàn)象(也許,漢文化更慫恿人自稱的超大量出現(xiàn))。
3 結(jié)論
設(shè)置“人自稱-人被稱-物被稱”三元并存范疇的意義在于:(1)彰顯人對自身生存狀態(tài)的自關(guān)心,人自稱的高度復(fù)雜性使我們認(rèn)識到人的高度復(fù)雜性。(2)彰顯人對自身生存狀態(tài)的自關(guān)心、對他人生存狀態(tài)的他關(guān)心、對物的他關(guān)心之間的差異。這一差異提示,人自稱對語言的復(fù)雜訴求終歸可以看成人對自己的優(yōu)先彰顯,這是不能以Frege提出的呈現(xiàn)方式不同與認(rèn)知內(nèi)容不同來解釋的。(3)研究“我”變體可以與海德格爾的“此在”相呼應(yīng)。“我”是此在的本質(zhì)規(guī)定性。人的優(yōu)先地位在Being and Time里以海德格爾式的闡釋方式實現(xiàn),在漢語里以人自稱的方式實現(xiàn)。人自稱正是“對自己存在的解說”!
假如某物在特定語言中的指稱方式有許多變體,該物的“存在和出場”就會比他物得到更多張揚(yáng)。人對世界一物一事的稱呼與描述,其實是以自己的眼光干涉其中的。
梁瑞清.語言地圖說[J].外語學(xué)刊,2008(3).
尼·布寧余紀(jì)元.西方哲學(xué)英漢對照辭典[D].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錢冠連.語言:人類最后的家園[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
蘇珊·哈克.總序一[Z].斯特勞森.個體:論描述的形而上學(xu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
Frege,G.On Sense and Reference[A].In P.Geach and M.Black(eds.).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Gottlob Frege[C].Trans.Max Black.Oxford:Blackwell,1952.
Heidegger,M.Being And Time[M].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ie&Edward Robinson,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Chengcheng Books,LTD.Reprinted from the English Edition by SCM Press Ltd.,1999.
Quine,W.V.O.Word and Object[M].Massachusetts:MIT Press,1960.
Russell,B.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M].London,Jorge Allen and Unwin,19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