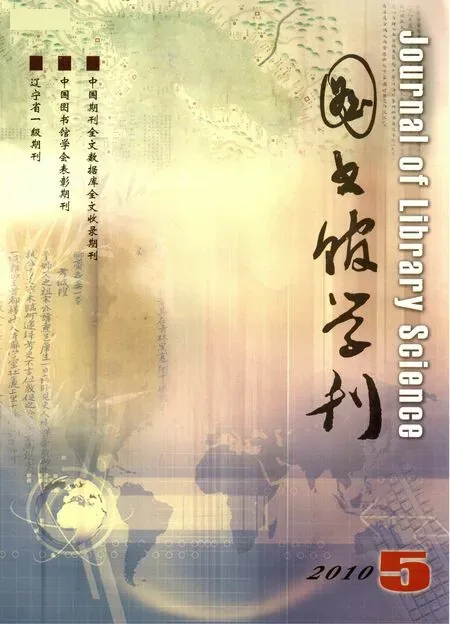西域文獻特色館藏建設的思考*
石詠梅趙建基梁國杰葉 勤
(1.塔里木大學圖書館;2.塔里木大學人文學院,新疆 阿拉爾 843300;3.華中農業大學圖書館,湖北 武漢 430070)
歷史上的西域是指中國西部疆域,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其范圍雖發生過一些變化,但漢唐以來,就成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西域的特殊地理位置,世界多種文化曾在西域交匯、沖突和流轉,構建了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絲綢之路既是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之路。正是絲綢之路的貫通,中原漢學、印度佛學、中亞伊斯蘭教、歐洲基督教等四大文化才在這里交融薈萃,西域文化也在與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改頭換面,甚至脫胎換骨。西域文化多樣化、多元化特征的文化生態,對文化創新和豐富文化內涵都有重要價值,西域文化研究日益成為國內外學者關注的熱門話題。塔里木大學位居西域的中心、絲綢之路交通要道之上,有著西域文化研究獨特的地理優勢。近年來,在“以環塔里木的生物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為特色,作塔里木文章,創區域性優勢,建綜合性大學”的辦學定位的指導下,西域文化研究已經初步成為塔里木大學特色的發展方向。西域文獻特色館藏建設目標也正是站在立足服務西域文化研究,建設特色優勢學科的角度,擬建成特色鮮明、館藏深厚,在國內甚至國際上具有西域文獻權威地位的特色館藏資料庫。
1 西域文獻庫館藏資源現狀
塔里木大學的西域文獻庫是伴隨著西域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而興建的一個特色書庫。西域文化研究在該校的發展歷史并不長,但研究成果已經贏得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西域文獻庫則是西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撐。2004年以來,在塔里木大學的大力支持下,西域研究所與校圖書館通力合作,通過重新分類、鱗選,在有限的與“西域”相關圖書基礎上,建立了西域文獻庫。隨后學校加大西域特色文獻庫的投資力度,通過圖書征訂、定向索取、館際交流等多種手段,大量收集西域文化與絲路文化研究的古籍新書和反映新疆政治、宗教、科教、民俗、歷史、地理、經濟、旅游資源開發等內容的地方文獻,截至2009年12月,西域文獻庫館藏已達2萬多冊。當前,西域文獻庫不僅為西域文化研究和教學提供了豐富而有價值的文獻資料,在提高全校師生和社會參觀者深刻認識西域文化的重要性方面發揮著積極作用,同時也對該校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和社科學術研究產生重要作用和重大影響。近3年來,該校獲得國家級、省部級社科基金項目立項逐年大幅遞增,僅2009年就有6項有關西域文化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10多項省部級的社科基金項目獲準立項。西域文獻庫的影響力也逐漸以學校為中心向周邊地區輻射,積極為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服務。西域文獻館藏不僅為本校的科學研究和教學研究提供了信息資源的保障,而且在“存史”、“資政”、“勵志”、“造福”等方面提供了文獻支撐。西域特色館藏建設和對其資源進行深入開發和利用,為該校人文社科研究與教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對加強新疆各民族相互了解,增進民族間的認同,對推動新疆政治、文化、經濟的發展,擴大地區之間、國際間的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該校西域文化研究在國內外的知名度不斷提升,西域文獻庫因突出鮮明的地域特征、文化特征和綜合性特征,不斷吸引國內外學者的關注。
然而,我們也要看到,由于建館時間短,文獻積累速成,西域文獻庫建設也存在方向太泛、思路模糊、架構混亂、開發膚淺等問題。在收集文獻上存在為提高館藏數量而饑不擇食、急功近利的問題;在館藏分類上存在缺乏科學架構、館藏特色不鮮明的問題;在館藏的利用和開發方面還多以文獻檢索和圖書借閱為主,文獻書目索引、題錄尚在編制中,地方文獻電子全文數據庫建設仍處于籌劃階段。如果資源建設缺乏科學長遠的規劃,盲目追求“大而全”,既不利于特色的凸顯和保持,也會因資金浪費和經費短缺影響建設步伐。
“信息資源的開發應當有明確的方向,著眼于整體布局,通過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進行合理、科學的開發和利用。”[1]在突出地域性的基礎上,強調資源的系統性、文化的多樣性、研究的定向性,實現“你無我有,你有我全,你全我精,你精我絕”的目標,是西域文獻庫館藏建設的原則和定位。
2 西域文獻庫建設需要解決的問題
2.1 “西域”界定不明,導致地域文獻收集方向不明
從西域文獻庫創建以來,西域地方文獻征集的地域范圍一直是個令人爭議的話題。縱觀歷史對“西域”的描述,有小西域、大西域和文化西域等不同概念。小西域即以新疆代西域。[2]大西域則將地域擴展西部疆域,包含中國歷代政府管轄的最大疆界。因其在疆域劃分上存在較大分歧并難以確定,廖肇羽先生則提出一個文化西域的概念,力圖以文化西域突破狹隘的地域觀念和種族觀念,通過文化大力拓展、了解西域智慧,從多元角度將西域傳統所具有的精神資源放大。[3]基于此,如果以小西域界定西域文獻資料庫的收集范圍,就很容易將西域文獻資料庫做成“新疆地方文獻庫”;而以大西域的界定進行西域文獻資料庫建設無疑會讓西域文獻資料庫建設無所適從,增添建設難度;相比較而言,以文化西域的概念建設“西域文獻書庫”既符合西域文化研究的宗旨,富有歷史文化的內涵以及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同時也讓“西域文獻庫”建設更為靈活、更加廣泛,同時也可真正從文化角度提升“西域文獻庫”的內在品質。
2.2 西域文獻庫建設定位模糊,導致文獻針對性不強
西域文獻庫館藏現在存在定位過大、過泛,一廂情愿地要將收集文獻的范圍無限擴大,試圖使之成為包羅萬象的西域信息百科文庫和將其建設成為西域歷史博物館。我們知道,任何事想要面面俱到,最終必然是面面不到,西域文獻庫建設也同樣要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西域文獻庫的定位,首先是一個書庫。因此,其館藏的主體應該是圖書形式的正式出版物,擴大些可以將一些內部出版物或內部資料匯編也納入其中,其館藏應與檔案館相區別。第二,西域文獻庫應該突出文化西域的內在品質,即其文獻的文化性、研究性。因此,西域文獻庫中的館藏主體應為史實資料和學術研究成果,應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價值,野史、演義和文學作品只能作為輔助補遺資料加以精選,史實文獻資料和學術研究成果應該是該庫館藏的核心。當然,有所側重地在某一特定研究領域,擴大資料收集范圍和內容,甚至是將一些文化遺存實物作為特殊館藏,對凸顯館藏精妙和絕響也是必要的。
3 西域文獻特色館藏建設框架
3.1 對“特色”準確定位是西域文獻庫建設的重要指針
圖書館必須加大對重點學科和特色專業文獻資源的收藏和開發,為特色辦學創造條件。特色是優勢,沒有優勢就沒有特色;特色是品牌,沒有品牌就沒有市場。雖然西域文獻庫本身就具有特色意義,但更重要的是館藏內涵質量和文獻服務能取得優勢地位。館藏建設要有明確指針,必須澄清其館藏特色到底是什么。是新疆地方史志館還是西域文獻資源庫?是社科文庫還是綜合性文庫?是“地方專題”還是“民族集錦”?是學術研究還是驚艷獵奇?是只限在正式出版物還是包括一些田野調查收集到的第一手影、音和書面資料?西域研究重在文化范疇,這個范疇應首先界定在人文學科領域、社會學科領域,即使對自然學科有所涉及,也應體現文化研究的意味。西域文獻庫首先是為科研服務,其次是為教學服務,再次是為興趣服務。循著以上思路,西域文獻庫的特色定位可以這樣確定:西域文獻特色館藏建設是以西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領域為文獻收集內容,突出環塔里木文化多樣性特征,以豐富系統的史實資料和學術研究資料為西域文化研究和特色優勢學科建設服務的高品位、高規格、特色鮮明的文獻庫和西域文獻特色數據庫。
3.2 西域文獻庫建設與特色館藏資源數字化建設
目前,西域文獻庫建設雖然已經初見成效,也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但館藏內涵質量和服務內容還遠遠不能滿足國際國內西域文化研究的需要,仍停留在傳統的圖書文獻館藏和服務模式,更無法滿足信息社會的發展要求。在網絡化、數字化的信息時代,應大力推進西域珍貴文獻信息的數字化,實現信息共享和遠程服務,要讓西域特色館藏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需求。為實現西域文獻館藏數字化目標,塔里木大學圖書館正積極進行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型,加大了圖書館自動化、網絡化和數字化建設力度。當前,已經展開了以圖書館網站為平臺的網絡服務,圖書館提供的數字資源已逐漸成為校園網上重要的信息資源,如:“多媒體視聽資源庫”、“精品資源展播”、“校園Vod點播”、各種中外文專業數據庫等,這些數字資源已逐漸成為廣大師生教學和科研的重要文獻保障。這都為西域文獻特色館藏數字化奠定了基礎。
西域文獻數據庫建設雖然具有相當難度,但與傳統文獻庫相比其內容可更豐富、形式可更靈活多樣、涉及面可更加廣泛,圖片、影、音資料都可以成為其重要的特色資源。為此,塔里木大學圖書館與西域文化研究所已經開始共同規劃籌建西域特色文獻數據庫、西域圖文志數據庫、西域影像志數據庫。西域文獻特色館藏通過文獻館藏資源與數字化、網絡化的配套建設,一定能走出一條突出文獻的地域性、文化的多樣性、研究的定向性、資源的系統性的特色化發展之路,并通過數字化和網絡化增強多向服務和遠程服務,為西域文化研究和特色學科建設提供更好、更全面的信息服務。
[1] 石詠梅.關于我國信息資源可持續發展的思考.現代情報,2004(12):16-17.
[2] 新疆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新疆簡史.第一冊.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3] 廖肇羽.再續小西天的佛教文化薪火.筆耕大漠憶吹簫,334-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