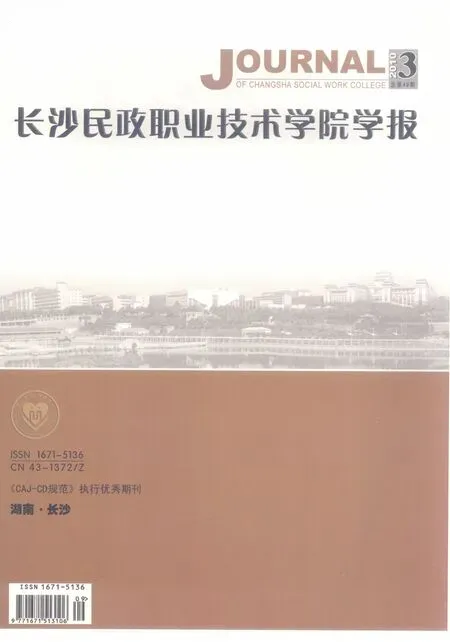山寨文化中“模仿”的特點
陳金美 廖海兵
(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山寨文化中“模仿”的特點
陳金美 廖海兵
(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具有平民性、媚俗性、相似性、創造性、游戲化的特點。模仿者皆為平民身份;對原型符號價值的追求使得模仿具有媚俗性;原型與摹本的外形、構造和功能等極為相似,但也存在差別;在模仿的形式上,摹本增加新元素,超越了原型;從創造者的心態看,模仿具有游戲化的特性。
山寨文化;模仿;特點
2008年歲末,“山寨”一詞狂飆突起。它已經從一種單純的經濟行為衍生為社會文化現象。而“模仿作為山寨文化的基本內核”[1]已成為共識。模仿作為一種行為以及行動的本能,其歷史幾乎和人類一樣久遠。而隨著時代和技術的發展,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出現了平民性、媚俗性、形似性、創造性和游戲化的特點。
一、平民性
平民性主要體現在模仿主體的身份上。在“山寨”盛行的當今,有多少山寨文化產品,就有多少個模仿者。盡管模仿者無數,但他們在多方面有著驚人的一致:(1)個人收入相對不高;(2)沒有顯赫的家世和社會背景;(3)遭遇過生存困境和話語霸權;(4)渴望訴求利益和表現自我。根據這些描述,山寨文化創造者的身份輪廓進一步清晰起來。他們大多絕非達官豪商、專家學者、明星貴人,也并非出自名門望族。根據2001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山寨文化創造者更多來自產業工人階層、個體工商戶階層和城市無業、失業和半失業階層,或者說,他們處在占據我國總人口多數的社會基層,如生產山寨手機的中小廠主、發起山寨春晚的四川北漂——老孟、制作山寨《百家講壇》的自由職業者——韓江雪、拍攝山寨《紅樓夢》的在讀大四學生——陳維實、模仿周杰倫的福建小藝人——周財鋒、手拿山寨火炬進行傳遞的山村農民等。他們有著不同的遭遇:或者飽嘗生存之苦,或者缺乏文化關懷,或者倍受各種歧視。但他們都用一種獨特的方式 (模仿)把自己的構想和理念付諸于現實,從底層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反叛之聲。他們是基層群體的急先鋒,緊扯著低成本模仿的福祉,積極投身于文化產品的生產中。這樣,籠罩于文化頭上的神秘烏云不斷散去,精英與民眾的距離被驟然拉近,文化創造不再是某些人的“專利”。草根民眾在高雅藝術和通俗文化之間搭起了一座橋梁。只要愿意,平民也可成為“導演 ”、“制片人 ”、“攝影師 ”、“主演 ”、“主講者 ”、“設計師”、“明星”等角色。然而,在古代社會里,由于經濟、教育及社會地位的不平等,藝術創作更多為貴族階級所壟斷。到了近代,模仿生活和教化世人成了知識分子的專利,民眾被迫游離在文化的邊緣,得勢的文藝精英們更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設置距離,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救世主”。進入到當代,這種現象并無多大改觀,精英文化仍為少數文化精英所把持,而貌似大眾自己的大眾文化也好不到哪里去。“大眾文化的從業者既是文化人,更是唯利是圖的商人”[2](p27)。機械復制只能是文化媒介人和資本家生產文化產品和利潤的工具。
二、媚俗性
媚俗性集中體現在山寨文化創造者 (以下稱創造者)所模仿的對象上,從實物到人物,再到精神產品,模仿的內容非常廣泛,如NOK IA手機、康師傅方便面、雕牌洗衣粉、999皮炎平、百度、谷歌及雅虎網絡搜索引擎、北京奧運會火炬、“神七”登月艙、鳥巢、劉翔、周華健,還有電影《幸福像花兒一樣》、央視春晚、央視《百家講壇》、電視劇《紅樓夢》等等,無不成了創造者模仿的對象。更為重要的是,對照山寨產品,我們便會發現山寨文化產品的原型 (模仿對象)有一個突出特點:它們都是早已為大眾熟知或當下流行的“經典”。正如中山大學李宗桂教授所言,“山寨文化的很多產品,都是對先進產品的模仿”[3],“先進產品”是創造者眼中所謂的“經典”,更是法國社會學家讓·鮑德里亞所提出的“媚俗物”。在消費社會里,消費者與物品的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消費者“不再從特別用途上去看這個物,而是從它的全部意義上去看全套的物”[4](p3)。這使得消費物品因其符號功能而逐漸弱化、喪失了實用功能,一切消費品成了一堆擺設,成為一個個的“媚俗物”。媚俗物的流行能為人們提供空幻的期許和自欺欺人的精神慰藉。它那強大的符號功能讓消費者對此趨之若鶩,頂禮膜拜。上列的品牌物品擺放于此,它吸引消費者的不僅是其客觀實用性,更是其昂貴的品牌、著名的商標以及它們所共同暗示的時尚、尊貴、富有和高人一等。由于品牌一旦確立就難以超越,再加上低端消費者無力購買價格較高的名牌產品,創造者只得通過對現成的媚俗物進行改造,重新生產出意義和快感。這樣,既滿足了他們的實用需求,更給予了自己極大的精神安慰。創造者對這些品牌或經典的模仿實際上是對它們所代表的文化符號的追求,其行為本身就帶有一種媚俗性。僅憑這點,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在源遠流長的模仿史上是獨樹一幟的。模仿對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斷地被加以修正和更新。以前,原型或者是與自然相應的主體的內心結構;或者是神秘原始的自然;或者是至高無上的上帝;或者是萬物基始的理式。它們作為形上之物,看不見摸不著,受世人模仿和景仰,具有無比的崇高性和神秘性。而現今的山寨文化創造者極力模仿形下之物,舍本求末,其媚俗性不言而喻。
三、形似性
形似性主要體現在原型與摹本關系的處理上,山寨文化從外形、結構、功能和商標、風格等方面模仿品牌、明星和經典。首先,從外形、構造、功能看,山寨商品和品牌商品極為相像,但創造者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在它們之間保留著極其微小的差異。比如,一些山寨手機外觀與品牌機酷似,功能接近甚至超越了品牌機,但其價格、質量 (手機自身和售后服務)的差別就能讓消費者識別它們各自的身份。再如“NOKLA”與“NOK IA”、“康帥傅 ”與“康師傅 ”、“營養干線 ”與“營養快線”、“慢嚴舒檸”與“慢嚴舒寧”之間在標貼上差之毫厘,可質量也許就失之千里。其次,雖然山寨明星在原型的發型、體形、招牌動作和神態上極盡模仿之能事,但他們的學識修養、歌唱水平和商業價值與原型還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差距。譬如,山寨周杰倫的長相盡管與周杰倫很像,但他們做廣告的價格真是天壤之別了。再說,作為山寨文化代表之一的山寨《百家講壇》,它模仿央視《百家講壇》的風格,主講人口述、話外音、插圖和背景,五臟俱全,可二者的制作成本及質量相去甚遠。由上可知,在創造者對原型的模仿過程中,他們使得摹本與原型在形式上建立了一種再現與被再現的關系。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就在像與不像、是與不是、叛逆與順從之間游離,獲得了一種形似的特征,即山寨文化在商標、外形、功能、動作和風格上無限地接近或靠近原型,同時又在模仿和照搬中刻意凸顯自己獨特之處。正如北大學者張頤武所指出,“‘山寨’產品一面制造混淆和相似,一面卻也表現差異和區別。……‘山寨’有模仿秀等文化潮流的影子,但它并不期望惟妙惟肖地變成被模仿的對象,而是一種刻意的‘像但不完全是’的姿態和風格”[5]。或者說,山寨文化的模仿追求的不是神似,而是形似。這種形似化處理既是商家善于打法律擦邊球的結果,更是草根受眾那種豪奢消費欲望與自己經濟實力極不相稱的矛盾心態的表達。
山寨版文化的模仿力求形似,而歷史上其他的模仿呢?傳統現實主義的藝術家模仿自然或生活,不求惟妙惟肖地模仿客觀世界的外形,而重在模仿一種超越外部世界的精神實質,即神似,給讀者以道德教化或精神鼓舞。模仿作為現代主義的一種創作手段,它要求藝術家全面模仿傳統作品中特有的風格甚至習性,務必在形式上達到一種“陌生化”的效果。福克納式的長句、勞倫斯別具特色的自然意象、普羅科菲耶夫的音樂風格等就是這方面突出的例子[6](p451)。后現代主義的拼貼是一種對傳統風格或習俗的空心 (缺乏嘲弄)模仿,是諸多歷史碎片的無序組合,更是一盤“歷史大雜燴”[7](p454)。其中除了一堆文本、文字、精神分裂者的語言,一無所有。這無疑將形式的模仿發揮到了極致。
四、創造性
從模仿的形式來看,模仿可分為客觀性模仿和創造性模仿兩類。前者主要以柏拉圖的鏡式模仿為代表,后者主要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并得到全面繼承和進一步發展。而山寨文化中的“模仿”就屬于創造性模仿。這種創造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山寨文化的生產者往往整合很多不同名優產品的長處,再根據草根消費者的需求,增加新的功能,或者在外形上講究變化,力求新穎,從而打造出一種新的商品。這一點在山寨機上表現尤為突出。山寨手機的生產廠家針對中國年輕消費者的“特殊需求”,增加了大屏幕、大喇叭、大容量、超長待機、雙卡雙待、驗鈔、電棍、游戲機等功能,甚至利用先進的拼裝技術,把八個低音炮喇叭、四個攝像頭、高倍率望遠鏡、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都拼接到一部手機上。網絡上正炒得火熱的“桔子手機”除了高仿蘋果 iPhone外,根據消費者的需求,還實現了兩個重要超越:一是超長待機時間,二是支持雙卡。另一方面,根據個人需求、地域特色、外在背景和現實條件,在材質、風格等方面力求變化,仿造出新產品,實現對模仿對象的超越。比如說,山寨鳥巢的制作者們根據北京鳥巢的外形,分別采用不同的材質如沙石、核桃、竹子,因地制宜,生產出不同版本的鳥巢 (沙盤鳥巢、山核桃鳥巢、竹鳥巢)。大四學生陳維實利用家中的被單、桌子等做道具,根據演員自己對角色的理解,拍出風格迥異的山寨版《紅樓夢》。“山寨的模仿里有自己的創造,照搬中有新的元素和想象的延伸”[8]。模仿暗含著創新,創新又隱藏在模仿中,山寨文化的特殊性就是巧妙地把它們融合在一起。模仿中帶著幾分草根智慧的創新,既符合模仿自身的規律,更有市場的需求必然。這更為山寨文化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把模仿當作照鏡子,開辟了機械式模仿的先河。到了古羅馬時期,藝術家的模仿更趨于逼真,尤其是造型藝術已沒有古希臘的那種神性的刻意美化,像奧古斯都、龐貝、尼祿這些大人物的肖像酷似原型,貼近現世的模仿觀占據主流。當代的機械復制就是這類模仿得到進一步強化的結果。比起它們,當代山寨文化的模仿在創新上確實前進了一步。然而,根據創新模式理論 (創新可分為跟進創新、集成創新和原始創新三個階段)進行判斷,山寨文化還只是停留在跟進創新或集成創新的階段。可以說,山寨文化中的創造性處在一個低級階段,還有待于日后的完善和發展,最終要向原始創新階段邁進。
五、游戲化
游戲化的形成與山寨文化創造者當下的心態和心理訴求是密切相關的。“新時期初彌漫于整個社會的樂觀、生氣勃勃、理想主義的情緒,伴隨著生存境遇的危機和個體在轉型期間的失落、無奈,形成一種普遍的懷疑精神和非理性主義。‘一場游戲一場夢’、‘瀟灑走一回’代表了一種普遍的‘游戲’心態”[9]。另外,在市場經濟社會里,人們的生活節奏日益加快,工作壓力
越來越大,人際交往愈發荒漠化,人們自由支配的時間和自由活動的空間特別是精神溝通的心理時空受到限制,在身心方面都很容易感到疲勞,從而使得他們產生了一種放松身心和享受娛樂的強烈需求,尤其是在俏皮中長大的年輕草根一代。因此,“游戲”心態定會在人們的行為中刻上烙印,娛樂需求必然構成他們行動的內驅力。山寨文化創造者正是用一種調侃、游戲甚至致敬的心態模仿原作,并在對原作的解構、拼貼、戲謔和嘲諷中,真正體驗到自由、解脫和精神勝利的快感。正如席勒所言:“人只有在‘游戲’時 (擺脫自然和理性的強迫)才是自由的”[10](p414)。山寨《紅樓夢》中那簡單的道具 (被單當華服)以及家人搓麻將的穿幫鏡頭令網民忍俊不禁,其實這更可看作是對新版《紅樓夢》脫離民眾欣賞趣味的嘲諷。山寨歌曲《說句心里話》中那漢語式的英文歌詞、很不地道的美聲唱法以及《阿甘正傳》的背景畫面無不讓人捧腹。山寨諾貝爾獎和山寨熊貓通過對社會事件與諾貝爾獎的嫁接和對松獅狗的“易容”,表達了草根大眾渴望獲得諾貝爾獎和一睹“國寶”風采的美好情懷,更是人們對當前一些社會現象的一種無奈和失望情緒的發泄。山寨文化中的“模仿”融入夸張、解構、拼貼和嫁接等后現代主義手法,寓嚴肅于輕松之中,達到嘲諷社會百態和追求快樂的目的,獲得一種啼笑皆非的效果。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山寨文化中的模仿也可稱作戲仿,這種游戲化特點與人們當下的“游戲”心態和強烈的娛樂訴求是契合的。另外,網媒的推動使得這個特點更會顯現出來。
[1][8]劉瑞生.中國刮起“山寨風”:山寨成最流行網絡新詞[N].人民日報,2009-02-19.
[2]葉志良.大眾文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
[3]李宗桂.何必跟山寨文化過不去?[N].人民日報,2008-12-07.
[4][法 ]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 [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張頤武.“山寨”的活力和限度[J].新西部,2009,(3).
[6][7][美 ]詹明信.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M].上海:三聯書店,1997.
[9]汪方華.通俗電視劇接受中的獨特心理機制 [J].現代傳播,2005,(1).
[10]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C913.4
A
1671-5136(2010)03-0015-03
2010-04-25
陳金美 (1952-),男,湖南南縣人,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研究方向:文化哲學;廖海兵(1980-),男,湖南衡南人、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