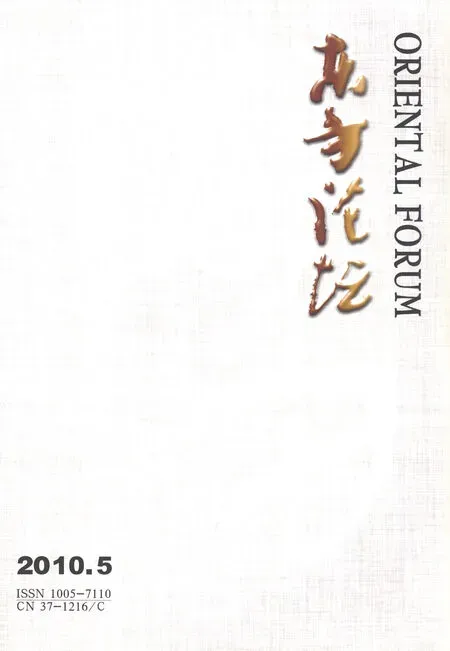《黃鸝聲聲帶血鳴
——孫犁抗日小說研究》的方法論啟示
王金勝 季美艷
《黃鸝聲聲帶血鳴
——孫犁抗日小說研究》的方法論啟示
王金勝 季美艷
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孫犁是個糾纏著諸多悖論的獨特存在。從1940—1950年代中國作家構成的譜系上看,他是位《講話》后成長起來的來自解放區(qū)的“中心作家”,其政治身份、政治地位,其寫作的合政治目的性,按理說是無可置疑的,但從批評界對其接受來看,情況似乎要復雜得多,孫犁自己也承認:“強調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評了;有時強調第二標準,情況具好一點。”[1](P396)進入1990年代后,他甚至又被研究者視為“革命文學中的‘邊緣人’”[2]。其前期文學創(chuàng)作只有一本《白洋淀紀事》、一本《風云初記》,外加兩個中篇《村歌》與《鐵木前傳》,但卻在文學史上占據了一個重要位置,且自1990年代以后日益成為研究熱點(在有的學者眼里大有超越曾被稱為“講話旗手”、“解放區(qū)文藝方向”的趙樹理之勢頭①這方面代表性著作:如趙建國的《趙樹理孫犁比較研究》,昆侖出版社2002年版。另外日本學者渡邊晴夫也認為:“趙樹理的作品在解放區(qū)和新中國成立后17年的中國得到了不可類比的高度評價,而孫犁的文學具有與之正好相反的特性。這大概就是對孫犁的評價近年有所提高的原因吧。而對孫犁的評價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定會越來越高。”,參見渡邊晴夫等的《中國文學史上對孫犁評價的變遷——與趙樹理比較》,《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 年第1期。)。孫犁晚年回顧自己的創(chuàng)作道路時,曾公開告白:“我最喜愛我寫的抗日小說,因為它們是時代、個人的完美的結合。”[3](P396)但學術界對其“抗戰(zhàn)小說”的研究卻較為匱乏,且基本停留在單篇作品的藝術鑒賞層面,以泛化的印象式批評為主,缺乏應有的學理含量。近年來,學界出現了些孫犁研究的專門著作和論文②代表性的著作:如閻慶生的《晚年孫犁研究:美學與心理學的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葉君的《參與、守持與懷鄉(xiāng)——孫犁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這些成果借助現代心理學、美學和西方哲學來探討孫犁的美學思想、身份建構等問題,但總體上還局限于對孫犁及其作品的內部研究,無法將作家納入歷史結構中大幅度地敞開主體的精神和心靈世界及其美學折光。1990年代初,兼具作家和研究對象身份的孫犁極為少見地表達了對批評界某些研究不足的抱怨:“研究不能老重復過去那些東西,什么孫犁文章行云流水呀,什么富有詩意呀,還有荷花淀流派等等,要拿出一些新東西。”[3]無疑,孫犁及其文本期待著研究者以突出的創(chuàng)新性打破研究成規(guī),尤其是其自期甚高的“抗日小說”的研究常規(guī)——這不僅因為孫犁的自我評價,還因為抗戰(zhàn)改變了他的人生命運和精神結構,更因為對“后期孫犁”“新孫犁”的真正有力的理解和闡釋無法繞過其抗戰(zhàn)寫作。從這個意義上講,李展博士的《黃鸝聲聲帶血鳴——孫犁抗日小說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簡稱論著)在選題上就體現出研究者的獨具只眼和基于既往學術積累所生發(fā)出的挑戰(zhàn)性。
論著打破了以往關于孫犁的作家狀況研究,作品研究,文學史型整合研究等傳統(tǒng)研究現狀,有針對性地運用傳統(tǒng)和現代批評方法,進行了一種帶有結構主義色彩的“總體性”研究。這種研究不但將孫犁作品的內在結構性呈現出來,而且將孫犁作品納入一種“歷史總體性”中獲得整體關聯的內在意義,同時揭示出孫犁創(chuàng)作的文化心理基礎與歷史性含義。
論著采用了知人論世的傳統(tǒng)批評方法。盡管孫犁的小說是一種具有濃郁的抒情性和鮮明的風景畫風俗畫描寫的“心靈—風景型”小說,但因為孫犁的作品及其本人的生活、思想與其所產生的時代有密切的關系,其小說作為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一部分,具有鮮明的時代面影和意識形態(tài)性,因此要真正了解孫犁小說,就必須“知其人”和“論其世”,唯如此,才能客觀地準確地理解和把握其小說的思想內容和美學風格。清代學者章學誠曾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在他看來,所謂知人論世,應當“論世”第一,“知人”第二。孫犁在評論古書古人時有著自己的知人論世的意識:“文人處世,有個人的特征,有時代的樣式。歷代生活環(huán)境不同,政治情況各異,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作風,他們對生活的態(tài)度,他們理想的發(fā)生,都不會一樣,都有時代的烙印。先秦兩漢,盛唐北宋,號稱太平盛世,文士眾多,文章豐富。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時,文人的生活處境及政治處境,就特別困擾艱辛。反映在他們處世態(tài)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難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時期,是個動亂的時期,北朝文人很少,他們的生活,尤其動蕩不安,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這種動亂。”“我們今天談論魏收,也不過就一篇簡短的傳記,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論世的試探,究竟有多少科學性,就很難說了。”[5](P68)應該說,以知人論世這一傳統(tǒng)批評方法來勘探歷經歷史風云變幻而又葆有“赤子之心”的孫犁及其文本的精神世界是符合作家實際的。論著對孫犁小說所論,首先是著重于作家個體特殊的身世經歷,其次是重視個人的才性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影響。也就是說,論著的“知人”不僅局限于革命意識形態(tài)為主的“志”,而是擴展到作家的個人生活、性情、才氣、身世、立身、行事、情趣,將淺層的才情、意趣深化為作家的人格精神。具體來看,論著對孫犁關注的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人”,二是“文”,“文”即孫犁獨特的藝術風格與藝術造詣。在對其人其文深度把握的基礎上,因文以論人,或因人而觀文,較好地做到兩方面的結合。這在“孫犁文學創(chuàng)作之心路歷程”部分體現得尤其集中。把作家放在所處的時代環(huán)境中,以五四新文學(尤其是魯迅、葉圣陶等)的影響、北平的流浪、抗戰(zhàn)烽火的激蕩、革命文學及理論的接受、“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講話》的發(fā)表、“冀中一日”運動、婚姻革命、身份革命等對孫犁其人其作產生重大甚至根本性影響的事件為中心,從生活史和精神史兩大方面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的起源、文學風格形成的心理基礎,及其家庭、婚姻、生活經歷、思想感情、個性品格、文化修養(yǎng)等進行了通盤的梳理與整合,闡釋了孫犁抗戰(zhàn)文學美學風格形成的根本原因,論述了孫犁小說與魏晉文學之相似與差異,探討了孫犁小說兼具審美和革命的功利性的二重性特征,對孫犁文學的主體意志進行了迥異于通常研究對孫犁作品非審美即功利的品格定位,指出:“孫犁文學的主體意志不是個體意志的意義存在,而是所謂革命理想的信念所形成的大寫的‘民族’概念,也正是這種大而化之的理想,才為他賦予了一種大化流行的傳統(tǒng)倫理感受,而非簡單現代意義的個人主體意志了”。這種分析和定位,把握住了對象在個體與群體(“民族”而非“國家”“階級”“政黨”等)、功利與審美、傳統(tǒng)倫理感受與現代主體意志、革命敘事與倫理敘事之間的復雜性,并以此為基點進行深入探討,并以其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貼合到位,而使論著生發(fā)出了諸多前人未道的創(chuàng)新點。
文史互證這一中國文史研究傳統(tǒng)方法在論著也得到了較好地運用。論著以孫犁文學創(chuàng)作寫作的歷史背景為出發(fā)點,把前者嵌入歷史的深層結構中,從對象的身世遭遇、歷史意識和政治態(tài)度入手,深入孫犁文學敘事生成的歷史環(huán)境,依據敘事內容探究孫犁從事抗戰(zhàn)活動的經歷,同時又借助相關革命史的發(fā)展脈絡來解讀孫犁小說,文學與歷史相互參正,旁推曲鬯,以意逆志,透過表面的藻繪,進入對象的心胸,打開了對象新的心靈世界。論著對1946—1956年間孫犁的心態(tài)、創(chuàng)作與當時政治氛圍、文學體制之間關系的分析;對延安時代的政治結構、政治規(guī)訓、女性分配與對孫犁小說“小資情調”的批判、孫犁小說的修改與發(fā)表之間關系的分析;對建國后知識分子問題與孫犁小說中知識分子形象塑造之關系的分析等等,作了一些頗見功底的考據分析,有些判斷很有見地。僅舉一例,論著對《風云初記》中李佩鐘對老革命高慶山表達愛情的一句話“是你們老干部討厭知識分子嗎”入手,進行了如下分析:“這句話可以是李佩鐘的愛情話語,但卻是作家本人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進而提出疑問“革命的老干部作為女性知識分子的戀愛對象,難道他們不喜歡這些有教養(yǎng)的女性知識分子嗎?”,論著又結合延安革命陣營的婚姻革命及將女性知識分子作為革命的祭禮的分配這些革命史料,挖掘出李佩鐘此話的深層含義:“難道老干部不討厭男性知識分子嗎?難道老干部不喜歡女性知識分子嗎?”一個簡單的細節(jié)分析,卻舉重若輕地透露了大量的歷史信息。
上述對李佩鐘愛情話語下潛在的作者的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分析,同時也得益于另一種批評方法的運用:癥候式閱讀。
論著以對弗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學說的充分的理論自覺,較合理地運用癥候式閱讀方法打開了深隱復雜的主體空間。在闡釋孫犁及其小說時,論著沒有停留于文本的表層空間,而是深入對象的心理和文本結構的深層空間,以文本的斷裂、含混、悖逆、反常等為突破口,尋求此類癥候出現的原因,重新闡釋作品的意義。除了上例,論著對《囑咐》中“性愛”場景的“缺位”這一癥候也進行了深度挖掘,認為,小說講述的實際上是一個“被‘革命’包裝起來的‘性愛’敘事”,“在故事的核心不是革命,而是夫妻對話,而夫妻對話都是性愛敘事的情愛話語”。在文本的敘述過程中,“經過‘革命’洗禮的戰(zhàn)士這時已經深陷重圍:‘情’與‘欲’的矛盾,歡愛與身體 矛盾,倫理秩序與身份定位的矛盾,革命不過在此提供了一個表演舞臺;而當生活一下‘失去軌道’(其父親去世帶來的混亂),革命的鑼鼓聲聲催人急的時候,‘倦意’就來了。”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性愛場景“缺位”的性愛敘事中,革命者和革命敘述因選擇“情”分離“欲”而陷入的困境。另外,論著對《荷花淀》中三個關鍵的文學場景的分析很有意思。從具體場景入手,論著通過對其語言和行為等細節(jié)處隱藏的反常、悖逆的探查,發(fā)掘人物如何在特定的歷史階段展現自我和自我變遷,揭示某些甚至不為作家自己所意識到的歷史內涵如何在超過場景、細節(jié)而形成的特定文化場域中獲得表現。
論著對孫犁抗戰(zhàn)文學中北方風景描寫的闡釋是相關領域中具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成果。它集中闡釋了孫犁作品中“游觀”視角、在游動中的人生“邂逅”傳奇、對于事件“目擊”直觀的心靈透入所帶來的孫犁小說美學最為深層的心理打動力量,它“將孫犁風景描寫有機地結合歷史風云與孫犁自身的創(chuàng)作歷程甚至將古典山水美學與中國革命的特殊性情景結合起來——這些都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研究境界,改變了孫犁研究的深度和廣度”[6]。這些都顯示了論著的獨特研究用心。
總而觀之,論著從歷史(革命史、精神史、美學史、文學史)的角度進入研究對象,突破了以往的封閉式研究,將對象納入一個風云動蕩的歷史空間中,不僅展開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視野,而且也使自身獲得了深沉厚重的歷史感和超越作家論個案研究的普遍性意義。
[1]孫犁.文學和生活的路[A].孫犁文集:第4卷[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2]楊聯芬.孫犁,革命文學中的“多余人”[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8,(4).
[3]孫犁.語重心長一席話——孫犁談文學研究[J].天津市孫犁研究會簡報,1994,(1).
[4]滕云.孫犁研究新聲息──孫犁創(chuàng)作學術討論會隨想[J].文學評論,1989,(3).
[5]孫犁.買《魏書》、《北齊書》記[A].孫犁文集?續(xù)編:第3卷[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
[6]郜元寶.序[A].李展.黃鸝聲聲帶血鳴——孫犁抗日小說研究[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單位:青島大學文學院)
book=125,ebook=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