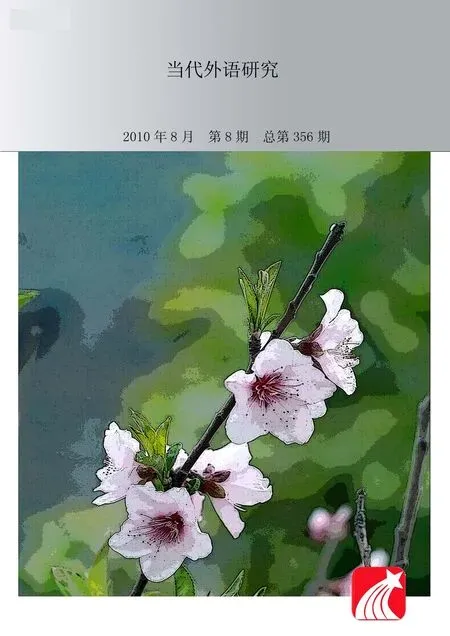楷模:杜波依斯、非裔美國知識分子與蓋茨的《十三種觀看黑人男性的方法》
李有成
(中研院歐美研究所,臺灣)
1.
2010年最新一期的《跨國美國研究學報》(JournalofTransnationalAmericanStudies)刊登了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的一篇佚文《非裔美國人》(TheAfro-American)。此文原作為一長達20頁的打字稿,長期躺在麻州大學杜波依斯圖書館的原稿檔案里,在杜波依斯生前或死后從未正式發表,也未收入杜波依斯的任何文集中。據日本多摩大學納亨姆·陳德勒(Nahum D. Chandler)的推測,此文當完成于1894年晚秋至1895年晚春之間,此時距杜波依斯剛自德國取道法國與英國回到美國大半年左右(Chandler 2010:4)。結束悠游歐陸學術與知識傳統的歲月,重新回到美國的現實,面對自己種族的困境,年輕的杜波依斯在世紀末思考美國社會中最根本的種族關系,并開始形塑一個他稱之為非裔美國人的“假定的歷史與社會主體”(5)。
《非裔美國人》一文以杜波依斯自身的遭遇開始入筆。就在他身居歐洲期間,面對并無惡意的歐洲朋友時,他發現自己始終是個“問題”:他的語言、他的膚色、他的國籍、他的種族無一不如此。他告訴他的歐洲朋友,他屬于“美國那九百萬人中的一位,這些人構成了所謂的‘黑人問題’”(Du Bois 2010:2)。
杜波依斯一向被視為20世紀前半葉最重要的美國黑人知識分子。他是位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教育家、編輯、社會運動分子、傳記與自傳作家、小說家、散文作家,尤其自1915年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逝世之后,杜波依斯儼然成為黑色美國最主要的發言人,其動向觀瞻格外引人注目。森奎斯特(Eric J. Sundquist)(1996)認為,杜波依斯的知識能源其實來自他與不同陣營黑人領袖的對立,包括他與布克·華盛頓與加維(Marcus Garvey)的齟齬(10)。布克·華盛頓在1895年的亞特蘭大棉花暨工業博覽會(The Atlanta States Cotton and Industrial Exposition)中楬橥其調解論(accommodation),向白人呼吁,“在所有純粹與社會有關的事務中,我們可以像手指頭那樣隔離,但在所有涉及相互進步的事務中,我們又可以像手那樣合一”(Washington 1965:148)。這個論調當然是整個“隔離但平等”政策與社會實踐的意識形態基礎,杜波依斯斥之為投降主義;在他看來,若接受這樣的投降主義,非裔美國人無異于自動放棄其政治與教育權利,而只勉強爭取其經濟權利。杜波依斯在其經典《黑人的靈魂》(TheSoulsofBlackFolk)一書中辟有專章,抨擊布克·華盛頓的種種不是,指其所散播的論調為“工作與金錢的福音”。他甚至以勸誡的語氣指出:“人的自尊遠比土地與房產有價,一個民族若自動放棄此自尊,或停止為此自尊奮斗,這個民族不值得過文明生活”(Du Bois 1965:247)。
杜波依斯雖然不以布克·華盛頓的調解論為然,同時極力提倡黑人靈魂之說,但他畢竟不是個極端的黑人民族主義者,因此對加維所代表的強烈民族主義并無好感。加維是位牙買加移民,在布克·華盛頓去世之后,其思想論說對非裔美國人社群頗有影響。他是黑人分離主義的主要倡導者,其分離主義主要具現在他所宣傳力行的“返回非洲”運動;但加維的分離運動在其輪船公司營運失敗之后遭到重挫,加維甚至因欺詐罪入獄兩年,后被遞解出境,遣返牙買加。基于其極端的黑人民族主義,加維認為種族混雜無異于種族自殺,這一點與白人種族歧視分子如三K黨者的看法不謀而合,加維因此不惜與三K黨人尋求和解。這其實正是杜波依斯強烈質疑甚至輕蔑加維的地方——盡管兩人都是廣泛的泛非運動的支持者(Sundquist 1996:11)。
杜波依斯似乎不得不在上述20世紀前后分別由布克·華盛頓和加維所代表的美國黑人社會運動中尋找出路。華盛頓大學美國文學教授波斯諾克(Ross Posnock)在一篇討論非裔美國知識分子的論文中曾試圖解決這個問題。波斯諾克的論點相當程度是在反地道政治(politics of authenticity)。他認為有關美國黑人知識史的討論長期以來一直深受認同政治的宰制,而此認同政治又出于對“種族地道特質與根源的崇拜”(Posnock 1997:324)。具有創造性的黑人知識分子在20世紀初之所以能夠形成一種社會類型(social type),關鍵即在于能夠抗拒此地道特質的意識形態。杜波依斯即是波斯諾克心目中的“黑人知識分子的主要理論家與具體象征”(325)。
杜波依斯活了93歲,著作等身,思想相當復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全盤交待。他早年也曾發表過像《論種族的維護》(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Du Bois 1970)之類極力為種族這一概念辯護的文章。此文原為杜波依斯在美國黑人學院(American Negro Academy)的演說;他在演說中所部署的論述策略其實不脫19世紀的生物種族主義或種族科學,甚至無限上綱將種族擴大為大敘事的要角,藉以解釋世界歷史的發展。他說:
世界歷史并非個人而是群體的歷史,并非國家而是種族的歷史,任何人忽略或不顧人類歷史中種族的觀念,即是忽略或不顧一切歷史的中心思想。那么何謂種族?通常種族指的是具有共同血緣與語言、總是背負共同歷史、傳統與本能的一大族人,主動或被動地群策群力為達成某種多少經過生動構思的生活理想而奮斗。(Du Bois 1970:75-76)
杜波依斯這一席話看似超越科學種族主義,而強調社會歷史的種族觀,其實并不盡然。阿皮亞(Anthony Appiah)在論及這個問題時,即這樣追問:“如果他已經全然超越〔種族的〕科學觀念,他演說中提到的‘血緣’扮演的又是什么樣的角色?”(Appiah 1986:25)。阿皮亞認為,杜波依斯既強調血緣,又指明是“一大族人”,顯然意指共同祖先(26),其種族觀不免有生物種族主義之嫌,雖然共同祖先未必就一定構成同一種族。此外,阿皮亞以為,所謂共同語言的條件也并非必然成立:“羅曼斯”族并無共同語言,黑人更是另一個現成的例子:黑人也沒有共同的語言。阿皮亞以相當的篇幅討論杜波依斯所謂的共同歷史的問題。問題在于:共同歷史可否成為區分不同人群的標準?阿皮亞的答案是否定的:
比方說杜波依斯本人。他是荷蘭人祖先的后代,何以他與14世紀荷蘭歷史的關系(他與所有荷蘭人后代共享的歷史)并未使他變成條頓民族的一份子?答案至為明顯:荷蘭人不是黑人;杜波依斯則是。由此推論可知,非洲的歷史之所以是非裔美國人共同歷史的一部分,并非單純由于非裔美國人系出某些在非洲歷史上扮演過某種角色的人們,而是因為非洲歷史是同一種族人民的歷史。(27)
阿皮亞的意思是:“分享共同群體的歷史不能成為決定是否為同一群體成員的標準,因為我們必須能夠先認定某一群體,才能認定此群體之歷史”(同上)。阿皮亞的分析一方面否定杜波依斯的社會歷史的種族觀,因為在杜波依斯的指涉架構中,此種族觀顯然不能成立;另一方面則認定杜波依斯其實并未走出19世紀的種族科學,依然以血緣、家族等生物證據思構種族屬性①。
三年后杜波依斯在泛非會議(Pan-African Conference)演講,發表其著名的有關膚色問題的預言,其看法也未能擺脫生物種族主義:“20世紀的問題是膚色界線的問題,也就是種族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顯現在膚色和發質——今后究竟如何形成否定超過半個世界的權利的基礎,使這些人無法盡其所能分享現代文明的機會與特權”(Du Bois 1970:125)。
據已故非裔美國批評家蘭伯沙德(Arnold Rampersad)的說法,進入20世紀之后,杜波依斯才逐漸修正他的種族觀。關鍵之一即是人類學家波亞斯(Franz Boas)的思想學說對他的影響。波亞斯有關非洲歷史意識與文化復雜性的觀點,以及他對文化與文化價值所采取的相對主義,都對杜波依斯純粹的種族觀帶來相當大的沖擊(Rampersad 1996:299)。不過,蘭伯沙德又認為,在認識波亞斯的思想學說之前,杜波依斯在其求學過程中即曾接觸過兩種反種族科學的力量,這兩種力量都與他的柏林經驗有關。其一是他在1892年至1894年留德期間所接觸的社會主義;其次是他的博士論文導師哈特(Albert Bushnell Hart)所堅持的一絲不茍的史學方法以及他在柏林留學期間所修習的實證社會學(Rampersad 1996:300)。上述種種對杜波依斯往后的種族觀都可能造成影響,至少在1903年的《黑人的靈魂》一書中,在悼念其早夭的頭胎兒時,他這樣描述他的孩子:
他不知道膚色的界線,可憐的孩子。帷幔雖然投影在他身上,但尚未遮蔽他半邊的太陽。他愛他的白人看護長,他愛他的黑人護士;而在他小小的世界里,靈魂孤獨地走著,既無顏色,亦無衣裝。(352)
帷幔(the Veil)一詞在杜波依斯的論述與創作世界中具有特定的象征意義,指的即是他心目中的膚色界線或種族藩籬。波斯諾克認為,在《黑人的靈魂》一書中,杜波依斯所進行的其實是一種雙重計劃:他的論述既在帷幔之內,又在帷幔之外,超越帷幔(Posnock 1997:326)。而最能夠擔負起超越帷幔的工作的,則是非裔美國知識分子:杜波依斯企圖在非裔美國知識分子身上開拓“去種族化的領域”(deracialized realm),進一步調解“種族獨特性與非種族普遍性”之間的沖突(325)。波斯諾克在總結杜波依斯有關黑人知識分子的議題時指出:“黑人文學知識分子的出現端看他們如何設計一種延異、曖昧與開放性的邊陲美學,以及某些同時也是去自然化的政治策略的文學再現型態”(326)。在一個視種族歧視的刻板印象為“自然”現象的社會里,去自然化毋寧是個極為重要的政治策略。
2.
杜波依斯有關黑人知識分子的討論中,經常被引述的是《論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The Talented Tenth”)一文。此文首見于1903年出版的《黑人問題》(TheNegroProblem)一書,據說此書若非經由布克·華盛頓編輯,至少是在獲得他的同意后才出版的。所謂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顧名思義,指的是美國黑人領袖,是杜波依斯在文中所提到的卓越人才或最優秀的族人,“他們可以帶領群眾遠離最惡劣的污染和死亡”(Du Bois 1996a::131)。
杜波依斯認為,美國歷史上不乏這樣的黑人領袖,“在他們的時代中卓越地屹立在最優秀的人們當中,……以他們的言行阻止膚色界線成為奴役與自由之間的界線”(Du Bois 1996a:135)。他特別強調,單在廢奴運動中,就有不少黑人領袖(即杜波依斯心目中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與白人并肩努力,……沒有這些人,〔黑奴解放運動〕將無法克竟全功”(137,強調部分為筆者所加)。在杜波依斯看來:
這些人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證明黑人種族的種種可能性,他們本身的艱苦經驗與精致文化所默默表達的,比歷史上所有時期的演說家所說的還要多。這些人使得美國的蓄奴制度不復可行。(同上)
可惜,美國人,特別是美國白人,對此毫無認識。杜波依斯因此質問:
美國人曾否停下來想想,在這片土地上有不下百萬人,他們有黑人血統,受過良好教育,擁有自己的住家,……從任何標準來衡量,這些人都達到了現代歐洲文化最佳類型的完美限度?忽略這些黑人問題的事實,貶抑這種熱望,抵消這種領袖能力,設法打壓這些人,讓他們回到他們與他們父祖因辛勤工作而冒出頭來的群眾中去,這算得上公平嗎?值得尊敬嗎?合乎基督教義嗎?(139)
基本上,杜波依斯把他心目中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視為“才智與質量的貴族階層”。而這個階層的最重要工作即在于伸手援助“所有值得拉拔到優勢地位的人”(同上)。要完成這樣的工作,教育是不二法門:“最優秀及最能干的年輕人必須在這塊土地上的學院與大學受教育”(140)。杜波依斯雖未特別規劃此教育內容,但對他而言,布克·華盛頓那種專注于基本謀生技能的教育是不完整的,因此在總結自己的論點時他特別指出:
教育與工作是提升人民的兩具杠桿。單單工作是不夠的,除非工作受到正確理想的啟發以及才智的引導。教育不應僅僅教導工作;教育應教導生活。黑人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必須被塑造成其人民當中思想的領袖與文化的傳教士。(156-57)
《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發表45年后,也就是1948年,杜波依斯發表其《論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紀念演講》(Du Bois 1996b)(“The Talented Tenth Memorial Address”)。文中特別強調黑人領袖犧牲奉獻的重要性,至于新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杜波依斯提出更為清晰、更為寬泛的看法:
一個群體領袖的觀念,不僅受過教育,需要自我犧牲,而對當今世界的狀況與險惡也有明晰的視境,能帶領美國黑人與歐洲、美洲、亞洲的文化群體結盟,同時期待一個新的世界文化。(168)
杜波依斯話里所描繪的正是蓋茨(Henry Louis Gates,Jr.)所謂的跨越行為(cross over):美國黑人在種族隔離的圍墻崩塌之后進入白人的世界(Gates 1996a:13),并進一步與世界主要文明對話并攜手合作。
蓋茨與韋思特(Cornel West)合著的《種族的未來》(TheFutureoftheRace)一書顯然是針對杜波依斯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的觀念而進行的論述計劃。兩人相信,“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所塑造的典范,使得像他們那樣的所謂“跨越”一代(“crossover” generation)的成員,那些統合歷史上屬于白人的教育與專業機構的黑人知識分子,知道自己所應該扮演的社會、政治與倫理角色(Gates和West 1996)。在一個對非裔美國人乃至于弱勢族裔依然不是那么公平、不是那么公義的社會里,非裔美國知識分子和領袖自然背負著特殊的責任;重讀杜波依斯的文章,目的即在于界定非裔美國人的族群屬性的“倫理內容”,以進一步厘清當代非裔美國人領導階層的道德責任。蓋茨與韋思特兩人皆自承是杜波依斯心目中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的后代,是民權運動與平權行動的直接受益者。
有趣的是,盡管兩人都體認到當代非裔美國知識分子的道德與倫理責任,但他們對杜波依斯的基本理念反應卻不盡相同。韋思特以其一貫的黑人左翼傳統的立場,以二分法描繪杜波依斯整個論述計劃的層系關系:
權威與傳統強化狹隘的鄉土主義與低層的文化。受過教育和伶牙利齒的階級(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是世故與優勢的代理人,而未受過教育而哀傷呻吟的階級(落伍的群眾)則被囚鎖在傳統之中。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的基本角色即在于教化、精致化、振奮和提升蒙眛無知的群眾。(West 1996:60)
杜波依斯的精英主義在韋思特的二分法下一覽無遺。其實,蓋茨也承認杜波依斯所思構的乃是建立在精英主義基礎上的論述與社會改造計劃:黑人“有產者”(black “haves”)對黑人“無產者”(black “have-nots”)所肩負的社會與倫理責任(Gates 1996a:119;1996b:132)。
對韋思特而言,杜波依斯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觀念其實饒富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化與道德價值,他認為杜波依斯所承續的其實不脫柯爾律治(Samuel T. Coleridge)、卡萊爾(Thomas Carlyle)、阿諾德(Matthew Arnold)等人所主張的精英傳統:
杜波依斯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觀念,大抵屬于大英帝國高峰時期維多利亞主要批評家所構思的文化與政治精英的后代……。柯立芝(柯爾律治)的世俗知識階層、卡萊爾的強勢英雄,以及阿諾德不偏不倚的異類無不避開物質主義的膚淺庸俗以及享樂主義的廉價刺激,同時極力保存與提倡高層文化,教化與圍堵低層群眾。杜波依斯的文章《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第一個及最后一個宏亮的句子不僅回響著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批評的“諸多真理”,同時也賦予受教育的少數人士救世的角色。“黑人就像所有人種一樣,將由他們的卓越人士來拯救。”(West 1996:65)
這里所謂的卓越人士指的當然是男性。韋思特因此指責杜波依斯的論述計劃其實充滿了眾多父權的感性。
韋思特企圖將杜波依斯精英式的杰出人士與他理想中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加以區隔,或者說他有意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取代杜波依斯式的文化精英。他指出:
公共知識分子的基本角色……在創造與維持高質量的公共論述,探討若干可以啟發并激勵公民的迫切的公共問題,鼓動他們采取公共行動。……知識分子與政治領袖既不是精英的,也不是民粹的;而應該是民主的,我們每個人都應不卑不亢地站在公共空間,為公共利益提出我們最好的視境與看法。而這些議論應在互敬互重與相互信任的氣氛之下提出來。(West 1996:71)
蓋茨收在《種族的未來》中的長文《杰出人士的寓言》(“Parable of the Talents”)并未直接檢討杜波依斯的論述計劃,而是以自述與論述的方式,以其作為“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后代的身分與經歷,分析當前非裔美國知識分子與領袖階層的危機,特別是這些人面對黑色美國所應該扮演的楷模角色。蓋茨的文章有相當的自況或自我辯護成分,因此文中不乏他對黑人文化民族主義的抨擊:“對民族主義的訴求……是為了掩飾黑人社群中的階級差異。隨著經濟差異增加,維持文化與意識形態表面的一致性也有必要跟著增加”(Gates 1996a:37)。他對當前若干非裔美國領袖人物操弄種族政治的意圖顯然頗為不滿。因此他認為,“黑色美國需要一種政治,此政治的首要任務不在強化黑色美國這個理念;同時也需要一種種族論述,此論述之中心關懷不在維護種族這個理念或者維護對種族的一致性看法”(38)。這種政治或論述在當代黑人藝術家或女作家的藝術生產中最能顯現出來:黑人藝術家既意識到其文化傳統的獨特性,但也假定黑人經驗有其普遍性;黑人女作家更是將種族政治擺在第二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相當敏銳的性意識(43)。
蓋茨雖然并未界定新的種族政治,但依他看來,以黑人文化民族主義為基礎的舊種族政治顯然已不適合跨越一代的非裔美國知識分子或領導階層。
3.
蓋茨的《十三種觀看黑人男性的方法》(ThirteenWaysofLookingataBlackMan)一書所反映的無疑正是這種不是那么重視種族的種族政治。這本書若非充滿父權感性,至少也彌漫著男性感性:全書所收的八篇人物側寫中,無一是女性,雖然其中有一、兩篇的主角是男同性戀者,如著名作家鮑德溫(James Baldwin)和舞者暨編舞者瓊斯(Bill T. Jones)。除鮑德溫外,作家還有穆雷(Albert Murray)和布洛雅德(Anatole Broyard);除此之外還包括了宗教領袖法拉干(Louis Farrakhan)、軍事家鮑威爾(Colin Powell),以及演藝界名人貝拉豐特(Harry Belafonte)。其中與書名同名的一章則是對辛普森(O. J. Simpson)一案的觀察與反省。蓋茨筆下的人物當然不盡都是知識分子,但無疑都是廣義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用蓋茨的話說,這些人的故事都可以歸類為文學批評家斯特普托(Robert Stepto)(1979)所說的“力爭上游的敘事”(“narrative of ascent”)。這些人大多出身寒微,但無不在不同行業中功成名就:他們是“塑造世界、也為世界所塑造的人”(Gates 1997:14)。正因為這些都是力爭上游的故事,蓋茨認為,這些人都必須扛負起所謂“代表的重擔”(“burden of representation”):你既然代表你的種族,你的一言一行可以給你的種族帶來榮譽,也可以讓你的種族蒙羞。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些人都是艾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50)所謂的楷模(Representative Men),都或多或少“背負著成為偶像的重擔:這些人無不被賦予意義,被寓意化;而這些人更是以跟其它意義和寓意的斗爭來界定自己”(Gates 1997:17)。正因為如此,非裔美國人的生命似乎更為緊密相連,形成真正的想象社群(imagined community)。蓋茨在洛杉磯華茲區(Watts)種族暴動之后,深深產生這種體認:“另一位黑人的行動影響你的生活,只因為你們兩位都是黑人。我知道我不認識的人的行動已成為我的責任,彷佛華茲區的黑人鄉親實實在在的都是我的派德蒙(Piedmont)村里的親戚”(6)。
蓋茨此書當然不是嚴謹的傳記,他將書中各篇稱為人物側寫(profile)。蓋茨認為,側寫這種文類“假定人物至關緊要”——不論這些人物所扮演的是他們自己、行動媒介,或被我們視為象征(Gates 1997:216)。我們同不同意這些個別人物的言行作為是一回事,我們卻不能不承認這些人都是非裔美國人社群中的楷模人物。最重要的是,這些人物的言論和行誼,以及蓋茨直接與他們的互動,諸如對他們的訪談,提供給蓋茨相當寬廣的論述或批判空間。本書所突顯的那種不是那么重視種族這個類別的種族政治只是一例而已。我們可以從蓋茨與其側寫人物的互動中看出這一點。
在蓋茨側寫著名作家鮑德溫的一章中,他回憶少年時代初讀鮑德溫的《原鄉之子札記》(NotesofaNativeSon)的經過。1965年8月,十五歲的蓋茨參加圣公會教會的夏令營,牧師給了他一本《原鄉之子札記》。蓋茨后來表示,這是他第一次聽到“這個國家里身為非洲人后裔一份子的極度興奮與焦慮”的聲音。對他而言,鮑德溫此書展現一種“亞當式的(Adamic)命名功能”,清楚剖析“美國文化想象中復雜的種族動力”。蓋茨隨即以自己在種族隔離的村莊成長的經驗指出:“我知道‘黑人文化’自身有其肌理,有其邏輯,而且與‘白人文化’糾結難分”(Gates 1997:7)。蓋茨對黑人文化這樣的體認其實是以另一種言說響應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靈魂》一書中所提到的黑人心靈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黑人自始就很清楚自己的“雙重性”(twoness):既是美國人,也是黑人,“兩個靈魂,兩種思想,兩邊無法妥協的抗爭;一個黑色軀體中兩個對立的理想”(Du Bois 1965:17)。蓋茨在八十年代討論非裔美國文學傳統時,即曾借用杜波依斯的觀念闡述非裔美國文學的“雙重性”:美國文學根植于非裔美國人的新世界歷史與經驗,進出于西方白人與非洲黑人的文化傳統,這種“雙重性”因此造就了非裔美國文學的獨特性(參見李有成2007:168)。蓋茨在回憶閱讀鮑德溫的《原鄉之子札記》時重提黑人文化與白人文化之間的糾葛現象,只是再一次申述長期以來他對種族文化絕對論的質疑,鮑德溫的《原鄉之子札記》為他提供論據,因此他說:“如果黑質(blackness)是座迷宮,鮑德溫就是我的向導”(Gates 1997:7)。
類似的理念在側寫鮑德溫這一章中俯拾皆是。譬如,在總結鮑德溫有關黑白關系的討論時,蓋茨認為,“如果鮑德溫有那么一個中心論點的話,那么其論點是,黑色美國與白色美國的命運是深遠而無可逆轉地糾纏在一起的。互相創造,互相界定與對方的關系,也可以互相毀滅”(Gates 1997:10)。換言之,這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系,互為因果,彼此界定,建立基于這種理念的種族與文化政治當然無法接受種族絕對論,也無法同情文化純粹論。在結束對鮑德溫的側寫時,蓋茨還忍不住引述鮑德溫在其散文集《票價》(ThePriceoftheTicket)一書結尾的話重申自己的論述立場:“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無助地、永遠地含納他者:男的含納女的,女的含納男的,白人含納黑人,而黑人含納白人。我們是彼此的一部分。我的許多同胞似乎認為這個事實極不方便,甚至不公平,我經常也這樣認為。但我們對此無能為力”(20)。蓋茨顯然對此深信不疑。他說:“二十年前我們需要聆聽這些話。現在我們仍需聆聽這些話”(20)。
在另一篇對著名非裔美國舞蹈家瓊斯的側寫中,蓋茨借用瓊斯在其舞蹈藝術中所部署的身體政治(body politics),討論黑人身體在西方白人的文化想象中的復雜意義,并從有關黑人身體的詮釋中看到此文化想象的雙重曖昧性:黑人身體一方面被西方文化妖魔化,被認為兇暴、粗糙,而且具有危險的性涵義;另一方面又被熱烈稱頌,被視為黝黑惑人——仍然具有危險的性涵義,不過是好的一面(Gates 1997:61)。在蓋茨看來,瓊斯在舞臺上擅于操弄身體政治,充分剝削白人的凝視(gaze):他在此凝視下工作,與此凝視嬉戲,并善用此白人凝視(62)。
蓋茨指出,瓊斯同情高度現代主義,因此無法接受“黑人文藝運動”(Black Arts Movement)所設定的種種約束②,尤其無法忍受此文藝運動所強調的黑人文化的純粹性及其背后的意識形態。瓊斯表示:“我不是黑人民族主義者。……從十二歲開始,我就跟白人一起成長,這些人在我家人之外真的給予我最大的關懷,有時候甚至遠超過我的家人,因為他們可以在我身上看到我在家里不會表露的東西。因此,當我進入舞蹈世界時,我是以一位前衛主義者進入的”(Gates 1997:55)。所以蓋茨認為,瓊斯堅持“先是藝術家,其次才是黑人”的信念(55)。他以瓊斯自己的話印證他的看法。瓊斯表示:“我對地道性比創新性要更有興趣。如果能達到創新性,那很好。我也想再現美。我的美的典范泰半是由歐洲中心的作品所塑造的”(69)。
與書名《十三種觀看黑人男性的方法》同名的一章是以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為主角,顯然寫于辛普森因殺妻案在刑事訴訟中被宣判無罪釋放之后。與其他人物側寫不同的是,這一章的重點不在敘寫辛普森,而是在記述與分析辛普森脫罪之后美國各界(特別是非裔美國人)的種種反應。另有一點與其他章節也不盡相同:蓋茨并未訪談辛普森,也未見他與辛普森的交往或互動。這一章與其說是側寫辛普森,毋寧說是記錄與析論辛普森殺妻案宣判后所觸動的美國社會中長期以來欲語還休的黑白種族關系。應該一提的是,蓋茨所記述的反應多來自非裔美國人的知識精英,包括學術界、教育界、宗教界、藝文界許多耳熟能詳的名字。這些人立場有別,看法互異,不過對辛普森能夠幸免于牢獄之災,許多黑人咸感振奮,而“許多驚慌失措的白人則有一種短暫的感覺,種族這玩意兒似乎遠比他們假想中來得纏結難解——當所有的敬意都退去之后,黑人確實是置身于他們之中的陌生人”(Gates 1997:104)。白人自以為了解黑人,辛普森殺妻案是個觸媒,讓白人驚覺得他們原來對共同生活了幾個世紀的黑人其實所知有限。不過依蓋茨的觀察,這樣的種族化約并非實情,反而忽略了黑人社群本身也一樣分裂的事實,只是分裂的方式對大部分的白人而言隱晦不明而已(119)。蓋茨本人即相信辛普森證據確鑿,罪無可恕;在案子宣判前夕,他甚至開始擔心辛普森如何渡過牢獄歲月(119)。
辛普森一案所激發的種種反應,以及這些反應背后所隱含的種族危機使蓋茨相信,危機確有其事。在總結他對這些反應的思考時,蓋茨感慨指出,“辛普森一案的判決引發是非對錯的辯論,跟我們長期以來討論種族與社會正義的方式若合符節。被告也許獲得自由了,但我們仍受縛于譴責與反譴責、憂傷與反憂傷、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二元論述中。……其結果是,種族政治變成想象的一個法庭,黑人伺機懲罰白人所犯的罪行,白人也伺機懲罰黑人犯下的罪行,隨之而來的就是以得分解決的無止境的倒退”(Gates 1997:121)。
蓋茨的感慨暴露了美國種族關系治絲益棼的一面,小說家里德(Ishmael Reed)稱此關系為斑馬新聞學(zebra journalism),非黑即白,反之亦然(Gates 1997:119),既無灰色地帶,也難言是非對錯。正因為這種黑白涇渭分明的種族政治,蓋茨認為,“像辛普森這么一艘空船才會載滿意義,以及更多的意義——比我們任何人所能承擔的更多的意義”(122)。
在辛普森案判決的兩周后,伊斯蘭聯盟(the Nation of Islam)的領袖法拉干在華盛頓特區發起百萬黑人大游行,這場大游行以黑人男性為主,連激進詩人與劇作家巴拉卡(Amiri Baraka)也對此深不以為然,他說:“首先,我外出打仗時不會把一半的軍隊留在家里”(Gates 1997:114)。這樣的性別排他性使這次大游行的意義遠遜于1963年金牧師(Rev. Martin Luther King)所召集的那一次。1963年那場大游行顯然較具包容性。然而,盡管蓋茨在辛普森一案中看到美國黑白種族關系纏繞晦暗的潛在危機,他仍然希望藉這樣的危機厘清非裔美國人如何在這么一個轉瞬變化的時代與形勢中建立新的種族政治,以響應杜波依斯終其一生無時無刻不在思考的所謂黑人問題:“成為問題的感覺如何?”
側寫黑人伊斯蘭教領袖法拉干的一章透露了相當多的信息。法拉干無疑是位十足的黑人民族主義者,一向持偏激的種族立場。蓋茨在訪問他之后卻特別強調,“法拉干說我們必須學習越過膚色,超越人類的各種區域界線”(Gates 1997:135)。他還提到,法拉干說“他自己的許多親戚(包括他父親與祖父)膚色都較淺,因此他怎能因為人的膚色而憎恨他們?”(137)。蓋茨回憶法拉干的話指出,法拉干甚至“談到越來越能夠欣賞妥協,談到漸漸能夠了解民權傳統中對立意識形態者所持立場的價值”(151)。
《十三種觀看黑人男性的方法》一書的主導符碼是種族這個類別。蓋茨透過對不同非裔美國精英的側寫,以眾多大異其趣的敘事,反復審視種族這個類別,論證新的種族政治的迫切性與可能性,并嘗試以新的種族政治響應我在上文提到的與黑人問題相關的兩個議題,即地道政治和代表的重擔。蓋茨此書所部署的新的種族政治不禁讓我們想到1948年杜波依斯所提出來的新的“十分之一的杰出人士”:從杜波依斯到法拉干,蓋茨顯然有意告訴我們,新的種族政治,或者波斯諾克所謂的多元的普遍主義(Posnock 1997:323),恐怕已是現代黑人知識分子和領導階層的普遍信念。這或許正是《十三種觀看黑人男性的方法》一書所要傳達的最主要信息。
附注:
① 卡露裘(Dana Carluccio)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基本上同意阿皮亞對杜波依斯的批評。卡露裘從進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角度分析杜布埃斯《論種族的維護》一文中的種族立場,認為杜波依斯并未成功提出一套“非生物學的”有關種族的論述。卡露裘在其論文中更進一步論證杜波依斯的種族觀與達爾文進化論的關系(Carluccio 2009:511-18)。
② 黑人文藝運動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黑色美國影響深遠的藝術運動,與當時風起云涌的黑權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關系密切,這個運動的主要目的在透過文化與藝術實踐來強化非裔美國人的政治與社會自主性,其主導符碼是自哈萊姆文藝復興即開始萌芽的黑人文化民族主義(參見李有成2007:112;Ongiri 2010:22-23)。
Appiah, A. 1986. The Uncompleted Argument: Du Bois and Illusion of Race [A]. “Race,”Writing,andDifference[C]. In H. L. Gates (ed.).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1-37.
Carluccio, D. 2009. The Evolutionary Invention of Race: W. E. B. Du Bois’s “‘Conservation’ of Race” and George Schuyler’s “Black No More” [J].Twentieth-CenturyLiterature55 (4): 510-46.
Chandler, N. D. 2010. Of horiz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fro-American’ by W.E.B. Du Bois—circa 1894 [J].JournalofTransnationalAmericanStudies(2): 1.
Du Bois, W. E. B. 1965.TheSoulsofBlackFolk[M]. New York: Avon Books.
Du Bois, W. E. B. 1970. Address to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A]. In S. F. Philip (ed.).W.E.B.DuBoisSpeaks:SpeechesandAddresses, 1890-1919[C]. New York and London: Pathfinder: 124-27.
Du Bois, W. E. B. 1970. 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 [A]. In S. F. Philip (ed.).W.E.B.DuBoisSpeaks:SpeechesandAddresses, 1890-1919 [C]. New York and London: Pathfinder: 73-85.
Du Bois, W. E. B. 1996a. The Talented Tenth [A]. In H. L. Gates & C. West (eds.).TheFutureoftheRace[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31-57.
Du Bois, W. E. B. 1996b. The Talented Tenth Memorial Address [A]. In Gates, H. L. & C., West (eds.).TheFutureoftheRace[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59-77.
Du Bois, W. E. B.2010. The Afro-American [J].JournalofTransnationalAmericanStudies(2): 1.
Emerson, R.W. 1850.RepresentativeMen:SevenLectures[M]. Boston: Philips, Sampson and Company.
Gates, H. L. 1996a. Parable of the Talents [A]. In H. L. Gates & C. West (eds.).TheFutureoftheRace[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52.
Gates, H. L. 1996b. W. E. B. Du Bois and “The Talented Tenth” [A]. In Gates, H. L. & C. West (eds.).TheFutureoftheRace[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15-32.
Gates, H. L. 1997.ThirteenWaysofLookingataBlackMan[M]. New York: Random House.
Gates, H. L. and C. West. 1996.TheFutureoftheRace[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ngiri, A. A. 2010.SpectacularBlackness:TheCulturalPoliticsoftheBlackPowerMovementandtheSearchforaBlackAesthetic[M].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 of Virginia P.
Posnock, R. 1997. How it feels to be a problem: Du Bois, Fanon, and the ‘Impossible Life’ of the black intellectual [J].CriticalInquiry23 (2): 323-49.
Rampersad, A. 1996. Afterword: W. E. B. Du Boi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Studies [A]. In W. B. Bernard, R. G. Emily & B. S. James (eds.).W.E.B.DuBoisonRaceandCulture[C].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89-305.
Stepto, R. 1979.FromBehindtheVeil:AStudyofAfro-AmericanNarrative[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undquist, E. J. 1996. Introduction: W. E. B. Du Bois and the Autobiography of Race [A]. In E. J. Sundquist (ed.).TheOxfordW.E.B.DuBoisReader[C].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P: 3-36.
Washington, B. T. 1965.UpfromSlavery[M]. New York: Avon Books.
West, C. 1996. Black Strivings in a Twilight Civilization [A]. In H. L. Gates & C. West (eds.).TheFutureoftheRace[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53-112.
李有成.2007.踰越: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批評[M].臺北:允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