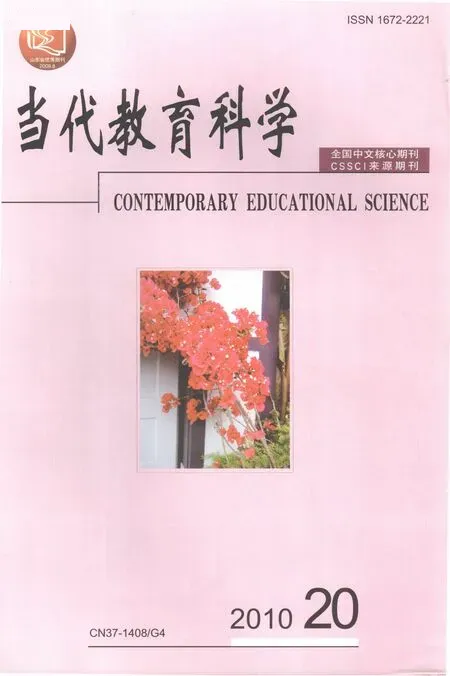教學公平:追求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
● 于世華
教學公平:追求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
● 于世華
教育公平在實踐的微觀層面上是課堂教學的公平。教學公平必須改變傳統課堂資源的教化功能為體驗功能。課堂資源的教化功能帶來的學生發展是不公平的,隨著課堂資源的無限豐富,教學不公平越來越呈現惡化趨勢。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映射出教師與學生的公平、產生了教與學的公平、展現了學生主體性的公平。課堂資源體驗功能的形式載體有:生活世界中的情境體驗與生命體驗;課堂交往中的對話體驗與價值體驗;課堂活動中的游戲體驗與審美體驗。
教學公平;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體驗的形式載體
教育公平在實踐的微觀層面上是課堂教學的公平。課堂教學的傳統辦法是抓兩頭促中間,然而,即使學生是橄欖狀的正態分布,在教學起點上也沒有做到公平,因為教師準備的教學資源是為一部分學生服務的。教師的教總是有針對性的,好比舞臺上的聚光燈總是投向特定的區域,只有該區域的物體才能顯示出色彩,而教學公平應該是陽光普照、萬物生輝。改變傳統課堂資源的教化功能為體驗功能,才能實現教學的陽光普照、萬物生輝,為教學公平開辟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一、課堂資源教化功能的不公平性及其惡化趨勢
課堂資源是教師在課堂上使用的以學生發展為目標的所有文本、活動、情境、話語等教師課前預設性材料和課堂運行過程中的生成性材料。課堂資源的傳統開發主要著眼于教師的教,突出其教化功能。教師對教材的使用總是鐘情于文本中的 “大字”,喋喋不休,反復強調,分析課文表達了哪幾層含義,各層含義的內在邏輯,而文本中的探究活動、相關鏈接、專家點評都是“輔文”,是為教材“大字”服務的。課堂探究活動直指生成的知識點,而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值觀都是“虛體”,只能靠實體的知識承載。展示的生活情境(包括文字、圖片、視頻等資源)往往是知識生成的“引子”,一旦大功告成就會棄之一邊,不再顧及。師生、生生對話是在教師的逼迫與誘導下,向著既定的目標奔去,假如有大膽學生表達了真實主觀感受的奇談怪論,教師要么避而不談,要么運用話語策略搪塞一下。
課堂資源的教化功能帶來的學生發展是不公平的。學生被看成一張白紙,等待教師來灌裝知識的容器,學生究竟能盛多少知識取決于教師的灌輸,這種灌輸表面上看是公平的,因為教師面對全班學生平等地提供教學資源,但資源的消化、吸收程度是由學生的內在心智結構規定的,課堂資源的教化功能傾向于語言和邏輯數理智能。加德納在他的心理學專著《智能的框架》中提出了7種智能,后來又提出兩種,他強調,人的才能是多元的,每個人都不同程度地擁有八種或九種智能,有的是強項,有的是弱項。因此,課堂資源的教化功能在學生發展的起點、過程、結果都傾向于語言和邏輯數理智能較強的學生,而對于語言和邏輯數理智能較弱的學生來說是不公平的。
現階段,課堂資源大為豐富,但在教與學的二元結構下,其教化功能的不公平性卻越來越呈現出惡化趨勢。在以印刷為媒體的文化傳播中,課堂資源的教化功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學習者接觸到的學習資源較少,使必須依靠大量資源的自學成為不可能,只得需要專門的教師傳授;另一方面,文字符號構成的學科知識需要讀者面對印刷媒體進行沉思,你要對抽象的文字進行解碼,需要冷靜客觀地面對文字,尋著教材的思路才有對文本的深層次理解。這都為課堂資源教化功能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礎。隨著網絡計算機的出現,人與人之間的隨時溝通成為可能,人們輕而易舉地就可以獲得想要的學習資源,可以說,只要你想得到,就能在網上搜得到。與舊的教學媒介相適應的課堂資源教化功能,在新教學媒介下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學生不再是孤陋寡聞的幼稚的無知物,他們在某一領域比教師知道的更多。教學資源的無限豐富并沒有帶來學習主動性的增強。在教與學的二元結構中,課堂資源的教化功能突顯了教師的教占有主導地位,教學是基于教育者信條的。“基于教育者信條的學習范式普遍呈現出他律性、強制性、排斥性品質,不僅導致學習意義的普遍失落,而且造成嚴重的逃避學習、恐懼學習、厭惡學習現象。”[1]當教師的教占有主導地位,面對無限豐富的課堂資源,一方面學生作為學習主體無法對課堂資源進行能動反應,另一方面呈現的課堂資源對學生發展的影響也不敏感。這意味著,在課堂資源無限豐富時,學生學習主體性提高不夠顯著,豐富的課堂資源帶來的利益大部分轉化為教化功能而非體驗功能,從而使教學不公平越來越呈現惡化趨勢。
二、課堂資源體驗功能的教學公平效能
(一)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映射出教師與學生的公平
人類的發展是在實踐中發展的,實踐是在實際情境下靈動、明智的行為,沒有外在目的性,而是一種內在的連續性的行為。像人類面對金融危機、海嘯地震、疫病流行,還是面對風晴日麗下長勢喜人的農作物,都是與情境的協作。人類在新文化傳媒下與情境的協作能力如何?學生的能力可能超過教師。在教學提供的作為人之成長的集約化和職能化的環境中,同樣,學生與情境的協作能力也不會低于教師。比如,你熟悉乘哪路車由南京站到新街口,現在繼續乘這路車就不是學習,你改乘從來沒有乘過的地鐵才是學習,教師要事先打聽好如何乘地鐵,但是直接領著學生上地鐵就沒有發揮學生的主體體驗,而應該讓學生找地鐵口、購票、上車、出站,學生可能比教師做得更好。所以,強調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還原了人類活動的實踐性,發揮了學生與課堂情境的協作能力,充分彰顯了學生學習的主體性,擺脫了教師教的強勢地位,實現了教師與學生的公平。
(二)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產生了教與學的公平
“體驗是通過實踐獲得的經驗和情感,是個體不可替代的形成意義的方式。”[2]體驗只能在人類實踐中獲得,紙上談兵的教化獲得的只能是看法或感受,而不是體驗。只有游桂林山水,才有對桂林山水的體驗。實踐活動是人們改造客觀世界的一切活動,教學實踐的目的性在教學活動中,是面對課堂情境解決問題。傳統上認為,教師教學是實踐,教師改造了學生的主觀世界(對教師來說是客觀的),而學生學習不是實踐,因為學生僅僅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對教師的主觀世界(對學生來說是客觀的)沒有改造,因此,傳統教學論在實踐層面上就將學生排除在實踐之外,排除在體驗之外。體驗的內涵在起點上就將教師和學生推向了教與學交互作用的過程。教與學是如何交互作用的呢?是通過對課堂資源的體驗獲得的。學生在課堂資源的體驗中不僅對自身原有的經驗產生影響,而且還作用于教師,是引起教師下一步如何教的促進因素,這就延伸出學的實踐性。所以,學生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教師教的教育者,教師既是教育者又是學生學的受教育者,這里的教與學都是實踐。如果學不是實踐,學生就沒有體驗,教師就成了高高在上的傳道者,而學生只能是俯首聽命的臣民,沒有師生的教與學的公平就沒有教學的公平。歸根到底,課堂資源體驗功能的喪失是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和結果。
(三)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展現了學生的主體性
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將教與學的壟斷地位打破,讓教師、學生真正回歸到作為實踐著的人的地位,使人的實踐性本質的主體性得以弘揚。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是將學生和教師都作為整體的、具有原創性的人來對待,學習是一個積極的自組織、自我建構的過程,是以人與外界發生作用的原初經驗與情感為基礎的,而這一點是每個人都具有的,學生的情感世界尤其純真、熾熱。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指出“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對課堂資源的體驗就是為學生的想象與思維活動提供極其豐富的材料,使他們有可能去組合、去創造新的形象。體驗中的人所抒發的、傾訴的、流露的、交融的情感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心理世界,進而影響學生潛能的開發。所謂“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課堂資源中所蘊含的豐富的情感因素觸及學生的心靈,在廣遠的意境中,進入“神與物游”的神奇美妙的境界。注重課堂資源的體驗是“順其天性而育之”,學生身上所呈現的那種永不怠倦的向上性和不可遏制的積極參與的主動性令人嘆服。
三、構筑課堂資源體驗功能的形式載體
對課堂資源的體驗形式研究有較多的文獻資料,大概分為三類,一是教材體驗,如,體驗引子、體驗沖突、體驗游戲、體驗反思、體驗行動[3];二是生命體驗,如,引導學生在生活世界中體驗生命,在道德主體間的相互理解中豐富生命,在真實的生命表達中展現生命[4];三是教學體驗,如,文本體驗、活動體驗、情境體驗、回憶體驗、共享體驗、建構體驗[5]。筆者以為,從課堂資源的體驗功能的公平性看,體驗形式應從師生兩條線對課堂資源進行分類、概括。一般地,學生體驗傾向于課堂資源的客體方面,多為教師提供的預設性課堂資源。教師體驗傾向于學生對課堂生成性資源的體驗,即對學生體驗的再體驗,簡單地說,就是對學生生命的體驗。從課堂實際運行來看,有生活世界中的情境體驗與生命體驗、課堂交往中的對話體驗與價值體驗、課堂活動中的游戲體驗與審美體驗。
(一)真實的教育生活世界是情境體驗與生命體驗的形式載體
教學生活雖與社會生活不同,具有生活情境集約化和教育的功能化,但教學生活作為師生生命親歷和體驗,需要教師營造一個真實的教育生活世界,教學才有生命追尋的過程。例如,教學《文化生活》,為了讓學生體驗多樣的文化生活是有好有壞的,要有判斷、選擇的能力,教師展示了正面的本校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建設,還有反面的“死亡筆記”、“筆仙拜佛”,以及校園攀比現象等。教師用發生在學生身邊的真實故事呈現問題,營造問題解決的環境,使課堂生活富有人情味、生活味,而不是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的知識冰冷面孔。學生的體驗也是真實的、開放的、甚至是挑戰性的,但都浸潤著學生的思想和心靈。在這里,生命是一切教育活動的起點,教師要明白學生的生命感受、內心體驗,對個體生命充滿溫情與呵護。學生的情境體驗可能有成功與收獲,也可能是失敗或倒退,如果教師輕易肯定或否定都會抹殺學生生命個體獨有的體驗與經歷。教師應尊重學生自我選擇的權利,寬容學生的失敗,并作積極的價值引導,以培育每一個學生獨特的生命情態。
(二)結構不良和開放性問題是對話體驗與價值體驗的形式載體
設計一些相關的結構不良和開放性問題,對于鼓勵學生大膽質疑、主動進行意義建構都是非常有成效的。例如,教師提出:“既然文化生活中的陰影是有害的,那它為什么還會存在呢?”這是一個真實的、開放性的問題。本來教材中的知識會給學生現成的答案,但在這個結構不良的開放性的問題下,必然會激起所有參與者進行有意義對話,教師的價值引導不再是定論式的陳述,而是循著學生對話的思路走下去,對教材進行適當的整合和發展,讓教材中的知識不斷創造師生對話的“起點”。在學生對現象感悟的基礎上,完成對落后腐朽文化存在原因的分析,從而理解落后、腐朽文化的存在是有客觀原因的,這里要注意對學生進行分析問題的思維能力訓練,比如主客觀角度、正反的辨證思維等。教學的前提是對學生的了解,教學的實質是引導學生學,不讓學生真實表達自己的觀點,怎么了解學生?怎么引導學生學?結構不良和開放性問題成了師生對話和教師價值引導的載體,在“和而不同”對話的原則下,對話是一種平視,任何對話的參與者都必須始終尊重他者,希望達到的是視域的融合,因此,每一個參與者都在必要的精神交鋒與互換中保持著個體的平等、公平,不受歧視。
(三)課堂上學習者的活動是游戲體驗與審美體驗的載體
筆者在講授高中思想政治選修三《國家與國際組織》時,讓出課堂的一半時間由學生介紹自己事先選好的某一個國家或某一個國際組織,從自主選擇上就看出學生有著極大的主體性,如一個洪姓學生選的國家是洪都拉斯,另一個學生選的是新西蘭,因為她去過,還有學生介紹世博會上的世界竹藤組織。學生對自己課件的保密程度不亞于央視的春節聯歡晚會,我想事先打聽一下,學生都是模糊地告訴我:馬上講的時候,您就知道了。學生在介紹某個國家政體或國際組織的時候,他(她)就已經熟悉了政體的組織結構或國際組織的宗旨目的、組織機構、作用等教材上那些僵死的符號化的條文,因此,學生活動擴大知識運用范圍,促進知識正遷移。教學實踐活動不是勞動隱喻,而是游戲的隱喻;不是傳授,而是參與;不是學科內容,而是文化;[6]例如,在學生獲得如何做出正確的文化選擇,抵制文化污染,奏響文化主旋律的策略基礎上,讓教材的知識學習再次回到實踐,把課堂學習落實到自己的文化生活中去,設計學習活動:在申奧成功的第一時間,我校就成立了“青奧行”志愿者服務隊,世界青奧會必將成為展現各國青年人的文化舞臺。那么,你會做怎樣的準備呢?“文化青奧”之路,就在你我的腳下!學習者的活動將會激活人的感知覺、記憶、情感和想象力,激活人的創造潛能,使學習成為聯想和激情的創造活動。正如,馬克思所說,美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外顯。只有學生參與課堂活動,其本質力量才能得到外顯,在活動中,感性與理性達到高度統一,學生能獲得一種審美感受,這種審美感受將學生帶向無限的創造天地。
[1]郝德永.學習者信條與學習范式的重建[J].教育研究,2008(12):56-61.
[2][5]王木丹,王彥.解放學習中的人:教育學行動與體驗的人文追求[J].教育研究,2009(10):37-41.
[3]趙飛,劉驚鐸.體驗式教材:德育教材新樣態[J].教育研究,2006(7):74-78.
[4]劉濟良.生命體驗:道德教育的意蘊所在[J].教育研究,2006(1):27-30.
[6]鐘啟泉.教學活動理論的考察[J].教育研究,2005,(5):36-42.
于世華/南京市第十三中學,中學高級教師,教育碩士
(責任編輯:劉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