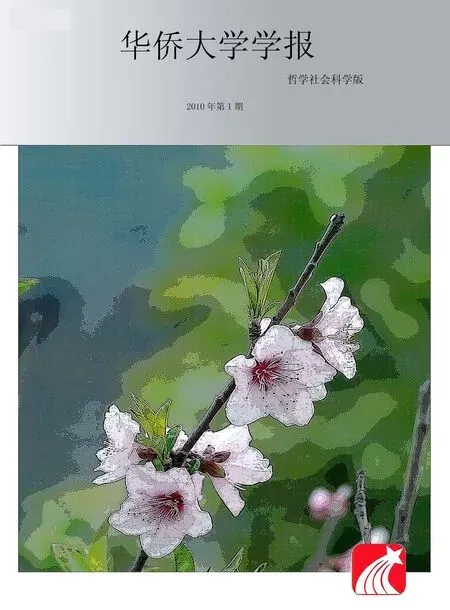中文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法律地位
——從中國入世法律文件的翻譯差錯談起
○陳儒丹 黃 韜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一 中國入世法律文件中的翻譯缺陷
經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公布的中國入世法律文件的譯本在其出臺之時就被認為存在諸多翻譯錯誤。[注]中國入世文件英文文本是經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批準并公布的,但中文文本只是公布并沒有經過批準程序。以《中國入世議定書》附件9之服務貿易部分譯文為例,其在詞的翻譯上有誤,比如將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翻譯為“自然人流動”;對于三資企業的稱謂,明明有我國國內法律所確定的名稱,即外商投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以及中外合作企業(后二者一般可合稱為中外合營企業),但在這里卻被譯為了“外資、股權式和契約式(后二者為合資)”,顯然會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此外,《中國入世議定書》附件9之服務貿易部分譯文意思傳遞上也不十分遵從原文:首先,有添加。譯文針對附件9有“僅以英文為準”的表述,而在英文的法律文件中根本沒有如此的話語(這種翻譯方法似乎是讓讀者不必過度依賴中文?但其后果可能是會遭到法語國家和西班牙語國家的不滿,畢竟WTO的官方語言有三種,而不只是英語)。其次,有省略。例如,將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 shall not employ Chinese national registered lawyers outside of China翻譯為“代表處不得雇傭中國國家注冊律師”。這里略去了outside of China,是故意為之,還是擔心理解有誤?僅附件9之服務貿易部分譯文就存在如此多的誤差,而這部分譯文僅僅占到《中國入世議定書》全部內容的22%而已。
2005年,中國在激烈的國際紡織品貿易摩擦中之所以一直處于不利位置,其中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來自譯文的不準確。具體體現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工作組報告》第242段的“紡織品特別設限”,其中就存在兩處關鍵的翻譯缺陷,即第242段(d)項和第242段(f)項。
第一處翻譯缺陷出現在第242段(d)項,中文譯本的表述是“如在90天磋商期內,未能達成雙方滿意的解決辦法,則磋商將繼續進行,提出磋商請求的成員可繼續根據(c)項對磋商涉及的一個或多個類別的紡織品或紡織制成品實行限制。”
其所對應的英文原文是If no mutually satisfactory solution were reached during the 90 day consultation period, consultations would continue and the Member requesting consultations could continue the limits under subparagraph (c) for textiles or textile products in the category or categories subject to these consultations.
而其中被引用的第242段(c)項的英文原文是Upon receipt of the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China agreed to hold its shipments to the requesting Member of textile or textile products in the category or categories subject to these consultations to a level no greater than 7.5 percent (6 percent for wool product categories) above the amount entered during the first 12 months of the most recent 14 months preceding the month in which the request for consultations was made.
可見,第242段(d)項…the Member requesting consultations could continue the limits under subparagraph (c)…是指維持第242段(c)中已經實施的…China agreed to hold its shipments … to a level…即維持中國實施的自動出口限制的狀態,而不是第242段(d)項中文譯本所說的“提出磋商請求的成員可繼續根據(c)項……實行限制”。若將第242段 (d)項將名詞性質the limits翻譯成“實行限制”,就等于賦予了向中國提出磋商的WTO 成員在只要提起磋商的前提下,可以通過本國或本地區海關,直接對原產于中國的磋商項下的產品采取任意數量限制措施的權利。但是,第242段(d)項英文原文的表述是…the Member requesting consultations could continue the limits under subparagraph (c)…據此提出磋商的其他WTO 成員只有要求維持根據第242段(c)項中國已經承諾的水平的權利,其主動權還是由中方掌握。所以,第242段(d)項將英文原文中名詞性質的limits譯為動詞“實行限制”,根本上改變了磋商方與中方的權利義務,是一個嚴重的法律誤釋。[1]48
第二處翻譯缺陷則出現在《加入工作組報告》的第242段(f)項。該條款的中文譯本表述是“根據本規定采取的行動的有效期不得超過1年,且不得重新實施,除非有關成員與中國之間另有議定……”而對應的英文原文是No action taken under this provision would remain in effect beyond one year, without reapplication,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Member concerned and China; and…由于reapplication這個詞本身有“再適用”和“再申請”兩種含義,如果翻譯成“根據本規定采取的行動的有效期不得超過1年,且不得重新實施”則表明行動有效期只能少于或等于一年(這也是中方在談判的觀點);而如果翻譯成“未經重新申請,根據本規定采取的行動的有效期不得超過1年”則表明只要重新申請,采取的行動的有效期就可以超過一年(談判對方的觀點)。因此這個翻譯問題會對雙方的權利義務造成本質上的影響,事實上這也是中歐、中美談判過程中的重大分歧點。筆者認為將reapplication譯作“再申請”才是正確的,理由如下:
雖然reapplication這個詞在英文中本身有“再適用”和“再申請”兩種含義,但在這里“No reapplication”表達的是一個前提,一個條件,不應該被翻譯成“不可重新實施”,而應該被翻譯成“沒有再申請”更恰當。
另外,without一詞本身有五種常用含義,分別是(1)not having, experiencing or showing, in the absence of;(2)not accompanies by;(3)not using;(4)與-ing形式后綴連用表示“不”、“沒有”等意思;(5)outside。查遍這五種含義的例句會發現without既可以表達一個前提條件,也可以表達一個狀態,當without表達一種狀態的話,該狀態是先于without之前的動作已經發生的或者與without之前的動作同時發生的,而不是將來的未發生的。[2]1748對照第242段的翻譯,“重新實施”必然要以初次采取行動為前提,必然是一個“根據本規定采取的行動”之后的動作,而不是之前已經發生的動作,可見第242段中without reapplication翻譯成“且不得重新實施”是不符合without的一般用法的,而作為前提條件看翻譯成“未經重新申請”才比較合適。就算作為狀態翻譯成“且不得重新實施”的話,without也應該直接與No action taken under this provision would remain in effect beyond one year相連,而不應該被逗號隔開,但是事實上英文文本中這兩者之間是用逗號隔開的。
二 入世文件中文譯本的法律效力
上文提到的翻譯缺陷并沒有呈現對中國總是有利或對中國總是不利的傾向(例如第242段(d)項的中文譯本是不利于中國的,而第242段(f)項的中文譯本卻是有利于中國的),因此可以推斷中文文本的翻譯缺陷并不是因為滿足某個先定的傾向性的立場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語言意思傳遞與表達以及翻譯必然存在的疏忽引起的,也可以看作是不同語言之間的固有差異引起的。
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就是關于同一事項的WTO不同語言文本之間出現了差異到底以哪一個為標準,例如第242段是以英文為準還是以中文為準。或者更簡單的講,入世文件中文譯本的法律效力到底如何?
在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體系中具有最高效力的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16條雜項條款第6款規定:“本協定應依照《聯合國憲章》第102條的規定予以登記。1994年4月15日訂于馬拉喀什,正本一份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寫成,三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由此可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中文不是官方語言,盡管中文一直是聯合國的官方語言。
而《中國入世議定書》第三部分最后條款中的第4條規定了“本議定書應依照《聯合國憲章》第102條的規定予以登記。 2001年11月10日訂于多哈,正本一份用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寫成,三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除非所附減讓表中規定該減讓表只以以上文字中的一種或多種為準。” 可見中文版的《中國入世議定書》在世界貿易組織法律體系之中是沒有效力的。
從《建立在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和《中國入世議定書》的相關規定可以推知,中國公布的加入WTO相關英文法律文本是直接約束中國的法律文件,而且英文版的議定書和工作組報告是WTO法律的一部分,而中文版本則只是個參考。而另一方面,從中國立法程序看,中國入世法律文件中文文本既不是我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也不是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因此它也稱不上是我國的法律。
而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工作組報告》第334段規定了:“中國代表確認,中國將使WTO成員獲得譯成一種或多種WTO正式語文的所有有關或影響貨物貿易、服務貿易、TRIPS或外匯管制的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并將盡最大可能在實施或執行前,但無論如何不遲于實施或執行后90天使WTO成員可獲得這些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工作組注意到這些承諾。”[3]46這也就表明不僅中文版中國入世法律文件沒有任何法律效力,所有的中文版的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在世界貿易組織中都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確定效力,都必須經翻譯成WTO官方語言并使之處于其他WTO成員可以獲得的程度才能獲得WTO體制內的法律效力,在未來發生貿易爭端時可以援引。單純的中文版法律、法規及其他措施在WTO體制內應該是無效的,不足以作為援引的法律證據。
可見,在目前的現狀下,不管第242段的中文譯本是否有利于中國都一概的無效,當中文譯本與用WTO官方文字形成的文件出現沖突時應一律以目前的WTO官方文字文本為準,換句話說,也就是說以英語、法語、西班牙語文本為準。
考慮到WTO法律文本的篇幅巨大,又大量使用了專業性強而略帶晦澀的“法言法語”,再加之東西方語言之間的天然差異和各成員法律傳統與法律體系的不統一,因此很難保證各種語言文本之間在轉化之后仍然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基于同語言文本的不同理解而產生爭議對于非英語、法語或西班牙語國家來說幾乎都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僅是一個翻譯技術的問題。
面對這樣的一個現實,我們或許應當轉換一個思路,即如何從WTO法律的制度層面來減少中國翻譯者(他們未必是專業的法律工作者)因為對WTO外文文本的不正確理解和不適當翻譯而給我國外經貿領域工作帶來的損失和不便利。
一個可行的努力方向就是力爭將中文升級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官方語言,使之成為WTO條約及其附件的作準文字。一旦這樣的假設成為現實,那么將外文文本的WTO法律文件翻譯成中文的目的就不再只是為了方便中國一國內部的使用,而是成為WTO各機構的一項常規工作,因而其人力物力保障可以得到提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期待減少誤譯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即使出現了中外文本涵義的不一致,由于中文已經“入世”,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3條第3項的規定,條約的條款應當推定為在各作準約文中具有同一意義。[4]206因此,從條約法律的角度來分析,一旦中文被接納為WTO官方語言,中文本的WTO法律文件不再是中國內部使用的參考文本,而是具有了嚴格法律拘束力的WTO官方文本,其效力和英文本、法文本以及西班牙文本的法律文件具有同等的效力,中方在WTO談判或者爭端解決過程中可以直接援引中文本文件作為法律依據。
三 中文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升級為官方語言的程序
目前,中文在世界貿易組織中還沒有正式的法律地位,與之呈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世界貿易總量中的比例日益上升,中文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法律地位勢必不能滿足中國的需要,也不能滿足亞太地區貿易乃至全球貿易發展的需要。那么中文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升級為官方語言的可能性究竟為幾何呢?
2006年4月13日,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干事Miguel Rodriguez Mendoza視察了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WTO信息查詢中心。在聽到中改院信息查詢中心一直致力于翻譯由WTO總部每日發來的獨家世界貿易新聞、規則、案例等文件,并及時通過互聯網向政府、企業和公眾提供之后,Mendoza先生稱他個人認為,未來中文可能成為WTO的官方語言,因此,中改院WTO信息查詢中心前期所作的大量翻譯將為此提供一個很好的基礎。這或許只是外交辭令,但至少傳達了這樣一條信息,即世界貿易組織官員已經意識到中文有必要且有可能成為WTO官方語言,這對中國、對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問題的關鍵是法律程序上能否運作,也就是說WTO法律文件中能否找到使中文上升為WTO官方語言的程序,或者說是一種渠道。
幸運的是,《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10條(修正條款)第1款規定:“WTO任何成員均可提出修正本協定或附件1所列多邊貿易協定條款的提案,提案應提交部長級會議。第4條第5款所列各理事會也可向部長級會議提交提案,以修正其監督實施情況的附件1所列相應多邊貿易協定的條款。除非部長級會議決定一更長的期限,否則當提案正式提交部長級會議后90天內,部長級會議應經協商一致作出任何有關將擬議的修正提交各成員供接受的決定。除非第2款、第5款或第6款的規定適用,否則該決定應列明是否適用第3款或第4款的規定。如協商一致,部長級會議應立刻將擬議的修正提交各成員供接受。如在確定期限內,在部長級會議的一次會議上未能協商一致,則部長級會議應以成員的三分之二多數決定是否將擬議的修正提交各成員供接受。除第2款、第5款和第6款的規定外,第3款的規定適用于擬議的修正,除非部長級會議以成員的四分之三多數決定應適用第4款的規定。”
將中文排除在WTO官方語言之外的條約依據是《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16條雜項條款第6款。也就是說規定只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是WTO官方語言的《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16條雜項條款第6款是屬于該協定第10條(修正條款)第1款規定中的可修正范圍內的“本協定”的條款。
因此,根據《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10條(修正條款)第1款規定,任何成員包括中國在內的成員國以及《馬拉喀什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4條第5款所列各理事會,即貨物貿易理事會、服務貿易理事會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理事會都有權向部長級會議提出修改第16條雜項條款第6款,要求增加中文為WTO官方語言的提案并按照第10條第1款的程序進行表決通過。
四 中文成為WTO官方語言后WTO不同語言版文件分歧的解決
如果按照上述的程序,中文將可能成為WTO官方語言,進而使得中文文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具備法律上的效力,而且根據《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第16條雜項條款第6款有關三種官方語言具有平等效力的規定,若中文成為未來WTO官方語言之一,和其他官方語言的關系肯定也是平等的。但是,由于以不同語言表述而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文有多種,但條約本身卻只有一個,因而翻譯所導致約文意義的分歧必然存在(這種分歧會隨著官方語言的增多而加劇),而且這種譯文上的不統一或者歧義對國際貿易爭端各方在爭端解決中權利義務地位產生影響的情況也很可能會發生。[5]1-24如果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那任何WTO官方語言“擴軍”的提案都會遭到順理成章的反對。
那么根據現行國際法(包括但不限于WTO法律體系規范)對于這個問題是又是如何闡釋的呢?
世貿組織《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第3條第2款規定:“WTO爭端解決體制在為多邊貿易體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預測性方面是一個重要因素。各成員認識到該體制適于保護各成員在適用協定項下的權利和義務,及依照解釋國際公法的慣例澄清這些協定的現有規定。DSB的建議和裁決不能增加或減少適用協定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那么什么是“解釋國際公法的慣例”呢?在美國汽油案中,上訴機構明確地確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所規定的條約解釋總原則已經獲得國際慣例的地位,所以,它是那些有關國際條約解釋慣例性規則的一部分。在日本酒精類飲料稅案中,上訴機構認為關于輔助解釋方法的第32條也已經獲得了同樣的地位,并認為“《維也納條約法公約》是國際法慣例的編纂,因而約束所有的國家。”[6]248-298
因此,雖然條約只有一個,不同語言的約文有多種,按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3條第3項的規定,條約的條款應當推定為在各作準約文中具有同一意義。按照該條第4項的規定,條約解釋者應當將各作準約文予以對照比較;對照比較的結果發現各約文具有不同的意義時,應當適用第31條和第32條兩條規定的解釋規則予以解釋;適用該兩條解釋規則尚不能消除意義的分歧時,就應參照該條約的目的和宗旨,賦予最能調和各約文的那種意義。[7]363最終應該參照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的目的和宗旨來調和各約文的意義,解決因為語言差異所引起的法律分歧。
參考文獻:
[1] 黃東黎. WTO規則運用中的法治——中國紡織品特別保障措施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 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M]. 北京:商務印書館;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3] 曹建明, 賀小勇. 世界貿易組織[M].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
[4] Louis Henkin.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s and Values[M]. Dordrecht,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5.
[5] John Jackson. Glob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998, Vol.1.
[6] James Cameron, Kevin R Gray.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02, Vol. 50.
[7] 李浩培. 條約法概論[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