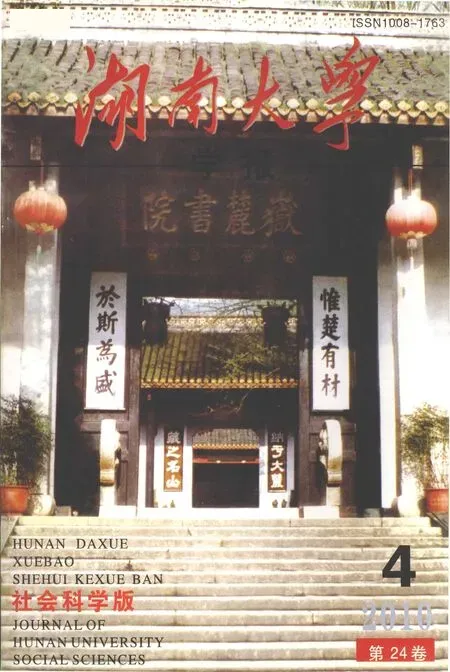淺談出土律令名目與“九章律”的關系*
于振波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淺談出土律令名目與“九章律”的關系*
于振波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湖南 長沙 410082)
根據傳世文獻,“九章律”作為漢代的律典是確實存在的,其篇目為九篇,也是無可否認的。與其通過否定“九章律”的存在來解決出土律令名目與“九章律”篇目不相應的問題,還不如另辟蹊徑。“律篇二級分類說”雖然還有待完善,但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另一種思路,而且不會與傳世文獻發生太大的矛盾。
出土律令;傳世文獻;九章律;律名;法律篇章
Abstract:According to extant ancient books,Jiu-Zhang Law had been indeed as law book of Han Dynasty,w hich w as composed of 9 chap tersw ithout question.We’d better search fo r another w ay rather than deny the existence of Jiu-zhang Law in order to exp lain the p roblem that the titlesof law s and decrees in unearthed documents do not co rrespond to the sections and chap tersof Jiu-zhang Law.The view of subclassification under chap ters of law p rovides a new way to solve the p roblem.
Key words:Law s and decrees in unearthed documents;extant ancient books;Jiu-zhang Law;titles of legal articles;sections and chap ters of law
史載,戰國時,李悝助魏文侯變法圖強,作《法經》六篇,即《盜》、《賊》、《囚》、《捕》、《雜》、《具》。秦孝公時,商鞅以《法經》為藍本,作秦律。漢興,蕭何捃摭秦法,增加《興》、《廄》、《戶》三篇,作九章之律。[1](P922)因此,漢代的主要法典歷來被稱為“九章律”。然而,睡虎地秦簡出土以后,尤其是張家山漢簡出土以來,由于簡牘上所見秦、漢律名已遠遠超過上述九個,于是有學者對漢律的篇章結構重新展開討論,甚至對“九章律”是否真實存在、“九章”之“九”是虛數還是實指,提出了質疑。楊振紅已對各家代表性觀點做了很好的綜述。[2]
質疑“九章律”的各家論點,綜合起來大致為:第一,出土秦漢法律資料所提到的律名有幾十個,遠遠超過九個,“九章律”容納不下這么多律名;第二,《史記》、《漢書》等留傳至今的漢代文獻都沒有提到“九章律”這個名字,說明當時沒有“九章律”;第三,《漢書·刑法志》、《論衡·謝短篇》提到過“九章”,這里的“九”只表示“多”,不是實際數字;第四,明確提到“九章律”的文獻,如《晉書·刑法志》、《唐律疏議》等,都是成書較晚的文獻,不足為據。本文認為,目前的出土資料尚不足以否定傳世文獻的價值和傳統觀點。試述如下。
一 律名未必等于篇名
不論傳世文獻還是簡牘中,都曾出現過很多律名。問題是,這些律名是否都是律典的篇名?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分別考察一下傳世文獻和簡牘中出現的若干律名。
(一)傳世文獻中出現的律名
1.“收孥諸相坐律令”
《史記·孝文本紀》: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3](P419)
“收孥諸相坐律令”在《漢書·文帝紀》中作“收帑相坐律令”,[4](P110)在《漢書·刑法志》中作“收律相坐法”,[4](P1105)所指應系同一類律令,名稱大同小異。說明當時人對這類律令的命名并不強求一律。《集解》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有“收律”,錄有律文五條,應屬于此類律令的一部分。據此可知,“收孥諸相坐律令”為相關律令的總稱,而且,并非所有犯罪,家屬都要連坐。[5]
2.“販賣租銖之律”
《漢書·食貨志下》: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揺,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錢。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農桑。”[4](P1176)
在《漢書·貢禹傳》中也有相關記述,其中的“租銖之律”,[4](P3076)無疑與上文中的“販賣租銖之律”是同一類律文的不同稱謂。顏師古注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錙銖而收租也。”則此“販賣租銖之律”應與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之“金布律”有關。是否為“金布律”的另一種稱謂,或僅指“金布律”的一部分,則不得而知。
3.“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漢書·景帝紀》:(景帝中元六年)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4](P148)
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偽金,偽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誑耀,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二年律令·錢律》中有關于盜鑄錢和為偽金方面的規定,[6](P159-161)因此景帝所定“鑄錢為偽黃金棄市律”應當屬于“錢律”的一部分。
4.“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后漢書·光武帝紀下》:(建武十一年)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7](P58)
奴婢射傷人,應屬于“賊律”。“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只是一條具體律文的名稱。廢除此律的目的在于減輕對奴婢的懲罰。
5.“挾書律”
《漢書·惠帝紀》:(四年)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4](P90)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三十四年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令焚書,并禁止私人收藏《詩》、《書》、百家語。[3](P254-255)此“挾書律”應系根據相關詔令制定的法律。這一法律似乎不太可能構成秦律法典的一篇,而很可能只是某篇中的一條或幾條。蕭何在采擷秦法編纂漢律時,保留了這部分律文,直到漢惠帝時廢除。
傳世文獻中所出現的律名不止于此。上述律名,有的表示若干條相關法律的總稱,有的表示某條律文的名稱,而并非都表示律典的篇名。
(二)律令類以外簡牘中出現的律名
律令類以外的簡牘中也出現很多律名,基本情況與傳世文獻差不多。例如:
囚律:告劾毋輕重,皆關屬所二千石官。(居延EPT10:2A)[8]
捕律:亡入匈奴、外蠻夷,守棄亭鄣逢燧者不堅守,降之,及從塞徼外來絳(降)而賊殺之,皆要斬,妻子耐為司寇,作如(敦煌983)[9]
上述兩條簡文中提到的“囚律”和“捕律”,是漢代律典的正式篇名,當無異議。再如:
捕律:禁吏毋夜入人廬舍捕人,犯者,其室毆傷之,以毋故入人室律從事。(居延395.11)[10]
“捕律”為漢律篇名,已如上述。“毋故入人室律”則是某條律文的名稱。[11](P153-154)
再看居延漢簡中EPF22:1-2這兩枚簡所引述的一條律文:
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都鄉嗇夫宮以廷所移甲渠候書召恩詣鄉。先以證財物故不以實,臧五百以上,辭已定,滿三日而不更言請者,以辭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8]
這是官吏斷案時首先向被審訊者宣讀的一條法律,高恒先生認為屬于“囚律”。[11](P150)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具律》有如下條文:
證不言請(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獄未鞫而更言請(情)者,除。吏謹先以辨告證。[6](P149)
居延漢簡中所引述的這條律文,與《二年律令·具律》相比,內容更加詳細具體,是否也屬于“具律”,尚無法確定。需要指出的是,這條律文的名稱可能也不固定。居延簡3.35中提到“證不言請出入罪人律”,[10]簡 EPT52:417中提到“證不請律”,簡EPT53:181中提到“證財物不以實律”,[8]這些簡牘本身不夠完整,未見引述具體律文,從名稱推斷,可能都是指上述簡EPF22:1-2所引述的那條律文。
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所殘存的漢律目錄也很值得關注。[12]這批簡牘的第4號正面有“永元元年正月”簡文,“永元”為東漢和帝年號。因此這批簡應當屬于東漢中期的遺存。
其第29號簡正面共六欄,文字大多漫滅,仍能看出屬于漢律目錄。其中第一、二兩欄為“盜律”目錄,能辨識者如:驕□□、詐發□、盜□□、殺人□□、盜出故(?)物、諸詐始入、□亡□;第三至六欄為“賊律”目錄,能辨識者如:詐 □喪、揄封、毀封、諸食 □肉、賊殺人、斗殺以刀、戲殺人、謀殺人已殺、懷子而……、□蠱人、□子賊殺、父母告子、奴婢賊殺、毆父母、奴婢悍、父母毆笞子、諸入食官、毆決□□、賊燔燒宮、失火、賊伐燔□、賊殺傷人、犬殺傷人、船人□人、諸□弓弩、奴婢射人、諸坐傷(?)人。
第33、34號兩簡可以綴合,正面也殘存部分“盜律”目錄,文例與第29號簡正面相同,能辨識的名目如:□出□鉗、盜主人、盜賊與□、□盜及□,等等。
這份殘存的漢律目錄本身,并未注明律典的篇名,但上面所列的名稱,都非常具體,多能從《二年律令》之“賊律”和“盜律”部分找到對應的條文。因此,目錄中的名目,既不是篇名,也不太可能是類名,而有可能是各條律文的條目名稱。
二 “九章律”之名稱
(一)“九章律”之“九”不是虛數
漢代人稱蕭何所編纂的漢律為“九章”。其中的“九”,是表示“多”,還是表示具體的數目?
東漢前期的王充已在其所著《論衡·謝短篇》中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答案:
法律之家,亦為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詰曰:“皋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征詣長安,其女緹縈為父上書,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后,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于禮,入于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13](P126)
上述文吏與儒生之間互相詰難的內容,主要圍繞“九章律”而展開,包括“九章律”的編纂者、刑罰制度及其與禮的關系。尤其是關于律與禮的關系,文吏抓住儒家經典中的說法與實際情況不符的矛盾,詰難儒生,指出儒家經典強調“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而實際情況是“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在這里,很顯然,不論是《禮經》的“十六”,還是“蕭何律”的“九章”,都是實際數目,而不是表示“多”的虛數。
《晉書·刑法志》引《魏律·序》:
舊律所難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后人稍増,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増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凡所定増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為増,于傍章科令為省矣。[1](P924-925)
根據《魏律·序》可知,三國時期,修訂曹魏新律諸臣參考了漢代的“九章律”和其他律令。其中提到漢律的九篇是由“舊律”(《法經》、秦律)六篇發展而來,尤其還提到《具律》在漢律中的排列次序“因在第六”。在這段文字中,不論是《法經》的“六篇”,還是漢律所增的“三篇”,都是實際數字,不應理解為“多”。其中又提到新律十八篇“于正律九篇為增,于傍章科令為省”,“正律九篇”即指“九章律”,與“新律十八篇”相對,仍然是實際數字,而不是虛數。
《晉書》雖成書于唐代,卻不能否定其價值。曹魏修訂的新律現在已經失傳,但《魏律·序》卻被收入《晉書·刑法志》中而有幸保存下來。《晉書》成書晚,并不代表《魏律·序》也成書晚。
上述資料證明,“九章律”之“九”是實際數字而非表示“多”的虛數,同時也證明“九章律”在漢朝是實際存在的。
(二)“九章”不是漢律的正式名稱
岳麓書院藏秦簡1656號簡背有一“律”字,應系標題,表明當時秦律只稱“律”,并未冠以諸如“秦”或“六章”之類的名稱。張家山漢簡律令部分的標題為“二年律令”,恐怕也無非是對此一律令抄本所做的簡單標識,而不是正式的律令名稱。更何況律、令抄在一起,也不可能有正式名稱。
如前所述,在傳世文獻和簡牘中所稱引法律之處,或提及律典篇名,或提及相關法律的類名,或提及某條法律的名稱,此外,在很多情況下只稱“律曰”,例如張家山漢簡《奏讞書》:
故律曰;死夫(?)以男為后。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為后。律曰:諸有縣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歸寧卅日;大父母、同產十五日。(敖)悍,完為城旦舂,鐵 其足,輸巴縣鹽。教人不孝,次不孝之律。不孝者棄市。棄市之次,黥為城旦舂。當黥公士、公士妻以上,完之。奸者,耐為隸臣妾。捕奸者必案之校上。……廷尉、正始、監弘、廷史武等卅人議當之,皆曰:律,死置后之次,妻次父母;妻死歸寧,與父母同法。以律置后之次人事計之,夫異尊于妻,妻事夫,及服其喪,資當次父母如律。妻之為后次夫、父母,夫、父母死,未葬,奸喪旁者,當不孝,不孝棄市;不孝之次,當黥為城旦舂;(敖)悍,完之。當之,妻尊夫,當次父母,而甲夫死,不悲哀,與男子和奸喪旁,致之不孝、(敖)悍之律二章,捕者雖弗案校上,甲當完為舂。[6](P227)
在這段文字中,官吏們引述法律條文時,只稱“律曰”而不提篇名或律名。顯然,“致之不孝、(敖)悍之律二章”一語,不可能表示當時律典中存在“不孝”和“敖悍”兩篇(章),而僅僅是指前面所引述的有關“不孝”和“敖悍”的兩條律文。這類例子還有很多,就不再贅述了。總之,蕭何所編纂之漢律,與“傍章”等相對而言時,則稱“正律”或“律經”;從篇章結構上說,因有九章,又稱“九章律”。“九章律”應為約定俗成的漢律名稱,只是從東漢開始,才逐漸演變成專有名稱,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提起。《史記》、兩《漢書》等傳世文獻中,明確提到“九章律”的情況并不多見,原因可能正在于此。
三 “九章律”的篇章結構
既然“九章律”作為漢代的律典是確實存在的,其篇目也確實有九篇,那么又如何解釋簡牘中律名遠遠多于九個的問題呢?楊振紅提出“秦漢律篇二級分類說”,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2]
如前所述,傳世文獻和簡牘中所提到的律名,既有律典的篇名,也有若干相關律條的類名或某條律文的名稱,這在某種程度上證明在律篇而外,確實存在對律條進行分類的情況。問題是,這種分類是律典本身所具有的,還是在抄錄、使用過程中約定俗成形成的?
我們注意到,《二年律令·錢律》中的某些條文,在《秦律十八種》中也屬于“金布律”。[14](P35-42)在《二年律令》中,“錢律”主要規定錢幣的規格與鑄造等方面的內容,“金布律”主要規定金、布的使用相關的內容,[6](P159-161,P189-192)而這兩部分內容在秦律中,都屬于“金布律”。也就是說,在秦律中屬于“金布律”的律條,在《二年律令》中分別歸入“錢律”和“金布律”中。這是秦、漢律典結構調整變化的結果,還是因為不同的抄本可以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史律”與“尉律”上。《漢書·藝文志》引述一條漢律: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4](P1720-1721)
《漢書·藝文志》沒有指出這條律文屬于哪一篇或哪一類。許慎《說文解字·序》引述了基本相同的律文,而稱之為“尉律”:
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15](P803-804)
《二年律令·史律》中也有相關律文:[6](P203)
史、卜子年十七歲學。史、卜、祝學童學三歲,學佴將詣大史、大卜、大祝,郡史學童詣其守,皆會八月朔日試之。
[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能風(諷)書五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有(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其八(體)課大史,大史誦課,取最一人以為其縣令史,殿者勿以為史。三歲壹并課,取最一人以為尚書卒史。
應該說,這條律文從《二年律令·史律》到《漢書
·藝文志》,再到《說文解字·序》,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三個多世紀中,名稱卻從最初的“史律”而變為“尉律”。是律典本身發生了變化,還是不同的抄本給予這條律文以不同的名稱?
《魏律·序》在概述新律各篇的修訂過程時,都提到各篇與“九章律”的關系,即從“九章律”某篇析出某些部分,編入新律的某篇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從“九章律”各篇所析出的部分時,很少提到《二年律令》中所見的律名,而更多提到的是較小的類名甚至條目名。例如:
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為詐律。[1](P924)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中與上述內容相關者有:[6](P134-136)
偽寫皇帝信璽、皇帝行璽,要(腰)斬以勻(徇)。
偽寫徹侯印,棄市;小官印,完為城旦舂
撟(矯)制,害者 ,棄市;不害,罰金四兩。
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完為城旦舂。其誤不審,罰金四兩。
為偽書者,黥為城旦舂。
諸言作(詐)增減券書 ,及為書故言作(詐)弗副 ,其以避負償;若受賞賜財物,皆坐臧(贓)為盜。其以避論,及所不當[得為],以所避罪罪之。所避毋罪名,罪名不盈四兩,及毋避也,皆罰金四兩。
毀封,以它完封印印之,耐為隸臣妾。
□□□而誤多少其實,及誤脫字,罰金一兩。誤,其事可行者,勿論。
雖然上述各條,都可總稱為“詐偽”,但在漢律中,“詐偽”含義并不如此寬泛,而可能專指“諸(詐)增減券書,及為書故(詐)弗副”之類的犯罪行為。“欺謾”則專指“諸上書及有言也而謾”之類的行為。總之,《魏律·序》中提及“九章律”各篇內容時,所提到的多為這種小類的名稱,甚至可能是某一律條的名稱。
另外,目前保存下來的最早最完整的唐律,各篇之下并不存在進一步的分類。秦漢律典各篇之下是否存在正式的二級分類?上述事例雖不足以給出否定的回答,但也非常令人困惑。那么,簡牘中所出現的眾多律名,是否是傳抄過程中約定俗成形成的呢?
如所周知,秦漢時期設官分職,強調官吏要根據自己的職務、秩次而行使職權,各負其責,不得超越權限,要求他們熟知其權限范圍內的法律條文。這在秦漢法律中已有明確體現,例如:
《秦律十八種·內史雜》:縣各告都官在其縣者,寫其官之用律。[14](P61)
《二年律令·置吏律》:官各有辨,非其官事勿敢為,非所聽勿敢聽。諸使而傳不名取卒、甲兵、禾稼志者,勿敢擅予。[6](P162)(敦煌漢簡2325:“律曰:諸使而傳不名取卒甲、兵、禾稼簿者,皆勿敢擅予。”[9])
可能由于簡牘比較笨重,大部頭著作完整抄寫既費時費力,又不便攜帶,因此,我們看到,迄今出土的戰國秦漢簡牘,凡篇幅較大的著作,大多只有單篇或幾篇,甚至是摘錄,很少有完整的。秦漢官吏使用法律,可能也出于同樣的原因,一般只是根據自己的職責范圍,各取所需,而不是抄錄整部法典。這些抄本所抄錄的律條,或標注其原來的律名,如“盜”、“賊”等,或根據實際需要,將相關條文重新歸類,并確定一個名稱,各官吏之間并無統一要求。但是,久而久之,或許會形成一些約定俗成的名稱。蕭何編纂漢律時所增加的“戶”、“興”、“廄”三章,相關律條及其分類名稱在秦時已經存在,蕭何很可能就是在約定俗成的基礎上將其歸納為這樣的三章,編入漢律中。
如前所述,律條的抄錄,可能存在不同的結構形式,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篇》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作為秦漢律令的抄本,沒有為各條律文編目,都是以類相從,為每一類律條確定一個名稱。張家界古人堤漢簡似乎是按篇抄寫,給每條律文命名并編目,以便查閱,可視為律令抄本的另一種形式。居延漢簡保存了一份漢令的目錄:“縣置三老二行水兼興舩(船)十二置孝弟力田廿二征吏二千石以符卅二郡國調列侯兵卌二年八十及孕朱需頌毄(系)五十二”(居延 5.3+10.1+13.8+126.12)。[10]這份殘目中所列出的似乎也是具體的條目名稱,而不是篇名或類名。兩種形式是始終并存,還是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形式,目前也很難下結論。
問題是,如果不同官吏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對所抄錄的律文分類并命名,那么,不同抄本之間,不論在分類上還是每一類律條的命名上,都可能存在很大差別,但是,在《秦律十八種》和《二年律令》中,明顯的差別并不多見。
《商君書·定分》中有這樣的主張:[16](P187-188)
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為法令為禁室,有鋌鑰,為禁而以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歲受法令以禁令。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縣諸侯一受寶來之法令,學問并所謂。吏民知法令者,皆問法官。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
或許,秦漢律典中每一篇之下并無進一步的分類,但內容上大體相近的律條還是基本上排列在一起的。各級主管法令的官吏負責法律的傳授,為便于使用,他們對法律條文做了進一步的分類,并為其命名。各種律令抄本,都來源于這些主管法令的官吏,因此有著大體相同的分類方式和律名。當然,這只是根據《商君書》所做的推測,仍然需要史實來證明。
四 余 論
本文認為,根據傳世文獻,“九章律”作為漢代的律典是確實存在的,其篇目為九篇,也是無可否認的。與其通過否定“九章律”的存在來解決出土律令名目與“九章律”篇目不相應的問題,還不如另辟蹊徑。“律篇二級分類說”雖然還有待完善,但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另一種思路,而且不會與傳世文獻發生太大的矛盾。
如所周知,《隋書·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凡與典章、律令有關的書籍,都收錄在史部之“舊事”、“職官”、“儀注”、“刑法”四類中。[17](P966-974)此后,歷代正史之《經籍志》或《藝文志》都大體沿用《隋書·經籍志》的體例,只是“舊事”改稱“故事”。然而,這一“成例”似乎并不適用于《漢書·藝文志》。
遍查《漢書·藝文志》,根據所收錄書目的標題,與典章制度相關者只有兩部。一為《五曹官制》5篇,本注:“漢制,似賈誼所條。”[4](P1734)然而,該書列于“諸子·陰陽”類中,內容顯然不是單純的典章制度,甚至與現行的制度無關,而很可能是利用陰陽五行思想所做的制度構想。另一部為《漢封禪群祀》36篇,[4](P1709)列于“六藝·禮”類,可能與當時的封禪禮制有關。
那么,與典章、律令相關的書籍是否因為收錄在私人著作中因而無法根據標題進行判斷呢?史載,“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4](P81)又曰,蕭何作《九章律》,叔孫通作《傍章》18篇,張湯作《越宮律》27篇,趙禹作《朝律》6篇。[1](P922)然而,《漢書·藝文志》中,根本沒有收錄蕭何、叔孫通、張湯、趙禹的任何著作。張蒼有著作被收錄,即《張蒼》16篇,本注:“丞相北平侯。”[4](P1733)該書收錄于“諸子·陰陽家類”,恐怕與前述《五曹官制》類似,與典章制度似乎也不會有太多關系。韓信也有著作被收錄,即《韓信》3篇。該書收錄在“兵書·兵權謀類”中,與典章或律令意義上的“軍法”恐怕也沒有直接關系。
其實,《漢書·藝文志》開篇已經說明,其所收書目,主要根據劉向《七略》,而《七略》是對祕府藏書整理分類后所撰寫的書目提要。[4](P1701)問題是,典章、律令是否屬于祕府藏書?這一問題,《漢書·禮樂志》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臧于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寢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4](P1035)
也就是說,禮儀與律令,都由“理官”(即法官)保存,因此,祕府藏書顯然不包括這部分書籍。《漢書·藝文志》沒有收錄現行律令、典章,所以不見“九章律”、“傍章”等各種律典,也不見諸如令甲、令乙或“功令”、“養老令”等各類令典,甚至也沒有當時官制、禮儀等典章制度方面的文獻,原因正在于此。關鍵在于,我們不能因此就否認這些律、令、典章制度在秦漢時期的存在。
[1]唐·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楊振紅.秦漢律篇二級分類說——論〈二年律令〉二十七種律均屬九章[J].歷史研究,2005,(6):74-90.
[3]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4]漢·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于振波.收孥法的變遷[A].簡帛研究(第三輯)[A].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6]張家山247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247號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7]南朝·宋·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
[8]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甲渠候官[M].北京:中華書局,1994.
[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M].北京:中華書局,1991.
[10]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1]高恒.秦漢簡牘中法制文書輯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與簡注[J].中國歷史文物,2003,(2):72-84.
[13]漢·王充.論衡[A].諸子集成(第7冊)[C].上海:上海書店據世界書局本影印,1986.
[1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15]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段注[M].成都:成都古籍書店據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10月版本影印,1990.
[16]高亨.商君書注譯[M].北京:中華書局,1974.
[17]唐·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Jiu-Zhang Law as Seen in the Titles of Laws and Decrees in Unearthed Documents
YU Zhen-bo
(Yuelu Academy,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K206.4
A
1008—1763(2010)04—0036—06
2010-05-28
于振波(1966—),男,內蒙古赤峰人,史學博士,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簡牘與秦漢三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