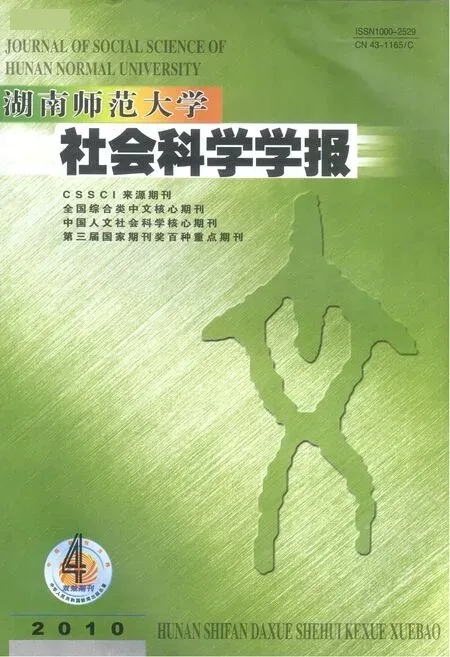近代西學東漸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推動作用
張金榮
(中南大學 政治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
近代西學東漸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推動作用
張金榮
(中南大學 政治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和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有著重要聯系。近代西學傳播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對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甚至推崇備至,為其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巴黎和會”期間,近代西學在中國的失落又促使中國先進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西學東漸;馬克思主義;傳播;作用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與近代西學東漸的歷史進程有著重要聯系。馬克思主義是在近代中國中西文化的接觸與碰撞、斗爭與融合的過程中,通過中國革命實踐和文化選擇機制,被中國先進分子理解、接受、信仰和發展的,是一批中國先進分子本著“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信念,努力向西方尋求的最佳思想武器。這其中,西學的傳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近代西學傳播給中國帶來了馬克思主義
西學傳入中國,始于明末清初,但不久因中外各種原因而被迫中止。西學再次傳入中國則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近代西學東漸的主體,早期是外國傳教士,之后是清政府出使各國的外交官員和隨從翻譯,以及留學歐美的留學生和一些主張改革的知識分子;再次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無政府主義者;然后是一批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人物。
自19世紀70年代起,清政府出使西方各國的外交官員或隨從翻譯,以及留學歐美日本的留學生與國內一些主張改革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向國內介紹西方各國政治、經濟、風土人情的同時,也介紹了普法戰爭、巴黎公社以及社會主義的有關情況。如崇厚、高從望、張德彝、黎庶昌、李鳳苞、汪鳳藻、王韜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870年6月天津教案發生后,清政府派崇厚前往法國道歉,張德彝以英文翻譯的身份隨使法國。期間正值巴黎革命爆發和巴黎公社建立,崇厚將他所見載入日記中,張德彝亦將其目睹情況寫成《三述奇·隨使法國記》一書。稍后,王韜翻譯和寫作了大量關于巴黎公社的報道,并匯編成《普法戰記》,該書于1873年由中華印務總局刊刻發行。此外,高從望撰寫了《隨軺筆記》,黎庶昌撰寫了《西洋雜志》,李鳳苞撰寫了《使德日記》,汪鳳藻翻譯了《富國策》,這些書都從不同側面介紹了馬克思主義。他們的介紹盡管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見,如把巴黎公社起義人員稱為“亂民”、“叛勇”,高從望甚至直呼公社戰士為“匪類”,《中國教會新報》也稱之為“賊黨”,但這畢竟讓中國人開始關注馬克思主義,客觀上在中國傳播了馬克思主義。
資產階級改良派在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立憲政體的同時,也將馬克思主義帶到了中國,康有為、梁啟超遂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康有為1894年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經多次修補,后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康有為為完成其構思多年的重要著作——《大同書》,進一步吸收了西方社會主義的某些觀點,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做出了一定貢獻。梁啟超是中國人在自己的論著中最早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改良派代表,1902年起,他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以及《中國之社會主義》等文章,論及馬克思及社會主義思想。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為脅迫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梁啟超直言不諱地講:“中國當時民族主義尚不暇及,何論于社會主義大同思想哉?曰:吾明知不能與驟致大國,而實欲立大同之基也。立大同之基何?曰:在迫朝廷專制政體為立憲政體。”[1]
資產階級革命派代表孫中山、馬君武、宋教仁、朱執信、胡漢民、戴季陶、廖仲愷、林云垓、陳炯明、李人杰、徐蘇中、沈仲九等人,也更加關注社會主義。1903年馬君武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簡單介紹了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史,還在馬克思的名下列舉了五本書:《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實際為恩格斯所著)、《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2]。孫中山于1905年至1907年,在《民報》上發表了大量介紹社會主義的譯文和論文,其他革命黨人也紛紛撰文傳播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革命派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樣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是預防未來中國社會出現資本主義的弊病,更好地實現中國的富強。孫中山坦言:“我國提倡社會主義,人皆斥為無病呻吟,此未知社會主義之作用也。處今日中國而言社會主義,即預防大資本家之發生可矣。”[3](P339)
中國在海外的部分無政府主義者,于1907年在日本東京和法國巴黎先后形成兩個無政府主義小團體。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組織了社會主義講習所,巴黎的無政府主義者創辦了《新世紀》雜志。他們在宣揚無政府主義的同時,也傳播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原理。正如吳雁南等人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者舉辦的刊物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在辛亥革命前各類報刊中,不僅介紹數量多,論述也有精到之處”[4](P405)。1911 年 7 月 10日在上海成立的社會主義研究所,改組為中國社會黨,推舉江亢虎為部長。中國社會黨成立后,江亢虎和社會黨其他骨干成員,如陳翼龍、沙淦等人有組織、有刊物地鼓吹社會主義。盡管他們介紹的目的在于說明無政府主義比馬克思主義更為優越,說服中國人民以無政府主義為理論指南,甚至大肆批評“馬氏學說之弊”,但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的過程中,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上述各群體在傳播近代西學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充當了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5],盡管他們的目的大相徑庭,傳播環境也有所差別,但是,他們使馬克思主義由附帶的、零星的傳入,到較為廣泛地介紹,至五四時期成為重要社會思潮,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二、近代西學東漸為中國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
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既具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又研究甚至推崇過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橋梁。如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等人就很有代表性。
李大釗于清末民國初年,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曾經主攻西方政治、法律學說和經濟學說,比較系統地掌握了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學說,并對之深信不疑。1913年冬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在該校政治經濟科一、二年級的課程表中包括國家學原理、經濟學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論、刑法要論、政治經濟學原著研究、古典經濟學原著研究、英文、哲學、第二外國語、政治學史、財政學、統計學等。而且該校對學生要求相當嚴格。這些嚴格的學習和訓練,為李大釗日后的思想變遷和政治活動打下了基礎。
李大釗的早期思想主要受到英國功利主義學術思想的影響,對法國學術思想涉及不多。但他對法國的柏格森哲學卻予以特別的關注,并接受了他的一些哲學觀點來建構其早期哲學體系。如李大釗把柏格森的“綿延”說用來作為反對封建復古論的武器;研究柏格森的“直覺”說,倡導國民個性的充分發展;闡釋柏格森“變的哲學”,得出社會改造是合理的結論;剖析柏格森關于生命沖動是意志自由創造的觀點,反對封建的宿命論。[6]李大釗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對法國學術思想給予了更多的重視,對法國學術史上進步觀念演進軌跡及其唯物史觀形成的貢獻有重要的評述。
李大釗崇尚西方的自由理論。在他看來,自由是西方文明最有價值的成果,是公民行使民主程序的基本要求。李大釗不僅接受了盧梭、鮑桑魁和穆勒等人的自由理論,而且還有所發揮。他轉述穆勒之語:“凡在思想言行之域,以眾同而禁一異者,無所往而合于公理。其權力之所出,無論其為國會,其為政府,用之如是,皆為悖逆。不獨專制政府其行此為非,即民主共和行此亦無有是。”[7](P159)穆勒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個人的自由問題,認為個人是自由的主體,言論自由則是個人自由的首要前提,個性的發展和完善是自由的目的。李大釗認為穆勒對自由的論述是“透宗之旨”。只有遵照穆勒的自由理論在中國推行代議制度,特別是要尊重民眾的思想自由,中國才能成為立憲之國。
李大釗到日本后不久就接受了托爾斯泰的“群眾之意志”的“累積”是“歷史上事件之因緣”的看法,并將其同自由主義觀念融會在一起,探討了“民彝”,從而形成了他自己的“民彝”政治觀念。李大釗進一步把盧梭“契約論”的平等精神和穆勒的自由精神結合起來,形成了以“民彝”為出發點和價值尺度,以代議制為形式,以自由、平等為其精神,即“民彝”與國法之間愈益疏通為目標的民主觀。同時,他稱贊托爾斯泰“唱導博愛主義,傳布愛之福音于天下”,是“舉世傾仰之理想人物”[7](P174)。希望人倫關系達到普遍的愛,甚至認為:“愛者,宇宙之靈也,人天之交也。吾人當信仰真理,吾人即當尊重愛。”[7](P180)
李大釗對西方民主精神的接納,既表現出引進西方文明的開放心態,又表現出很強的民族心理選擇機制。這奠定了他民主意識和獨立品格的思想基礎。
陳獨秀出身于“習儒業十二世”的世家,十七歲中了秀才。1898年,陳獨秀考入杭州求是書院,他在這里開始接觸和接受到了新式教育,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響,還學習了英文、法文、天文學、造船學等。在1915年創辦《青年雜志》之前,陳獨秀曾三次東渡,留學日本,廣泛地接觸并學習研究西方各種思想學說。
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說道:“歐洲文化,受賜于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于文學者亦不少。予愛盧梭、巴士特之法蘭西,予尤愛虞哥、左喇之法蘭西;予愛康德、赫克爾之德意志,予尤愛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愛倍根、達爾文之英吉利,予尤愛狄鏗士、王爾德之英吉利。”[8](P174-175)對于每個國度,陳獨秀首先提到的都是一個哲學家和一個科學家,如法國是哲學家盧梭和科學家巴士特(今譯巴斯德);德國是哲學家康德和科學家赫克爾(今譯海克爾);英國是哲學家倍根(今譯培根)和科學家達爾文。這足見陳獨秀對西方文化了解的廣泛與深入。陳獨秀的早期憲政思想,以法國的民主主義為基調,其中亦雜糅了英、美等國的自由憲政思想。陳獨秀關于民主的大部分觀念沿襲了盧梭的“主權在民”學說,而他以個人主義闡釋的人權觀念和有關法治的一些主張,實際上更多地源于英美的自由主義傳統。
陳獨秀在《新青年》早期對法國文化情有獨鐘,推崇備至。在《青年雜志》的創刊號上,他以《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濃墨重彩地頌揚法國文明,還選譯了法國歷史學家薛紐伯的《現代文明史》和同樣是法國人的Max O’Rell的《婦人觀》;在《青年雜志》的第三、第四期《世界說苑》欄目中登載了李亦民編譯的《法蘭西人之特性》。在陳獨秀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出現過類似“法蘭西人為世界文明之導師”[9]這樣的文字。陳獨秀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把他認為足以代表“近代文明之特征”的三件大事——人權說、進化論和社會主義——都歸功于法國。他說:“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8](P81)在他的筆下,法國不僅對近代文明有其獨特而重大的貢獻,就連法國人的國民性也遠非其他西方先進國家所能比擬。“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德、法三國。而英俗尚自由,尊習慣,其弊也失進步之精神。德俗重人為的規律,其弊也戕賊人間個性之自由活動力。法蘭西人調和于二者之間,為可矜式。”[8](P129)對比德、英兩民族而獨獨推崇法國人。“從陳獨秀所受法國影響的來源看,即有來自法國革命和啟蒙運動尤其是盧梭思想的因素;又有來自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孔德實證主義哲學思潮的因素;他還受到了19世紀下半葉以降的自然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10]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陳獨秀領導的這場思想啟蒙運動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取自近代西方,尤其受到了來自法國的重大影響。由于壓倒一切的任務是迫切地要為中國的問題找到快捷的解決方法,這促使陳獨秀思想上經歷了急劇變化,即從一個倡導“人權”的自由主義啟蒙者,一變而為高舉“民主”旗幟的民主主義者,再變則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青年毛澤東同樣具有中西合璧的知識基礎。他自幼熟讀四書五經、中國史地、古典文學。在對西方文化的求索中,毛澤東曾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半年,他回憶說:“在這自修的時期內,我讀了許多書籍,讀到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極大的興趣第一次閱讀了世界的輿圖。我讀了亞當·斯密士(亞當·斯密)的《原富》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物種起源》)和約翰·斯陶德密爾(約翰·斯·密勒)所著的關于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騷(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學》和孟德斯鳩所著的一本關于法學的書。我將古希臘的詩歌、羅曼史(傳奇)、神話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國的‘史地’混合起來。”[11](P37)毛澤東回憶中談到的這些印象深刻的書,都是18-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古典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名著。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倫理學課程由楊昌濟采用德國哲學家、倫理學家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作課本。該書共約10萬字,毛澤東閱讀時寫了12萬字的批語,這就是《〈倫理學原理〉批注》。當時楊昌濟翻譯的由日本人所寫的《西洋倫理學史》尚未出版,毛澤東將其借來,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來。一師畢業之后的兩次北京之行,使毛澤東廣泛深入地接觸了蜂擁而至的西方文化思潮。1920年6月7日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道:“我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只這三科。哲學從‘現代三大哲學家’起,漸次進于各家。”[12](P479)這三大哲學家即指法國哲學家柏格森,英國邏輯學家、哲學家羅素,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毛澤東自覺學習、研究西方文化,為他日后改造、融合西方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是他日后沒有出洋,卻能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有機結合的重要因素。
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文化基礎之上的,西方近代文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人民接受馬克思主義開辟了道路。對西方近代文化的深入研究甚至推崇備至,就成為中國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前提。
三、近代西學在中國的失落促使中國先進分子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中國先進分子在崇尚西學,宣傳西方文化的同時,并沒有盲從,他們在宣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同時,就已經開始對它持有某種懷疑和保留的態度。比如,陳獨秀在1915年9月即已指出:“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8](P80)李大釗對民國建立以后的政治局面始終是不滿意的,這就促使他去探求理想的民主政治,于是,他在《民彝與政治》一文中提出了他的政治設想和方案。在李大釗的構思中,最適宜之政治就是“惟民主義為其精神、代議制度為其形質之政治,易辭表之,即國法與民彝間之連絡愈易疏通之政治”[7](P149)。盡管“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然即假定其不良、其當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較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國法之制,決非退于專制政治,可以篤信而無疑焉”[7](P158)。青年毛澤東在1917年8月也說過:東方思想固不切于實際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盡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12](P86)。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思想中的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這種懷疑論成份,推動他們去探索挽救中國危亡的新途徑,為他們爾后接受社會主義準備了適宜的思想土壤。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是中國先進分子思想轉變的關鍵因素。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性質和前途的認識,李大釗與同時代的其他論者一樣,首先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看成是維護世界人道公理的戰爭,是反對暴力的正義、和平、公理的戰爭。在《威爾遜與平和》中,他說:“吾人終信平和之曙光,必發于太平洋之東岸,和解之役,必擔于威爾遜君之雙肩也。”[7](P268)從而表達了他對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陳獨秀曾真誠地歡呼協約國方面的勝利,他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上,表達了這種“公理戰勝強權”的欣喜之情,并真誠地把美國總統威爾遜稱作“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8](P304)。
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李大釗在《論國人不可以外交問題為攘權之武器》中,有如下的論述:“方今世界各國,罔不投于戰爭漩渦之中,一時軍事內閣之成,自為其應有之象。顧余敢斷言,戰場之硝煙一散,此曇華幻現之軍事內閣,即將告終,而一復其平民政治之精神,此又戰后復活之世界潮流也。吾人挾此最有勢力之世界潮流以臨吾政府,武斷政治之運命將不摧而自倒。”[7](P280)堅信“平民政治之精神”將會代替“武斷政治”而成為“戰后復活之世界潮流”,這正是李大釗觀察、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的出發點。俄國“十月革命”發生之前,李大釗對國際政治和民主主義運動的研究投入了極大的熱情,特別是對俄國二月革命后形勢的發展格外關注,撰寫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俄國大革命之影響》、《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等一系列文章,促使他后來能夠在國內較早地關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李大釗認為,俄國二月革命“由內政言之,則實自由政治之曙光”[13](P1),意味著“平民政治之精神”在世界上的最初出現。在此意義上,他又在《庶民的勝利》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看成是相對于“大……主義”(專制的隱語)和“資本主義”而言的“民主主義”和“勞工主義”的勝利。此后,其論著中就反復出現“平民政治之精神”(平民主義)的主題,這促使他較快地接近并接受馬克思主義。
當巴黎和會中中國主權和利益被包括法國在內的列強所出賣之時,陳獨秀發現,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所謂的公理戰勝強權,不過是一句空話。他說:“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8](P397)他心目中幾近完美的法國形象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動搖。他寫道:“法蘭西國民,向來很有高遠的理想,和那軍國主義狹義愛國心最熱的德意志國民,正是一個反對。現在德意志不但改了共和,并且執政的多是社會黨,很提倡縮減軍備主義。而法蘭西卻反來附和日本、意大利,為著征兵廢止、國際聯盟、軍備縮小等問題,和英美反對……不知理想高遠的法蘭西國民,都到那里去了?”[8](P358)其實,他在 1918 年初就已經看到:“二十世紀俄羅斯之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于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8](P254)此時,隨著“巴黎和會”所引起的對西方文明的幻滅和“五四運動”的開始,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十月革命”后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俄羅斯,投向了這一 20 世紀“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8](P381),并由此開始了他向馬克思主義的轉變。
不可否認,近代西學傳播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推動作用。可以說,沒有近代西學東漸就沒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近代西學的傳播在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發揮著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這種啟蒙作用不能因為中國先進分子之后拋棄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認為可有可無,實際上這種啟蒙的深度與廣度直接影響著中國人日后對馬克思主義接受、理解、應用的質量。中國人在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合乎邏輯地經歷了器物——制度——觀念由表層到深層的過程。就在高舉西方民主與科學精神的新文化運動進一步發展之際,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巴黎和會”與俄國“十月革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使中國先進分子在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失望之余,從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看到了民族國家的希望,時代的轉換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1]梁啟超.秘密結社之機關報紙[J].新民叢報(38,39合刊),1903-10-04.
[2]馬君武.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J].譯書匯編(11),1903-02-04.
[3]孫中山.孫中山文集:上卷[M].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
[4]吳雁南.中國近代社會思潮:第2卷[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5]李軍林.從“五W”模式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特點[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7,(1):63.
[6]吳漢全.五四時期李大釗對法國學術思想的研究[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5):87-88.
[7]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陳獨秀.陳獨秀文章選編(上)[M].北京:三聯書店,1984.
[9]陳獨秀.陳獨秀答一民[J].《新青年》2卷 3號,1916-11-01.
[10]韋 瑩.陳獨秀早期思想與法蘭西文明[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3):94.
[11][美]埃德加·斯諾筆錄.毛澤東自傳(汪 衡譯)[M].青島:青島出版社,2003.
[12]毛澤東.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
[13]李大釗.李大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責任編校:彭大成)
Promoting Effect of Modern Western Learning into East on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ZHANG Jin-rong
(School of Politic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There is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between the wid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dern western learning into east.The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brought Marxism to China.Chinese advanced elements did in-depth research on and even highly praised modern western culture,which laid a cultural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ir acceptance of Marxism.However,during World War I especially during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the loss of modern western learning in China made the advanced elements choose Marxism.
western learning into east;Marxism;spread;effect
A81
A
1000-2529(2010)04-0027-04
2010-04-05
湖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歷史上三次外來文化在中國傳播的比較研究”[07YBB028]
張金榮(1960-),女,河北平泉人,中南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