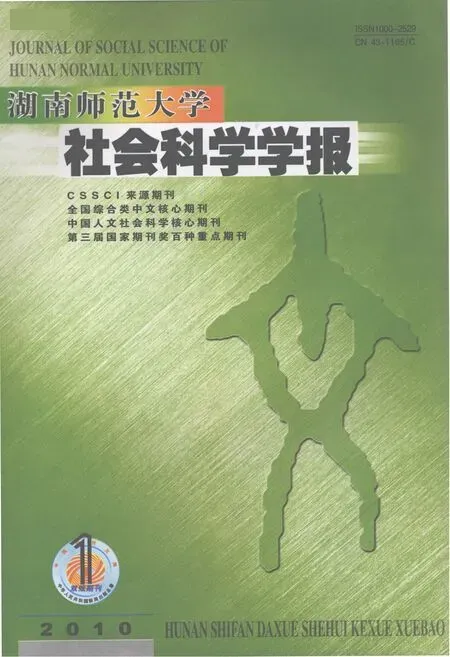新浪漫主義:五四文學與存在主義的關系性建構
楊經建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新浪漫主義:五四文學與存在主義的關系性建構
楊經建
(湖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五四文學與存在主義的價值關系是近年來學界已開始意識到的話題。從“新浪漫主義”入手探尋五四文學的存在主義傾向是一種新的“問題意識”生成點。“新浪漫主義”文學產生于五四啟蒙現(xiàn)代性的歷史語境,它以非理性主義為文化價值立場和審美思維形態(tài),以現(xiàn)代主義為時代精神表征和藝術訴求方式,以生命哲學、生命詩學為創(chuàng)作話語的意義本體內涵。正是通過上述話語知識結構的建構“新浪漫主義”確證了五四文學與存在主義之間價值關系的必然性。
五四文學;存在主義;新浪漫主義;非理性主義;現(xiàn)代主義
李歐梵先生在《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稱五四一代作家是“浪漫的一代”,梁實秋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一文中明確指出“現(xiàn)今文學是趨于浪漫主義的”從而把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統(tǒng)一定義為“浪漫主義”文學。[1](P27)如果加以深究便不難發(fā)現(xiàn),五四文壇所推崇的浪漫主義其實是所謂“新浪漫主義”。
對此茅盾其時的言說頗具代表性:“能幫助新思潮的文學該是新浪漫主義的文學,能引我們到正確人生觀的文學該是新浪漫主義的文學,不是自然主義的文學,所以今后的新文學運動該是新浪漫主義的文學。”[2](P44)考慮到目前學界對五四文學與存在主義的價值關系或五四文學的存在主義傾向已有初步的認定,因此,對新浪漫主義話語進行重新清理與詮釋是進一步求證和確認存在主義與五四文學關系性建構的必要一環(huán)。
一
很明顯,五四時期流傳于文壇的新浪漫主義一詞主要來源于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近代文學十講》,廚川北村在該書中廣泛聯(lián)系西方近代社會生活和文化思潮的變遷,評述了自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西方文藝思潮的演變,在此基礎上對新浪漫主義的產生原因、性質和特點做了相當精辟的論述。他所提出的“新浪漫主義”的指稱及其表現(xiàn)形態(tài)受到了五四作家普遍認同,并成為五四文壇描述、概括世紀初文學的特定話語概念。“1919至1922年間,茅盾、田漢都是把新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新文學發(fā)展方向加以提倡。”[3](P31-32)
不言而喻,廚川白村的思路凝定在“西方”的“新浪漫主義”上。廚川白村認為它“并非是最近一切文藝的總括,它只是最近歐洲文壇的一個主要傾向而已”。這種傾向是“源于浪漫時代的那一股主觀傾向的暗流”,一種“情緒主義”的抬頭[3](P33)。事實上,西方新浪漫主義盡管也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浪漫主義的藝術審美表現(xiàn)形態(tài),但其最本質的話語內涵卻表現(xiàn)為抗衡科學理性、工業(yè)文明的文化哲學特質——一種現(xiàn)代非理性主義思潮本色。
很明顯,傳統(tǒng)浪漫主義一開始就包含著理性與感性、彼在與此在的張力:它以幻想和激情來抵抗理性的重壓;以鄉(xiāng)村和異國風情對抗工業(yè)化的城市;以主觀性來對抗冷冰冰的客觀現(xiàn)實。問題卻在于,在其本質上傳統(tǒng)浪漫主義依然拘閾于西方傳統(tǒng)理性主義邏輯所施予的美學建構模式——創(chuàng)作主體性建構的合法性基礎主要并不是感性而是理性。將理性的超越價值抬舉到感性體驗之上是前現(xiàn)代性的特點。須知,長期以來西方文明發(fā)展史是一部理性發(fā)展史,近代哲學家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更是把理性推崇到了人類本質的地步。然而,“現(xiàn)代人類須藉理性以提高其控制生活條件的能力而趨達自由,而理性化的社會分工所成就的經濟(工業(yè)化)、政治(官僚化)的科層組織,在促進社會進步的同時,又反過來成為人性異化的根源,現(xiàn)代人的異化勞動和異化生活表征著人的片面化、非人化和機械化。這樣,‘理性’就從解放人的工具蛻變?yōu)榕廴说募湘i,現(xiàn)代化反成為人的精神自由的敵人,于是有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之非理性的文化現(xiàn)代性的反撥。”[4]現(xiàn)代非理性主義所揭示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人不僅是理性的更是非理性的,人的本質是非理性的實體而理性只具有工具性質。人的直覺、感覺、本能、情感、欲望、需求、信仰、審美以及實現(xiàn)它們的愿望等等無一不是非理性的,這是一個永遠無法改變也無需改變的事實,是人類社會和人本身不斷發(fā)展的基本動力,同時也是人與人之間平等的一個自然基礎。“自尼采之后,非理性作為一種重要的表現(xiàn)對象,整體性地進入哲學、美學視野,成為現(xiàn)代主義表現(xiàn)的重要主題。如世界是荒謬的、人性異化等……在尼采身后,人類進入了一個非理性言說的時代。”[5](P592)
眾所周知,存在主義是現(xiàn)代西方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典型形態(tài),當代美國學者威廉·巴雷特的堪稱西方研究存在主義的經典著作《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哲學研究》就是將存在主義置于非理性主義語境中予以闡釋。作為現(xiàn)代西方一種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存在主義力圖超越傳統(tǒng)形而上學對本體論的理解方式,把存在本體論從理性認識論的遮蔽下解放出來;它對于人的生存狀態(tài)的關注以及對人的存在意義的追問標志著西方哲學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轉折。
事實上,作為一種文化哲學話語的存在主義本身就擁有一種非理性或“詩”之“思”基因。如果說一般意義上的形而上學本體論可以被看作對世界的一種類科學知識式的介入,那么存在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則是被當作現(xiàn)代思想視域對世界的一種詩性把握,這就使它具備了詩性哲學與感性論美學的特質因而與文學有著天然的血緣關系。的確,在存在主義的話語表述中,“詩”(藝術)與“思”(理性)以不同方式對同一本源加以言說:“詩”是人進入存在的開端,是穿透人的歷史的詩性啟悟;“思”是對存在顯現(xiàn)的本真領悟,存在之“思”是原詩(Urdichtung),“詩”的本質因而以“思”為依據(jù)。存在之“思”的最終歸宿是海德格爾的“詩意地棲居”。“因此自克爾凱郭爾往后的存在主義哲學,趨向于回避甚至拒絕系統(tǒng)的說明,而寧愿用雜記、小品文、小說、戲劇以及與個人生活相關的一切寫作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6](P90)以至于給人造成這樣的印象:“存在主義者所想做的某些事,做得最好的是表現(xiàn)在藝術而不是在哲學中。”[7](P44)這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非理性”文學。由此,新浪漫主義——非理性主義——存在主義便成為一種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話語意義鏈。
嚴格地說,五四文學的時限性所對應的是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以克爾凱郭爾、叔本華、尼采、柏格森等代表的前期存在主義階段。尼采在20世紀漢語思想文化界的接受史就是明證:尼采剛死不久就潛入王國維、魯迅這樣的“中國魂”乃至掀起了一種世紀性的“尼采熱”。其實在五四運動之前,梁啟超、王國維、李大釗、蔡元培等先覺者們都較為詳細地介紹過尼采、叔本華的學說,“而五四作家反抗封建文化理性主義束縛的有力工具,不是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tǒng),而恰恰是從西方世紀末非理性主義思潮中汲生發(fā),它并不必然地和自動地導向人生理想的崇高境界,所以魯迅申明只有當離心力大于求心力,生命才會“焉興作,會為大潮”。而對于作家來說只有“生命力彌漫”者方能生出“力”的藝術來。[10](P244)不僅如此,魯迅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身體力行如其《野草》,“《野草》的人生哲學作為20世紀的產物,它與現(xiàn)代人本主義思潮,尤其是以存在哲學名字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非理性主義確實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與思維淵源……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魯迅對尼采、基爾凱廓爾曾投以極大的熱情;但人們很少這樣考慮,這兩位公認的存在主義理論先驅恰恰可能成為《野草》與存在主義之間的橋梁。”[11](P287,289)而在田漢的眼里,“所謂新羅曼主義,便是想要從眼睛看得到的物質世界,去窺破眼睛看不到的靈的世界,由感覺所能接觸的世界,去探知超感覺的世界的一種努力。”[12](P73)其劇作《古潭的聲音》以靜寂深邃、吞噬生命的“古潭”象征一種未知的既誘惑人又毀滅人的勢力,更象征著生命的歸宿,作者賦予古潭以深邃的人生與審美寓意,充滿了對未知世界的探索。至于茅盾所力倡的新浪漫主義則包含有象征主義、未來主義、印象主義、表現(xiàn)主義、頹廢主義、唯美主義、新理想主義等,這是對“現(xiàn)代性焦慮”的一種真切而不乏超越意味的藝術感受方式。要言之,新浪漫主義所吸取的主要是西方19世紀末以來的非理性主義哲學、美學和文學思潮的種種質素,諸如叔本華、尼采、柏格森等人取靈感,繼而形成一套特有的反傳統(tǒng)思路的。這一點從魯迅對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的接受和創(chuàng)造性轉化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證……魯迅、陳獨秀等人則已經從世紀末反理性主義思潮中看到了理性的虛妄,他們雖然也打出了‘科學和民主’的大旗,但在這個科學主義的根基下卻是反科學主義的土壤。也就是說他們追求的不再是注重理性分析和文化秩序,不再是像康梁(筆者注:康有為和梁啟超)那樣主張通過社會結構的內部轉換和調整求得歷史的進步,而是提倡‘價值重估’和‘破壞偶像’,也就是一種非理性主義的懷疑和反叛精神。”[3](P24,26-27)
也就是說,五四期間的新浪漫主義是一種典型的非理性主義文學話語建構。具體言之,新浪漫主義文學的哲學心理基礎是現(xiàn)代人的生存苦悶,創(chuàng)作理念基礎是對感性個體生命的認同,其藝術表現(xiàn)原則倡揚自由地表現(xiàn)本源自我。魯迅聲稱個體生命既有適應生活的“生”的本能又有承接已逝生活“死”的本能,兩種生命本能的“形變之因,有大力之構成作用二:在內謂之求心力,在外謂之離心力,求心力所以歸同,離心力所以趨異。歸同猶今之遺傳,趨異猶今之適應”[8](P11)。郁達夫則強調在人的“種種的情欲中間,最強而有力、直接搖動我們的內部生命的,是愛欲之情。諸本能之中對我們的生命最危險而同時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9](P266)。兩者都強調的是:人的本能欲望是一種強力——蘊含著一種向上的沖動力與競爭力;這種本能欲望之力又是會朝相反方向的哲學思想和美學主張,強調文學的創(chuàng)作本體由物到人、由客觀到主觀、由理性到非理性、由人的意識世界到感知世界的轉變。換言之,新浪漫主義“它切斷了中國哲學的理性主義、倫理中心、社會中心,而以個體、感性、生命為中心,在文化上帶來了一個由倫理本位文化向感性本位文化的轉向,使得審美上產生了以群體、理性為中心的美學向著以個體、感性為中心的美學的轉型。這一轉向的哲學基礎來自于‘五四’思想的反儒家傳統(tǒng)。‘五四’文學美學的基本潮流是反理性主義的感性主義、個性主義,在‘五四’一代小說家中尼采、叔本華、柏格森、弗洛伊德的名字要比任何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家響亮得多,人們將美的本質等同于‘自我’的生命、心靈、欲望、人格、情感等等,這是一種與儒家傳統(tǒng)倫理主義美學完全不同的美學思潮”[13]。
由是,以新浪漫主義為癥候、與存在主義意義關聯(lián)的“現(xiàn)代西方非理性文學思潮對20世紀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原初性、內在性、整體性的,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孕育、誕生期,現(xiàn)代非理性文學思潮作為一種強大的異域文化力量,就參與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建構過程,非理性文學就構成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一種結構性存在……非理性人學雖為現(xiàn)代西方思想的產物,但它已成為20世紀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一種本原性、精神性存在。”[14]
二
不難發(fā)現(xiàn),新浪漫主義一方面具有諸多的包容性和多種發(fā)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浪漫主義’概念是一個特定歷史的產物,是對現(xiàn)代主義萌芽狀態(tài)的文學思潮初步的、感性的認識的結果,在西方‘新浪漫主義’所概括的文學思潮現(xiàn)在基本上被納入了‘廣義的現(xiàn)代主義思潮’中。建國后,茅盾曾就此做過說明:‘新浪漫主義這個術語,20年代后不見再有人用它了……現(xiàn)在我們總稱為現(xiàn)代派的半打多的主義,就是這個東西。’當代學者樂黛云先生把它與現(xiàn)代主義概念相等同……袁可嘉先生也認為‘五四時期所稱的新浪漫主義,其實即是我們今天所稱的廣義的現(xiàn)代主義,包括唯美主義、印象主義、象征主義’”[3](P32)。
當以五四新文化運動昭示著中國文化和文學實際上已步入“世界性”和“現(xiàn)代性”進程后,無論是作家的主體精神結構還是作品的審美形態(tài)結構都與傳統(tǒng)文學有著明顯的差異,“按五四時期流行的進化論邏輯推演,在西方文藝流派流程中處于寫實主義之前的舊的浪漫主義,當時并不為郭沫若、茅盾等所注意,他們首先關注的是內涵相當于今天的現(xiàn)代主義的‘新浪漫主義’”[15]。
而從時段上說,以存在主義為哲學底蘊的西方現(xiàn)代文化其典型的審美形態(tài)正是現(xiàn)代主義文藝。“現(xiàn)代主義是現(xiàn)代性走向成熟時代的文學思潮,是對現(xiàn)代性的徹底抗議、對理性的全面反叛。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發(fā)展到成熟階段,現(xiàn)代性的黑暗面突出顯現(xiàn),社會生活已經全面異化。啟蒙以來建立的理性神話破產,非理性思潮蔓延。文學也開始全面反叛現(xiàn)代性和理性,抗議人的異化。存在主義哲學成為現(xiàn)代主義的理論基礎。現(xiàn)代主義揭穿理性的虛偽,揭露世界的異己性、非人性,揭示生存的荒誕和無意義。現(xiàn)代主義關注個體精神世界,展示人的心理體驗,表現(xiàn)現(xiàn)代人的孤獨、苦惱和絕望。現(xiàn)代主義繼承了中世紀和浪漫主義文學傳統(tǒng),人物和世界被抽象、變形,塑造一個非現(xiàn)實、非理性的世界。”[16]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運動可由波德萊爾、福樓拜、陀思妥也夫斯基追溯到尼采、易卜生和克爾凱郭爾,它是以盧梭肇其端的浪漫主義運動的精神后裔,進而以審丑的“矛盾性”反諷來表達審美的“解放性”精神。
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之所以強烈的反傳統(tǒng),是因為19世紀現(xiàn)實主義文學以前的各種“反映論”和“模仿論”在把握社會現(xiàn)實方面固然成功也是深刻的,但現(xiàn)代主義文學不再滿足于對社會、歷史和道德等認識論范疇進行批判和思考,而是從本體論上追問世界、時間和生命存在這些形而上的問題。文學開始由對社會生活現(xiàn)象的揭示轉向對世界存在本體的探究,由對具體現(xiàn)實中的人的描寫變?yōu)閷θ说纳嬖跔顟B(tài)的質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現(xiàn)代主義文學在本質上是一種存在主義文學。事實上,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興起幾乎與存在主義的先驅克爾凱郭爾以非理性主義、個體主義為基本特征的神秘主義哲學,以及叔本華、尼采的意志論哲學,柏格森的生命哲學的出現(xiàn)是同步的,這些產生于19世紀下半葉的學說有力沖擊了以往人類對世界的認識方式,一切傳統(tǒng)價值觀都要在新的價值準則下被重估。現(xiàn)代主義文學于是承繼乃至擴展了克爾凱郭爾、尼采、叔本華等的思想傳統(tǒng),其創(chuàng)作表現(xiàn)為美學上激進的實驗氣質和對生命存在本體意義的思考。“事實上在西方學者那里,他們普遍認為現(xiàn)代主義小說中都具有存在主義的主題或者影響……要是把《惡心》這樣一部作品同卡夫卡或貝克特的小說創(chuàng)作作一對比,事情就很清楚,本體論的想象比存在主義的論辯對文學創(chuàng)作更為適宜。也可以同樣說,現(xiàn)代主義小說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通過形象和想象的方式對現(xiàn)代人關于存在的觀念進行表現(xiàn),它本身就孕育著更為形象和直觀的存在主義哲學。這一點,國內的學者也持相似的看法。”[17](P243)
王富仁先生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中國的一個現(xiàn)代主義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學運動就是中國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運動”[18]。如果此說可以成立,那么嚴格地說,這個“現(xiàn)代主義文學運功”只能由新浪漫主義承擔并完成。
五四時期陳獨秀、茅盾等在描述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大勢時都將現(xiàn)代主義列為未來的甚至是理想的藝術形態(tài),盡管他們所用的概念是“自然主義”或“新浪漫主義”之類的名稱,正如魯迅用“象征印象主義”作為他所認知的現(xiàn)代主義的異名一樣。新浪漫主義因而成了許多文學家的努力目標。在魯迅的《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中,拜倫、雪萊等浪漫主義精神和尼采、叔本華、施蒂納以及克爾凱郭爾的新浪漫哲學融為一爐被視為重振“社會元氣”、“立人”然后“立國”的精神資源。而“強化人的生存價值與意義這一人本主義哲學命題,在魯迅看來,將成為‘20世紀之新精神’,‘20世紀之文明’的根本所在。人不能陷于資產階級文明的現(xiàn)代性,即庸俗的物質功利主義之中,不能忘卻生存的另一向度——‘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1907年的魯迅就已經悟及這一層面。關于詩意人生的思考與追尋,構成魯迅浪漫主義美學觀念中最亮麗的部分”[19]。其時的論者昔塵這樣言說:“自然派文學是建立在近代科學之基礎上的,但到了現(xiàn)在,人們不但追求物質,更追求精神,所以產生了新浪漫主義。新浪漫主義的文學發(fā)于‘靈底覺悟’,它暗示人生隱秘的一面,把不可見的真相,依具體的事物表現(xiàn)出來。它用神秘象征的筆法,先把讀者拉到空靈飄渺的境界,使他們在沉醉戰(zhàn)栗的片刻之內,得到極深切的感應。新浪漫主義還能從事物外表的丑尋出內在的美質來。這既不同于浪漫主義,也不同于自然主義。我們應該吸取。”[20]
這一方面是由于五四文化如前所述本身就是一種不同于中國傳統(tǒng)道德理性本位文化的感性本位論文化,由此開創(chuàng)了一個文化上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時代,在藝術形態(tài)上屬于個體論感性美學范疇,其審美表述上則體現(xiàn)出顛覆性或反叛性特征。比如魯迅的《野草》,“作為魯迅個人精神心理的一種象征性表現(xiàn)和他對意義的探求的一種隱喻性記載,這個散文集在他的全部著作里最為晦澀,因此,對于中國讀者來說,也最難懂。魯迅似乎超越了他那一代人的那種常見的感受力而跨入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門檻……魯迅的這些‘超現(xiàn)實主義’特色的作品不僅僅揭示出人類所處的那種‘普遍的’荒誕境地,以及個人陷入的那種毫無意義可言的絕境,而且還帶有一種對意義的尋求那種人文主義式的激情……盡管魯迅從未對這些內容做過具體說明,但是最后的那種信息似乎指出這樣的可能性:人類的一種倫理行為將依然會把某種意義賦予這種現(xiàn)存的毫無意義可言的環(huán)境。”[21](P233)田漢早期戲劇中的現(xiàn)代主義傾向也是鮮明的,要言之,現(xiàn)代主義給田漢的主要影響反映在他對靈魂和抽象真理的專注,以及手法上對夢幻、心理剖示等的運用。而在茅盾的闡釋中新浪漫主義內容雖然極其龐雜,包含有象征主義、未來主義、印象主義、表現(xiàn)主義、頹廢主義、唯美主義、新理想主義等,但在審美表現(xiàn)上新浪漫主義都以情緒化、情感化、感性(感官)化為藝術手段與表現(xiàn)方式,其深層反映了人的情緒、情感對理性的判斷與解構,其實質是展示了以人的藝術直覺和審美體驗為解放動力的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精神,寄寓的是世紀初中國知識階層對世界、對社會、對自我整體及其存在命運的體驗和感受,它更是人類把握和認識世界方式的深刻改變。即所謂“‘五四’文學顛覆了中國宣教型、靈魂型、診斷型文學傳統(tǒng),開創(chuàng)了非群體性、非道德性、非宣教性的文學審美新范式,帶來了一個審美形式上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時代。”[13]
當今學者陳思和從五四文學的“先鋒性”上對新文學的發(fā)生進行精辟論述,他在五四文學中歸納出以創(chuàng)造社作家為代表的一種“先鋒的運動”,所謂“先鋒的運動”確切地說應該是具有現(xiàn)代主義特質的新浪漫主義文學。這個“激烈的文學運動或審美運動”與傳統(tǒng)斷裂的結果是帶來了“新穎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文學模式”。“它們構成了推動整個20世紀文學發(fā)展的一種力量”[22]。在這個意義上新浪漫主義實質上是20世紀初中國文學在“現(xiàn)代性焦慮”中所導致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現(xiàn)象,否則就無法最終成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必須指出,以現(xiàn)代主義為時代癥候的新浪漫主義文學并沒有脫離20世紀中國現(xiàn)代性敘事賴以建立的啟蒙主義知識框架。在西方,現(xiàn)代主義是與啟蒙現(xiàn)代性或社會現(xiàn)代化相對立的文化現(xiàn)代性中的審美現(xiàn)代性,雖然“現(xiàn)代主義”、“審美現(xiàn)代性”和“文化現(xiàn)代性”三者之間有著邏輯關系上的種屬差別,但其共同性則是對啟蒙現(xiàn)代性或社會現(xiàn)代化的“反思”與“批判”。實際上,現(xiàn)代性的內在悖論——啟蒙現(xiàn)代性與審美現(xiàn)代性的矛盾與生俱來,但由于兩者的“同根同源”從而使得審美現(xiàn)代性與啟蒙現(xiàn)代性之間存在著既對立又相互依賴的張力狀態(tài),其動力和功能從根本上說是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不斷完善所需的自我修正和試驗。
與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不同,由于五四正處于思想文化啟蒙的肇始階段,更由于借思想文化(包括文學藝術)解決社會問題是五四啟蒙的基本思路,所以以新浪漫主義文學為所指的現(xiàn)代主義實際上將社會現(xiàn)代性與文化現(xiàn)代性、審美現(xiàn)代性渾融一體。“當五四作家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美學中的現(xiàn)代主義那種藝術上的反抗意識聲氣相通的時候,他們并沒有拋棄自己對科學、理性、進步的信仰。”[21](P236)五四文學最醒目的特征是:中國作家并非在自己的內心或藝術范疇中有所反省;而是假借外在的現(xiàn)實,極為顯眼地展現(xiàn)自己的個性。在這層意義里,五四文學在某種程度上近似于西方初期的現(xiàn)代主義。[14]其中最具論辯力的個案莫過于魯迅及其《野草》,“《野草》的人生哲學作為20世紀的產物,它與現(xiàn)代人本主義思潮尤其是以存在哲學的名字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非理性主義確實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淵源……但是這種深刻聯(lián)系只有被置于魯迅獨特的精神結構和中國社會文化的復雜狀態(tài)中才是真正有效的……它把‘無路可走’的境遇中的‘絕望抗戰(zhàn)’作為每一個人無可逃脫的歷史責任,把義無返顧地執(zhí)著于現(xiàn)實斗爭作為人的生存的內在需要,從而使人通過反抗而體驗并賦予人生與世界以創(chuàng)造性意義。”[23](P288-290)以致梁實秋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浪漫趨勢》中將這種現(xiàn)代主義與啟蒙現(xiàn)代性難以分離的新浪漫主義稱之為“浪漫的混亂”,“浪漫的混亂”正是對新浪漫主義之所以只存在于五四新文學中的確切定位。
顯然,現(xiàn)代性語境中的存在主義選擇成為新浪漫主義文學的“問題意識”生成點:一種真正具有“現(xiàn)代主義”特質的文學現(xiàn)象。乃至可以說,在五四文學中,沒有存在主義,現(xiàn)代主義顯得很不合理;沒有現(xiàn)代主義,新浪漫主義同樣令人不解。
三
如果說,非理性主義是從文化價值立場和審美思維層面,現(xiàn)代主義是從時代精神氣質和藝術觀照方式上來言說新浪漫主義,那么由生命哲學轉換的生命詩學則成為新浪漫主義文學的話語意義的構成性內涵。
魯迅先生明言“新文學是在外國文學潮流的推動下發(fā)生的”[24](P339),具體說,“對其產生影響的‘世界之思潮’、‘外國文學潮流’主要有三種:一是以易卜生為代表的以個性主義為特征的現(xiàn)代理性哲學思潮;一是以叔本華、尼采、柏格森、弗洛伊德等人為代表的標舉‘體驗’的現(xiàn)代人文主義哲學思潮;再就是以杜威、羅素等人為代表的重實證的現(xiàn)代科學主義哲學思潮,即‘賽先生’。雖然后來的發(fā)展表明,個性主義和科學主義思潮占據(jù)了壓倒性的主流地位,但就五四時期對中國文學影響的深廣度而言,叔本華、尼采等人的現(xiàn)代人文主義哲學思潮的影響更明顯、更深遠,這是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產生的特殊的歷史文化語境密切相關的。魯迅所指的‘世界之思潮’、‘外國文學潮流’,主要指的就是這種現(xiàn)代西方非理性文學思潮。”[14]
所謂“標舉‘體驗’的現(xiàn)代人文主義哲學思潮”顯然是指西方現(xiàn)代生命哲學。一般而言,廣義的生命哲學探究人的生命存在或者生存問題,它賦予人的生命存在以一種本體論意義:把生命意向提升為宇宙世界的本原和本質;而把握這種生命存在狀態(tài)主要取決于諸如“直覺”、“觀”、“領悟”等非理性思維方式。“最狹義的生命哲學,所指的當然是西方20世紀以狄爾泰、柏格森為代表的哲學流派,以至包括以叔本華、尼采為代表的意志主義,乃至于以海德格爾、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哲學。”[25]這也是學界對生命哲學是存在主義構成性資源的共識。在這里“哲學活動同其他生命浩劫錯雜在一起,理論活動成了一種生命活動”[26]。
如前所述,由于時限的原因五四文學的生命詩學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形態(tài)對應的恰恰也是以生存意志論及柏格森式生命哲學為標識的前期存在主義。問題也許在于,自王國維以叔本華的生存意志說闡釋《紅樓夢》開始,中國生命哲學(詩學)的現(xiàn)代轉型就已經開始。王國維的生命哲學(詩學)與西方生命哲學當然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但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探詢生命哲學(詩學)的起點,他的思考無疑開啟了20世紀中國文化、文學探尋生命哲學乃至存在主義的思路。幾乎與20世紀中國文學同步,“中國的生命詩學是在20世紀的新文學運動中才開始發(fā)軔,并在20世紀中西文化的碰撞與交織中得以充實與發(fā)展……五四時期郭沫若、宗白華、田漢等在西方詩學影響下張揚起了生命詩學的旗幟……它的源頭可以直溯郭沫若對尼采的‘藝術生理學’、宗白華對柏格森的創(chuàng)造進化論、田漢對廚川白村的苦悶象征說的接受。”“就生命詩學理論的發(fā)生而言,如果說尼采的‘藝術生理學’首先將肉體的生命引進現(xiàn)代中國詩學的理論視域,柏格森的創(chuàng)造進化論使中國的新詩人明白了生命意志是一個巨大的活力沖動,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則將這一生命沖動的內涵界定在生命遭遇壓抑的痛苦及其能量的爆發(fā)與轉化上。正是這三種影響了20世紀世界文化發(fā)展趨向的重要思潮的涌入,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生命詩學的哲學基礎,拉開了現(xiàn)代生命詩學建構的帷幕,使得現(xiàn)代中國詩學不僅關注詩自身生命的內部結構,而且開始關注詩與人的生命之聯(lián)系。”[27]
五四文學對生命詩學的弘揚者首推魯迅。可以說,魯迅對叔本華、尼采的生命哲學是積極認同和贊許的:“時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觀,或張皇意力,匡糾流俗,厲如電霆,使天下群倫,為聞聲而搖蕩。”“知主觀與意力主義之興,功有偉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故如勖賓霍爾所主張,則以內省諸己,豁然貫通,因曰意力為世界之本體也。”[8](P54)魯迅對生命詩學的執(zhí)著更在于他以生命自由來構建人的主體性。在《野草》中“那種懷疑一切、撞擊一切的勇氣和力量,那種不斷向人傾訴內心體驗,哪怕是黑暗體驗的真誠沖動,那種敢于虛無而獨自在荒原上舞蹈的自由精神……只有這種生命世界觀才能提供豐厚的資源。如果不聯(lián)系到這種生命世界觀,就很難接近他”[28]。1920年2月郭沫若在《學燈》雜志上發(fā)表題為《生命底文學》的論文,明確指出“生命是文學底本質。文學是生命底反映。離了生命,沒有文學”。
倘若將五四時期的生命詩學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形態(tài)稍加辨析,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當五四作家憑借生命詩學創(chuàng)造一種審美化生存時,在封建傳統(tǒng)積習深厚的現(xiàn)實生存中則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甚至感受到悲劇式的人生體驗。不同的是,魯迅是在“絕望”與“虛妄”中張揚尼采的強力意志和“超人”精神,用生命力去抗爭一切邪惡。“尼采的意圖就是要人走向悲劇藝術,通過悲劇意識去開掘生命本能中所有豐富的內涵,特別是通過悲劇藝術去喚醒生命藝術,使兩者合為一體,進而提升生命,實現(xiàn)生命最自由自在的活動。”[29](P139)即如《過客》中的“過客”在前行中無論前面是“墳墓”或“鮮花”都無所畏懼,惟其如此,個體存在才能在生命自覺意識觀照下呈現(xiàn)出存在論的價值和意義。而田漢、郭沫若(主要是小說)、郁達夫、廬隱以及淺草—沉鐘社諸成員在體驗到現(xiàn)實的悲劇性糾纏時,不是如魯迅那樣發(fā)揮尼采的生命強力意志去“反抗絕望”,而是像叔本華那樣由對現(xiàn)實的厭倦回歸到對生命欲望的悲劇性解脫,體驗著生存的“焦慮”,咀嚼著存在的“憂郁”,“這種憂郁和頹廢更多的是一種形而上的本體焦慮,是對個體生存的意義、靈魂歸宿乃至時間流逝的恐懼與詰問”[3](P187)。因此他們的筆下展示著所謂的“生的苦悶”和“性的苦悶”。這是五四作家直面生存現(xiàn)實對個人生命偶在性和屬己性的生、死、愛、欲等人生問題的自我辯難,明辨答案的渴望表現(xiàn)為帶有時代癥候的“世紀病”。它極似其前輩王國維的那種“望斷天涯路”的文化追詢,從而呈示出叔本華生命哲學的意味。叔本華對生命欲望的悲劇性解脫與尼采的藝術拯救說不同,它以否定生命意志為前提,因此叔本華的學說最終遁逸于類似于佛教的空無境界。
其次,五四時期的生命詩學對于西方生命哲學具有一種本土化的吸納功能,是對傳統(tǒng)生命哲學現(xiàn)代意義上的承傳。可以說,以“生”為本體的思想是中國文化的鮮明特征。儒學經典《周易》是中國生命哲學的源頭,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學觀把整個世界看成是大化流行的生命現(xiàn)象。由《周易》抽象而來的生命哲學揭示了宇宙本體發(fā)展變化的根源在于尚同天志以汲取普遍生命的精神以及人類剛健有為的創(chuàng)造精神。隨著儒教日益?zhèn)惱砘渖軐W也逐漸體現(xiàn)于“中和”觀念:消除心和物的對立從而達到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最終走向美善和諧與形神和諧——一種既是生命追求也是審美追求的最高境界。道家強調的是生命個體的價值與自由,莊子論道要求人們從人為的束縛中解脫出來感受人與自然融通的無尚快慰,體驗宇宙生命自由自在的無限樂趣。莊子提出“達生”之說是要通過體悟之路達到人與宇宙生命的完全契合使自我復歸于真實生命的本體,并進而演化為“道妙自然”之美即貫通了大道的障礙——讓人的存在呈現(xiàn)出一種本真狀態(tài):詩性棲居的狀態(tài)和體悟美感的境界。故而道家思想與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最為接近。而佛教的意旨是助眾生了解生命的意義以充實生命的內容,至于如何充實生命,禪宗強調圓融之境——生命意義的圓滿為最高的生命境界。其實禪學的核心話語“禪”即以生命為主體,在禪學看來,圓就是禪,也就是生命本體與宇宙本體是圓融一體的,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是冥然合一的。因此,心本就是圓,只有圓融無礙才能體悟到天地之心和去偽存真、圓悟圓覺,才能達到與天地一體的圓通禪境,領悟和把握自己的本心、本性——一種生命最高存在方式。簡言之,中國傳統(tǒng)生命哲學更多的是強調對生命的藝術化觀照:在藝術實踐和審美體悟里尋求生命存在的意義,這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生命詩學。就五四生命詩學尤其是其創(chuàng)作實踐層面而言,以魯迅和田漢領銜大致可分為“生命藝術化”和“藝術生命化”兩類。
生命藝術化主要以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生命哲學觀為主體并整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創(chuàng)化說”,尼采以“酒神精神”為驅動的生命意志論進而熔鑄成生命藝術化的獨特質素。魯迅以深刻的“中間物”意識在《野草》中創(chuàng)建了一個獨特的生命世界。所謂一切都是“中間物”實則意味著無論是對于歷史/現(xiàn)實還是對于東方/西方都呈現(xiàn)出“在”而又“不屬于”的張力狀態(tài)。在《野草》中“魯迅以這樣一個動態(tài)的生命,同各種思想遺產和思潮處于復雜的糾纏關系中……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克服邏輯之嫌,以一種整全的方式去領會這個世界,從而把握存在”[30](P40)。如果說,生命藝術化諭示著藝術是生命存在的一種基本需要,那么藝術生命化則體現(xiàn)著藝術是一種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
藝術生命化基于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論。既然生存意志的本質就是痛苦叔本華尋找著解脫人生苦難的良方:只有否定生存意志,其途徑便是藝術創(chuàng)造、審美直觀以及哲學沉思。而狄爾泰的生命體驗方式和柏格森的生命直覺方式恰恰能使得主體“自失”于體悟中,由此把握生命的實存意義也就濾卻了叔本華式的虛無主義人生觀。所有這些再通過心物俱冥、物我統(tǒng)一(道家),天人合一、形神和諧(儒家)以及圓融無礙、人生與審美冥合(禪宗)的境界等具有本土化生命哲學的融洽進而熔鑄為五四生命詩學中藝術生命化的創(chuàng)作現(xiàn)象。田漢早期劇作追求人的個性生命的獨立,尤其崇拜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以全生命求其美”的生命意識,在一種“人生錯失”和“生命有憾”的深層戲劇情節(jié)結構中表現(xiàn)生命沖突的內在張力。但他不似王爾德那樣把美作為一種個性生命在靈與肉兩方面徹底享樂的對象,而是將生命內部靈與肉的沖突轉化為外在的現(xiàn)實與理想,社會丑惡與人生之美的沖突,注重繪寫由于生命的困惑所引起的人性的痛苦、生命的困惑、存在的尷尬。而滲透其間的生命之思往往與家國興衰、人生無常、離愁別恨、無名感傷等聯(lián)系在一起。由是,藝術生命化以生命本體存在為構思的邏輯起點,在對唯美傳統(tǒng)、超越情懷、感傷氣質以及生命意義的探究、存在價值的追詢中,借助“感性本體論”或“此岸生存論”將理想社會和生命境界通過想象性關系連接起來。
無疑,五四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生命詩學形態(tài)體現(xiàn)出一種以存在主義為價值指向的現(xiàn)代人本主義文學傾向,也是在此意義上,五四文學的生命詩學及其創(chuàng)作實踐對于存在主義文學來說已具備了創(chuàng)作本體論的意義。
綜上所述,以新浪漫主義為文學表征,以現(xiàn)代主義為時代精神氣質和藝術訴求方式、以生命哲學、生命詩學為創(chuàng)作話語的意義構成,以存在主義為“詩”之“思”的話語本體內涵的“現(xiàn)代非理性文學思潮作為一種強大的異域文化力量,從一開始就參與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建構過程……在一定意義上也構成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性’的一個重要標志”[5](P608-609)。
[1]梁實秋.現(xiàn)代中國文學之浪漫趨勢[A].梁實秋批評文集[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2]茅 盾.茅盾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3]肖同慶.世紀末思潮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4]高力克.分裂的現(xiàn)代性:社會與文化[J].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1998,(1):1-5.
[5]朱德發(fā).20世紀中國文學理性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法]約瑟夫·祁雅理.二十世紀法國思潮(吳永泉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7][美]W·考夫曼.存在主義(陳鼓應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8]魯 迅.魯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9]郁達夫.郁達夫全集:第5卷[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2.
[10]魯 迅.魯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1]解志熙.生的執(zhí)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12]自劉平.戲劇魂——田漢評傳[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3]葛紅兵.“五四”文學審美形式論[J].江漢論壇,1999,(1):74-80.
[14]朱德發(fā),溫奉橋.非理性視野中的現(xiàn)代中國文學[J].北方論叢,2003,(4):90-97.
[15]俞兆平.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浪漫主義的歷史反思[J].文學評論,1999,(4):123-133.
[16]楊春時.文學思潮:一種現(xiàn)代性反應[J].粵海風,2006,(4):6-8.
[17]張清華.中國當代先鋒文學思潮論[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
[18]王富仁.中國現(xiàn)代主義文學論(上)[J].天津社會科學,1996,(4):66-75.
[19]俞兆平.論魯迅早期的浪漫主義美學觀念[J].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3):71-77.
[20]張大明.“五四”文學革命傳統(tǒng)芻議[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2):52-56.
[21]李歐梵.現(xiàn)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0.
[22]陳思和.試論“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鋒性[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6):11-27.
[23]汪 暉.反抗絕望——魯迅及其文學世界[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24]魯 迅.集外集拾遺補編——魯迅全集單行本[C].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25]黃玉順.生存結構與心靈境界——面向21世紀的中國哲學[J].周易研究,2002,(4):16-24.
[26][西]加塞爾.什么是哲學(商梓書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27]譚桂林.現(xiàn)代中國生命詩學的理論內涵與當代發(fā)展[J].文學評論,2004,(6):95-103.
[28]王學謙.青年魯迅生命世界觀結構及其文化類型分析[J].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2):243-262.
[29]周春生.悲劇精神與歐洲思想文化史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0]王乾坤.魯迅的生命世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責任編校:譚容培)
Neo-Romanticism:the Rel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y Forth Literature and Existentialism
YANG Jing-j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 valu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and existentialism has been realized in recent years.To probe the existentialism tendency of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from“Neo-Romanticism”is a generic point of a new kind of“problem awareness”.The“Neo-Romanticism”Literature arose from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enlightenment historical context of modernity.It takes the irrationalism as the cultural value standpoint and the aesthetic thinking form,takes modernism as the token of the time spirit and the artistic pursuance,takes life philosophy and life poetics as the significance connotation of the creative content.Through these constructing system of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it confirmed the valu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 and Existentialism.
the May Fourth Literature;existentialism;Neo-Romanticism;irrationalism;modernism
I206.6
A
1000-2529(2010)01-0108-07
2009-09-15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世紀中國存在主義文學論”(09YJA751025)階段性成果
楊經建(1955-),男,湖南瀏陽人,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
book=138,ebook=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