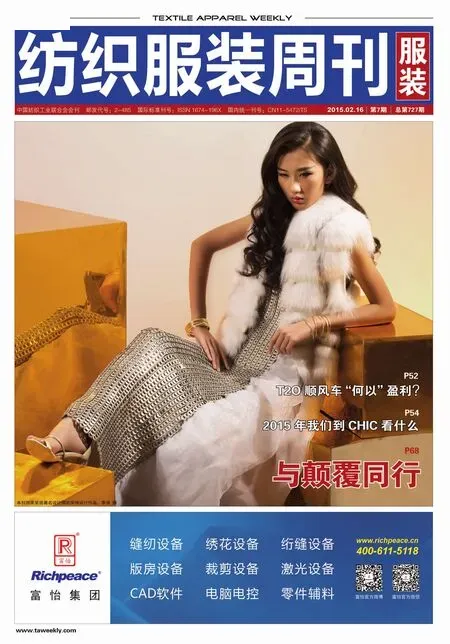化纖產業的升級樣板盛虹科技依靠新型聚酯掌握市場話語權
本刊記者_郝杰 文/攝
化纖產業的升級樣板盛虹科技依靠新型聚酯掌握市場話語權
本刊記者_郝杰 文/攝
走進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產車間,整潔的空間、干凈的地面、機器轟鳴,潔白的絲餅順著生產線下來被一個個機械手抓起,準確地放到來回穿梭的運輸小車里。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張葉興告訴記者,這里生產的不是一般的聚酯長絲,而是PTT功能性纖維。這種纖維的背后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PTT聚合生產技術,以及新型聚酯系列化復合技術。盛虹依靠年產3萬噸 PTT聚合生產能力,使其成為繼美國杜邦和殼牌后第三個掌握PTT聚合技術的企業,25萬噸熔體直紡全消光纖維生產線讓盛虹得以繼續在功能性化纖領域處于領先地位。“新型聚酯聚合及系列化復合功能纖維制備關鍵技術”因此獲得紡織之光2014年度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科技進步一等獎。
最具發展潛力的聚酯品種
獲得紡織科技的最高榮譽讓盛虹人興奮不已,他們還清楚地記得,兩年前杜邦公司的高層曾專門來到盛虹,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收購盛虹的這項創新成果,盛虹人當時給出的答復就是“出什么價格也不會賣,一定要自己做”。
是什么樣的纖維讓杜邦如此緊張?聚酯纖維占我國紡織纖維總量的60%以上,同質化現象嚴重,產能過剩,企業利潤微薄。美國杜邦公司開發的PTT纖維被看做是未來聚酯纖維重要的替代產品,它綜合了錦綸的柔軟、腈綸的蓬松、滌綸的抗污以及接近氨綸的彈性恢復能力,將多種化纖優良性能集于一身,被稱為21世紀最有發展潛力的聚酯品種,是目前化纖行業開發的重點領域,具有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由于PTT聚酯原料PDO合成十分困難,PTT聚酯合成技術一直被美國殼牌和杜邦兩家公司所壟斷。
早在2005年杜邦公司就開始在中國市場推廣PTT纖維,杜邦緊緊抓住PTT纖維產業鏈頂端的PTT聚酯切片生產技術,對中國企業只通過合作的方式出售PTT切片。盛虹看到產品良好的發展趨勢,就引進了國內第一條生產線,采用杜邦的原料進行生產,“當時產品供不應求,附加值很高。” 張葉興回憶說,杜邦公司后來看到了市場潛力,他們不想讓盛虹一家獨大,因此轉而發展更多的客戶。他們開始在原料上進行限制,減少供應切片,這意味著市場機會就要喪失。“最嚴重的時候,盛虹每月需求600噸PTT聚酯切片,杜邦只供給150噸。” 張葉興說。
打破壟斷獲美國專利
盛虹意識到,要擺脫國外公司的限制就必須擁有自己的聚合技術和生產能力,自己解決原料問題。2008年,盛虹與國內院校和設計公司合作,開始了PTT聚合技術的研究。研發的過程中有很多難點,最難的是催化劑的穩定性,因為催化劑抗水解能力差,在酯化過程中容易水解,水解后就會失效。研究過程很緊張,經過數月的努力這一難題才被攻克,為后續的研發奠定了基礎,也鼓舞了研發人員的士氣。
這以后,聚合速度及產品質量的有效控制、副反應的控制及副產物處理、PTT結晶速率的調控等一系列難題先后被攻克。我國首條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3萬噸/年PTT及改性PTT生產線終于建成,PTT聚酯切片的主要物理指標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色相明顯優于殼牌和杜邦產品。打破了國外的技術壟斷,填補了國內空白。
隨后,盛虹又在全球率先實現了25萬噸/年熔體直紡全消光復合功能聚酯纖維產業化,產品質量指標達到國際領先水平。該技術與切片紡工藝相比,無需熔體造粒與切片預結晶、干燥工藝,可大幅降低終端產品的能耗。大容量熔體直紡工藝的成功開發,進一步降低了建設投資、產品的物耗、能耗及人員費用等,生產出了吸濕、抗靜電、抗紫外線、彈性等不同組合的功能聚酯纖維。
新型功能性纖維的推出受到了市場的熱捧,包括日本帝人、東麗都成了盛虹的客戶,近三年來,盛虹累計銷售系列化功能纖維42.7萬噸,銷售額達 65.03 億元,利稅為7.28億元,出口創匯1400.28 萬美元,產品已出口歐、美、日、韓等國家。由于掌握了產品的話語權,在最近石油價格大跌中,該產品售價并未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