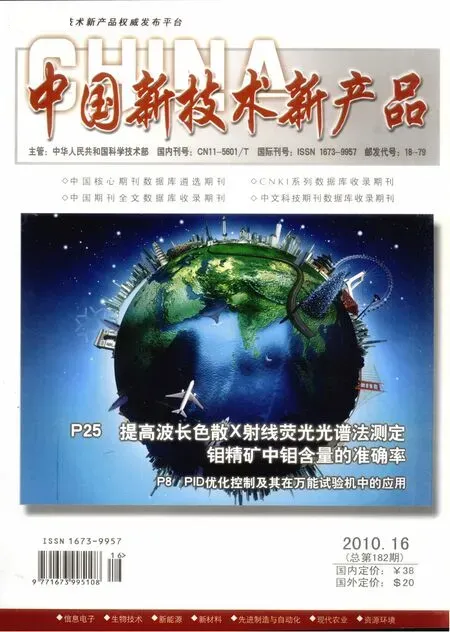基于財政科技投入的基礎(chǔ)研究績效評價指標(biāo)體系研究
曹京京 陳世高 梁嘉明
(廣東省技術(shù)經(jīng)濟(jì)研究發(fā)展中心,廣東 廣州 510070)
基礎(chǔ)研究作為最具前瞻性和探索性的知識創(chuàng)新活動,是新技術(shù)源泉,與技術(shù)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日益密切。基于公共財政理論,政府對高等院校基礎(chǔ)研究的投入屬于公共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基礎(chǔ)研究投入的主體。將“績效”引入到財政管理是我國改革和轉(zhuǎn)型的一項重要舉措。實行財政部門實行量化績效管理的大背景下,“績效評價”是績效管理體系的重要工具和依據(jù)。因此,開展基礎(chǔ)研究績效評價體系研究,建立操作性前的、全面的績效指標(biāo)體系,為基礎(chǔ)研究活動績效評價提供基礎(chǔ)性工具,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1 評價指標(biāo)篩選的原則
基于財政科技支出的基礎(chǔ)研究績效評價指標(biāo)體系,是度量高等院校基礎(chǔ)研究的發(fā)展水平和效率的工具,為了使測量結(jié)果全面、準(zhǔn)確、客觀,在選取評價指標(biāo)時,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1.1 系統(tǒng)性原則
評價指標(biāo)體系設(shè)計遵循系統(tǒng)性原則,即要求所建立的評價指標(biāo)體系具有足夠的涵蓋面,包括學(xué)術(shù)成果、人才培養(yǎng)、成果產(chǎn)業(yè)化、改善科研條件等多個方面,反映充分的信息量。
1.2 科學(xué)性原則
指標(biāo)體系的科學(xué)性要求制定評價指標(biāo)體系時,應(yīng)注意遵循基礎(chǔ)研究活動的規(guī)律,所選取的指標(biāo)要能體現(xiàn)出高等院校基礎(chǔ)研究活動的不同特點。
1.3 可比性原則
即要求評價指標(biāo)體系中各指標(biāo)的含義、統(tǒng)計口徑、統(tǒng)計時間和范圍等必須明確,以確保評價結(jié)果能夠進(jìn)行橫向與縱向比較。因此,評價指標(biāo)應(yīng)盡量平衡相對指標(biāo)和絕對指標(biāo)。
1.4 可操作性原則
引理2[5] G是一個(p,q)圖,s和m均為整數(shù).如果G是s-邊優(yōu)美的,那么G也是(mp+s)-邊優(yōu)美的,即{k≥s:k≡smod p}?EGI(G).
這一原則主要包括3方面的內(nèi)容:數(shù)據(jù)資料的可獲得性,數(shù)據(jù)資料能通過調(diào)查問卷獲得;數(shù)據(jù)資料的可量化性,定性指標(biāo)盡量少用,定量指標(biāo)要保證其數(shù)據(jù)的真實、可靠、有效;評價指標(biāo)不宜過多,應(yīng)盡可能簡化。
2 績效指標(biāo)研究綜述
目前,國外學(xué)者對基礎(chǔ)研究績效指標(biāo)的研究較多,但是,他們提出的績效指標(biāo)比較寬泛,操作性不強,以定性為主。相對而言,國內(nèi)學(xué)者或機(jī)構(gòu)研究提出的指標(biāo)則比較具體,更具實踐指導(dǎo)價值。因此,本文以國內(nèi)研究和實踐中提出的績效指標(biāo)為參考(詳見表1),通過綜合各方意見提出本文的績效指標(biāo)體系框架。
國內(nèi)學(xué)者從不同評價需求,提出基礎(chǔ)研究績效指標(biāo)涵蓋的內(nèi)容也不盡相同。例如,李正風(fēng)等(2002)和孟等(2005)提出的績效指標(biāo)包括論文、專著、學(xué)術(shù)會議報告、專利等,屬于基礎(chǔ)研究活動的直接產(chǎn)出績效。而周洪芳等(2002)提出的績效指標(biāo),既包括項目后續(xù)應(yīng)用和人才培養(yǎng)等間接績效指標(biāo),也包含了論文、專利、獲獎等直接績效指標(biāo),但是卻沒關(guān)注專著、會議報告等指標(biāo)。
與此同時,國家和地方科技行政部門根據(jù)工作需要,也開展基礎(chǔ)研究績效調(diào)查實踐,提出了相應(yīng)的績效指標(biāo)。國家科技部基礎(chǔ)研究管理中心(2006)為了掌握各省市基礎(chǔ)研究能力和國家基礎(chǔ)研究項目實施情況,進(jìn)行績效調(diào)查時,創(chuàng)新性地提出了研究平臺條件、項目團(tuán)隊水平、專項經(jīng)費等投入指標(biāo)。其指標(biāo)涉及面廣,較宏觀,但是沒有采用專著、會議報告、以及后續(xù)項目應(yīng)用、人才培養(yǎng)等指標(biāo)。廣東省自然科學(xué)基金績效評價小組(2007)提出的基礎(chǔ)研究直接產(chǎn)出成果和間接產(chǎn)出成果方面的指標(biāo)也沒把學(xué)術(shù)會議報告納入其指標(biāo)體系。此外,該小組還研究提出了項目管理方面指標(biāo),關(guān)注的是基礎(chǔ)研究工作制度性建設(shè),值得我們進(jìn)一步研究。

表1國內(nèi)基礎(chǔ)研究績效指標(biāo)研究成果匯總
3 績效指標(biāo)分析
本研究認(rèn)為,以項目為單位進(jìn)行調(diào)查統(tǒng)計時,為了保障評價結(jié)果的客觀全面,以及滿足后續(xù)組合評價工作需要,應(yīng)根據(jù)系統(tǒng)性、科學(xué)性、可比性等原則,來分析和篩選績效指標(biāo)。
3.1 投入指標(biāo)
國內(nèi)開展基礎(chǔ)研究績效調(diào)查時,投入指標(biāo)包括項目經(jīng)費、項目團(tuán)隊水平、研究平臺條件等三方面指標(biāo)。本論文認(rèn)為,項目經(jīng)費是政府為支持基礎(chǔ)研究活動而投入的資金,其最終會轉(zhuǎn)化成為科學(xué)研究所必須的人才、材料、設(shè)備、信息等資源;項目團(tuán)隊著重通過擁有的專業(yè)知識、科研經(jīng)驗以及辛勤勞動,攻克科學(xué)難關(guān),因此團(tuán)隊水平的高低對項目成敗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研究平臺條件指標(biāo)反映了項目承擔(dān)單位的科研條件和積累的基礎(chǔ)性成果水平,是項目團(tuán)隊啟動基礎(chǔ)研究活動的物質(zhì)基礎(chǔ),其優(yōu)劣對項目研究成敗具有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在建立績效指標(biāo)體系時,采納了以上三項指標(biāo)。
3.2 直接績效指標(biāo)
在產(chǎn)出指標(biāo)方面,論文情況、獲獎情況、專利、專著、學(xué)術(shù)會議報告是衡量基礎(chǔ)研究項目直接績效指標(biāo)。前三項指標(biāo)在國內(nèi)研究和實踐中已得到認(rèn)可,后兩項指標(biāo)具有一定爭議。我們認(rèn)為,專著是研究成果系統(tǒng)化、體系化的標(biāo)志,其學(xué)術(shù)價值和影響力不是論文所能代替的;學(xué)術(shù)會議報告則標(biāo)志著項目研究選題具有的前瞻性,研究進(jìn)展和成果代表該領(lǐng)域研究的最新水平,因此,我們采納了這兩項績效指標(biāo)。
3.3 間接績效指標(biāo)
在過去的研究和實踐中,項目后續(xù)應(yīng)用、人才培養(yǎng)與引進(jìn)、設(shè)備購置等指標(biāo)被用于衡量基礎(chǔ)研究項目間接績效。其中,項目后續(xù)應(yīng)用情況反映了項目成果水平的高低,體現(xiàn)其社會經(jīng)濟(jì)價值,后續(xù)應(yīng)用領(lǐng)域越廣泛,得到各方資金支持越大,項目績效越大;研究人才是基礎(chǔ)研究的主體,通過項目實施,培養(yǎng)或引進(jìn)更多高級科技人才,增強地區(qū)基礎(chǔ)研究人才隊伍建設(shè)。培養(yǎng)或引進(jìn)人才越多,層次水平越高,項目績效越大;項目實施過程中購置科研設(shè)備,有利于改善科研條件,在其它成果產(chǎn)出不變的情況,購置科研設(shè)備越多,對項目承擔(dān)單位基礎(chǔ)研究能力強化作用就越明顯。因此,本論文建立績效指標(biāo)體系時,采納了以上三項指標(biāo)。
3.4 過程管理指標(biāo)
廣東省自然科學(xué)基金績效評價小組(2007)提出的績效指標(biāo)包括了項目管理指標(biāo)。設(shè)計該指標(biāo)的目標(biāo)是用于評價省自然科學(xué)基金的管理制度建設(shè)情況,其評價對象是政府行政部門。但是,本文認(rèn)為,國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委員會、科技行政部門制定出臺的自然科學(xué)基金管理制度,對其資助的所有項目均有約束力,而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機(jī)構(gòu)的項目管理權(quán)已下放給科研團(tuán)隊或科研人員,科研管理部門基本不參與具體項目組織工作,因而對各個高校、院所的項目而言,該指標(biāo)是無差異化指標(biāo)。而且,項目績效評價本質(zhì)是以結(jié)果為導(dǎo)向的評價,所有過程管理均可通過產(chǎn)出指標(biāo)來體現(xiàn)。因此本文設(shè)計的指標(biāo)體系沒有采用過程管理方面指標(biāo)。
4 績效指標(biāo)體系的設(shè)計

?
在綜合、分析國內(nèi)學(xué)者以及政府有關(guān)部門實踐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基礎(chǔ)研究績效指標(biāo)之間相關(guān)性,依據(jù)可操作性原則,本文研究提出了基于財政科技支出的基礎(chǔ)研究績效評價指標(biāo)體系,(詳見表 2)。
該指標(biāo)體系共包含2個一級指標(biāo),6個二級指標(biāo),16個三級指標(biāo)。一級指標(biāo)由投入指標(biāo)和產(chǎn)出指標(biāo)兩項構(gòu)成。其中產(chǎn)出指標(biāo),按照績效屬性分類合并,確定了學(xué)術(shù)成果、知識產(chǎn)權(quán)、研究能力強化作用等幾個方面指標(biāo):
4.1 “學(xué)術(shù)成果”(2.1)部分是基礎(chǔ)研究直接績效成果之一,包括論文、專著、學(xué)術(shù)會議報告、成果獲獎情況等。此外,由于后續(xù)項目來源和資金是衡量學(xué)術(shù)成果水平的重要指標(biāo),因此把這兩項指標(biāo)歸并到這一部分。
4.2 “知識產(chǎn)權(quán)“(2.2)是對項目科研成果水平的標(biāo)準(zhǔn)化調(diào)查,這主要是因為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申請和授權(quán)是有明確制度規(guī)定和嚴(yán)格審查的,并且在產(chǎn)業(yè)化應(yīng)用方面具有排他優(yōu)勢,是論文、著作等學(xué)術(shù)性成果的重要補充,也是直接產(chǎn)出。
4.3 “成果價值“(2.3)部分則是定性指標(biāo),涵蓋了社會、科技、經(jīng)濟(jì)三大領(lǐng)域,是對項目成果應(yīng)用價值的主觀調(diào)查。
4.4 “研究能力強化作用“(2.4)則是綜合了“人才培養(yǎng)情況“、“購置科研固定資產(chǎn)“、“學(xué)科地位情況“等三個方面。設(shè)計這三項指標(biāo)主要因為,一方面,與其它科研活動相比,基礎(chǔ)研究是風(fēng)險性更高的科研活動,并不是每個項目都是成功的。對于失敗的項目,只要通過項目實施,在“失敗“中獲取經(jīng)驗,為同行或他人提供了該項研究“不可行“理論依據(jù),那么該項目“失敗也有績效“。另一方面,打造了一個有經(jīng)驗的科研隊伍,創(chuàng)造了更好的科研條件,研究能力的強化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1]李正風(fēng).基礎(chǔ)研究績效評估的若干問題《.科學(xué)學(xué)研究》.2002(4).P67-71
[3]周洪芳,陳文賢,張林.醫(yī)藥類基礎(chǔ)研究項目的績效評價初探《.中華醫(yī)藥科研管理雜志》.2002(9).P155-157.
[4]國家科技部基礎(chǔ)研究管理中心.基礎(chǔ)研究數(shù)據(jù)采集表.內(nèi)部資料.2006.6
[5]廣東省科技廳開展自然科學(xué)基金專項績效評價小組.2005年廣東省自然科學(xué)基金財政支出績效自評報告.內(nèi)部報告.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