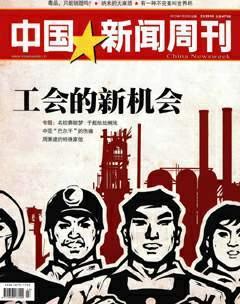一個維權者的工會情結
劉子倩

自從看到南海本田工人停工的消息,張軍一連幾天睡不好覺。作為過來人,張軍深知處在各方博弈漩渦中的工人,維權之艱難。
這種擔心一直持續著。當千里之外的本田工人提出重組工會的訴求時,他喜憂交加。喜的是,這些剛滿20歲的年輕人提出如此訴求,難能可貴;憂的是,他不愿看到這些剛剛成年的孩子最終在與資方的較力中一敗涂地。
騎著一輛破舊的二手摩托,沒有固定的工作,一家三口蝸居于44平米的斗室。這就是一個工會維權者的現狀。
作為土生土長的煙臺人,張軍身材中等,皮膚白皙,說話溫文爾雅。此前,他過著寬裕的生活,工作有序,收入穩定,在煙臺算得上中等水平。但當他與工會維權結合起來后,他的生活便發生了變化,平日談笑風生的閑聊,變成了維權的爭吵,每月固定的收入大部分填進了工會的腰包。
而改變張軍的命運的,正是他對于工會的不斷夢想。
為妻子“討說法”
2006年春節前,張軍的老婆通過面試成為了澳利威公司的員工。該公司承諾春節后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相對于當地每月53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澳利威每月1200元的收入,對當地人頗具誘惑。
妻子順利入職澳利威,讓張軍懸著的心也落了下來。但春節后發生的一系列變故讓夫妻二人始料不及。澳利威公司不僅沒有和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反而兩次降低工人的工資。更離譜的是,在“五一”勞動節前夕,公司更是辭退了58名女工,其中包括張軍的妻子劉美珍。
張軍看不過妻子“受氣”。于是,他干脆帶著這58名女工集體到福山區勞動局去“討說法”。
通過與勞動局的多次談判,張軍為女工們要到了300元的補償金。但劉美珍等7名工人不想要300元補償,對她們來說,每月千余元的收入和固定繳納的社保更為重要。
在張軍多次交涉下,7名女工一個月后重新回到了澳利威公司。然而,澳利威公司的勞資關系日益緊張,工人們對資方日益不滿,成立工會的呼聲高漲。
2006年10月,在工人代表的帶領下,工人們試圖通過罷工的形式成立工會。為此,張軍專門請假過去聲援,揭露工廠違法事實,號召工人團結一致。最終,澳利威130多名工人中,有110名在要求成立工會的申請書上簽了名。對于這個女工占99%的企業,簽名率如此之高實屬不易,張軍由衷地佩服女工們的勇氣,甚至回到家中仍為妻子加油打氣。張軍突然發覺,在這些女工身上,似乎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
有工會情結
張軍的人生似乎注定要與工會維權聯系在一起。1987年,不滿17歲的他進入一家國營企業不久,就成了工會會員。而這家企業的工會對工人的關心也讓張軍第一次意識到了工會的溫暖。之后,他先后在不同的企業工作,但這些企業均未設立工會組織。
直到2001年,張軍進入一家擁有工會的中美合資企業,這勾起他對工會的美好回憶,上班第一天他就找到工會主席,申請加入工會。
工會主席以張軍處于試用期為由拒絕了他的申請。雖然規定是三個月的試用期,但半年后張軍仍未轉正,學法律出身的他知道公司違反了《勞動法》,于是尋求工會的援助,并將試用期過長的問題反映給了當地勞動部門。讓張軍未曾想到的是,兩天之后,工會主席通知他,“你被公司辭退了。”
張軍不服,把公司告上了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而更讓張軍吃驚的是,仲裁庭上的公司代表竟然還是這位工會主席。最終,張軍輸掉了那場官司。
這個經歷,讓工會在張軍心目中的印象發生了180度的轉變。時至今日,張軍總有一句話掛在嘴邊:“我是被工會傷害過的。”
或許出于本能,張軍不想讓包括妻子在內的女工們再受到企業的傷害,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勢在必行。
盡管澳利威公司給工人設置了層層障礙,甚至阻止福山區總工會負責人進入廠區與工人接觸,但張軍已篤定要聯合工人,以最大的勇氣爭取利益。
隨后,他通過電話與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取得了聯系,并向全總說明了要求成立工會的情況。經過多級工會的努力,2006年10月20日,在煙臺市總工會與福山區總工會的主持下,按照法定程序,澳利威的工人直選投票,選舉出澳利威工會的工會主席、副主席及工會委員,共5人。她們均為生產線上的普通工人,并全部都參與了罷工。作為工會的幕后推手——張軍,則被聘為工會顧問。
成了工會顧問,張軍的工會情結再次被激發。不會打字的他為了提高工會人員的法律意識,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手抄出一套勞動法律手冊,印發給工人。除此之外,為了更好地宣傳工會,張軍購置電腦,安裝寬帶,學習寫博客。同時,為了工人維權,他還添置了用于取證的DV、相機、錄音筆等數碼器材。雖然妻子工作穩定下來,但一心投入工會的張軍因經常曠工,收入驟減。
但張軍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這個工會的意義非同凡響。
夢想何時照進現實
然而,張軍并未料到種種困難接踵而至。盡管他們手里拿著上級工會批準成立的文件,但澳利威公司對工會不予認可,并稱該工會是通過罷工成立起來的非法工會,限制工會干部辦理正常事務,并對支持工人訴訟的工會干部給予曠工處分,扣除工資。
對于類似問題,張軍曾多次向上級工會反映,但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在澳利威工會成立后的第一個工作日,福山區工會的一個領導就善意地提醒張軍,不能做與公司對抗的事情,否則公司會采取對工會主席不利的行動。
一年后,澳利威工會另一個副主席于麗艷也被澳利威公司開除。隨后,于麗艷向福山區勞動監察大隊投訴澳利威公司,并向福山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了仲裁,至今也未有結果。
民選的工會主席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卻無法令資方滿意,當資方拿走工會主席的飯碗時,這個曾令張軍們無限自豪的工會立刻脆弱得不堪一擊。然而,上級工會又無法提供有力的支持,使這個直選工會處境更為尷尬和艱難。
張軍未曾想過,阻力如此之多,來勢如此迅猛。然而,回想起工會成立之后所做的一切,張軍又隨即釋然:在澳利威工會的監督和投訴下,澳利威公司逐步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
其中一個特殊的維權案例令張軍頗感自豪。澳利威公司一名副總裁因工作問題被辭退,但公司并未按合同給予賠償。這位副總找到張軍,最終通過工會幫其索要到近萬元的賠償。張軍說,工人的正當權益受到資方侵害時,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這也是工會精神的體現。
但在資方眼中,張軍是工會真正的幕后推手。一位研究工會領域的學者,在對澳利威工會做了系統調研后,將張軍稱為“澳利威工會維權行動的靈魂”。事實上,自工會成立起,工會的文件起草,方針制定,戰略實施均由張軍負責。
盡管處處碰壁、備受打擊,但是張軍并沒有放棄努力。2009年9月,張軍接受丹麥工人聯合會的邀請,赴丹麥介紹煙臺澳利威工會經驗,并到澳利威集團總部,當面表達對澳利威公司打壓中國基層工會的不滿。這標志著張軍作為一名中國普通工人在歐洲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2009年4月,盡管張軍是他所在公司的唯一一名電工班長,但是該公司在張軍的勞動合同到期時還是終止了和他的勞動關系。就在此時,煙臺澳利威公司因搬遷關門停產,凝聚張軍心血的澳利威工會也名存實亡。如今,閑下來的張軍仍會定期更新“澳利威工會”的博客,這里是他的輿論陣地。此外,張軍還注冊了網名為“澳利威熱線”的QQ,為工人免費提供法律咨詢服務。
眼下,張軍每天都密切關注南海本田的消息,他發現,本田停工與澳利威罷工都有同樣的維權訴求,但前者比后者方式更溫和,態度更強硬。但讓他憂心忡忡的是,工人重組工會的訴求,只是工會意識的萌芽,并未提出明確的重組方案,“這也超出了他們的經驗范圍,所以這個階段他們更需要業內人士的指導。”張軍說,只要工人需要,他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