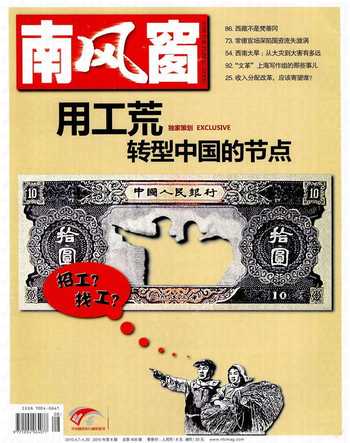拯救政府公信力
王大鵬

當政府相關部門都已經成為相關的當事方時,由他們出面調查已經難以保證客觀公正,所以,為提高公共事件調查的公信力,適時引入第三方進行調查勢在必行。同時也應該加強立法和司法部門的監督,而不是由當事部門自己調查。
近年來,公共衛生事件多有發生,包括安徽阜陽問題奶粉和三鹿奶粉事件,特別是最近發生的山西和江蘇的“疫苗”事件、嘉禾血鉛超標事件問題已經直指我們的后代了。其中山西“疫苗門”事件,至今已歷時3年之久,經過了患者家長長期的奔走呼號,經過了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科原科長陳濤安的多次舉報,還經過了《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的明查暗訪及公開詰問,終于引發了社會的強烈關注。
今年1月份的《瞭望》刊登《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的文章說,中國將持續面臨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威脅,人類能夠做到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災害降臨之前,構筑一道堅固的公共衛生防御屏障,建立起健全快速應急反應體系,預防和減少疾病的發生和流行。
和這種威脅相對應的就是政府公信力危機。
“被監督者”的邏輯
從目前披露的信息看,山西疫苗案問題出在流通環節;江蘇疫苗案問題出在生產環節。要真正理解“疫苗事件”,就必須理解中國的“疫苗體制”。在衛生部出臺《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之后,疫苗分為二類,一類是免費的(所謂一類疫苗),是政府完全“埋單”;一類是“市場化”的(所謂二類疫苗),由被注射者自己掏錢。這樣的分類也是恰當的,因為“二類疫苗”包含著很多特殊需求,而不像“一類疫苗”是針對基礎需求(比如小孩“乙肝疫苗”)。同時,“二類疫苗”鼓勵疫苗生產企業競爭。如果有很好的市場、社會和專業的監督機制,監管部門和企業的合作不容易出大問題。但如果變成了政府部門和不法企業合作壟斷市場,排擠競爭者,屏蔽所有的監督,隱藏所有的信息,攫取壟斷利潤,那么就會出大問題。
此時,一旦出現了大問題,政府部門也就會出現被監督者的被監督行為邏輯,其模式在于:事件曝光后,首先是隱瞞和控制信息;其次是利用自己的各種優勢;然后是能拖就拖,再推卸責任,在推卸不掉后才勉強承認,而不是首先考慮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正如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分析的那樣:“不管任何人,遇到監督的時候,都會盡力自我保護。一旦發現問題,被監督者,首先會隱瞞或否認事實。然后會盡可能利用自己的各種優勢,比如信息不對稱的優勢,專業知識的優勢,解決問題中的位置優勢等,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然后是盡可能開脫自己的責任。尤其當被監督者的問題比較大的情況下,尤其如此。”
而在以上這些公共衛生事件中,相關的地方政府也大都采取了回避、隱瞞等態度,直至最后無從逃避時,才出面糾錯。這其中,政府與民眾的關系變成了“貓鼠游戲”,博弈大于合作,這顯然與我們打造以人為本的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是背道而馳的。
而在此時,人們也通常會發現,在被監督者的行為邏輯下,一級政府會被整個動員起來控制事態的發展。除了媒體這個“異己”力量之外,人們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出面。因此,被監督者的行為邏輯也客觀上導致將各種社會風險引向中央政府。
在現代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誠實是保證決策信息真實完整的基礎,而信息真實完整則是決定決策是否科學的生命線,因此,“誠實”乃公共政策的最優選擇。一個誠實的政府才是一個勇于負責任的政府,才是一個具有現代行政道德意識的政府,才能得到公眾的認可。任何對公眾不誠實的行政行為,都是在自毀形象。從山西省政府的新聞發布會看,省政府、衛生廳已經以認真誠實的態度對待疫苗事件,勇于承受輿論壓力,積極回應輿論質疑,這是公開、透明、正確、及時地處置好此次事件的開始。
公共衛生事件中的第三方調查
在事件的邏輯鏈條中。地方政府在行政理念、行政制度、行政行為上都有“失范”之舉,這對政府公信力定然是一種傷害。因為實際上,像疫苗和疫苗注射這樣專業度高、同時直接關系到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行業,民眾最在乎的就是“正規”兩個字,而“正規”所代表的就是政府有關部門的認證、檢驗和監督。從這個角度講,當那些掛著政府有關部門認證標牌的企業,以繞過監管欺騙政府的手段生產或經營劣質產品的時候,例如疫苗、奶粉、藥品、食品等等,其所傷害的就不僅僅是民眾的利益,也傷害了政府有關部門的信用。因為民眾一直相信政府,也只能相信政府,如果政府有關部門最為嚴格監管的行業仍然出現問題,損害的不僅僅是民眾的健康,還有政府的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屬政治倫理范疇,是政府通過自身行為獲取社會公眾信任、擁護和支持的一種能力,它實質上體現了政府工作的權威性、民主程度、服務程度和法治建設程度。在某種意義上,政府公信力是一堵“防火墻”,公信力越高的政府,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概率就越低。
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又有所區別。2007年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對全國28個省市居民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民眾對中央政府信任度最高,而地方政府則次之。根據《小康》雜志2007年8月發布的《2006-2007中國信用小康指數》報告,2006-2007年我國政府公信力指數為60.6分,比上年提高了0.1個百分點。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超過70%的受訪者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著“隱瞞真實情況,報喜不報憂”的現象。這表明民眾對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不作為和亂作為的擔憂。
由于在公共衛生事件中,面對惡性事件,面對民眾對某個行業某類產品的信任危機,以及人群中潛在的恐慌情緒,政府作為終極擔保人出面,必然將疫苗的安全與政府有關部門的信譽捆綁在一起。在去年12月以前,江蘇延申是經過國家認證、在政府監管之下的“正規”疫苗生產企業。衛生部門是在這個認證的信用之上購買的這些假疫苗;民眾也是在這個認證的基礎之上注射的這種疫苗。
事實上,事情發展到現在,單靠其中一方來不斷澄清,已不能消除公眾懷疑。特別是在腐敗的陰影下,山西已喪失了科學檢驗的公正性,官方調查報告的主要專家來自疾控中心,報告不具有權威性和公信力已是不爭的事實。
要想弄清楚事實,必須有一個獨立的第三方介入調查。這個第三方可以是一個權威的、有公信力的調查組,調查組的成員和調查的每一個環節都要接受公眾的監督。沒有了利益牽扯的公眾的監督,其公信力也就有了保證。
再推而廣之,當政府相關部門都已經成為相關的當事方時,由他們出面調查已經難以保證客觀公正,所以,為提高公共事件調查的公信力,適時引入第三方進行調查勢在必行,同時也應該加強立法和司法部門的監督,而不是由當事部門自己來進行調查。這種自我調查既難以服眾,也難逃推卸責任之嫌。例如,在上海曝出釣魚執法丑聞后,浦東新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作為當事部門,就矢口否認存在釣魚執法。遭到公眾質疑后,浦東新區隨后重新組織聯合調查組,結果證明當事部門的調查明顯違背事實。這個聯合調查組即相當于一個第三方的獨立調查組,其成員包括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還包括律師和媒體記者,從而還原了事實的真相。
西方哲學家史里斯·博克說:“信任是我們必須保護的東西,因為它就像空氣和水源一樣,一旦受損,我們所居住的社會就會土崩瓦解。”如何建立政府公信力,已成為世界性命題。2007年聯合國舉辦的第七屆“政府創新”全球論壇,其主題就是“建立對政府的信任”。對于我們來說,重塑民眾對政府的信任,也是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當下所要面對的問題。政府公信力的拯救主要有賴于政府自身改革,如果寄希望于通過各種社會重大事件推動政府公信力建設,代價是昂貴的,特別是我們不能拿孩子的健康作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