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醫院改革待破冰
楊 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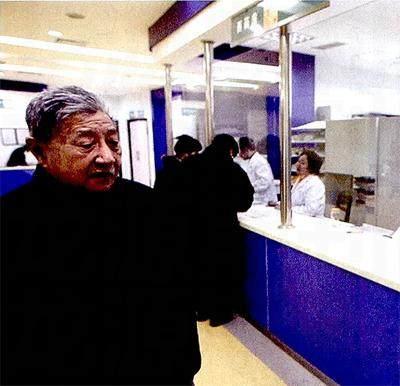

和中國所有有待推進的改革一樣,公立醫院改革難的不是合理方案的制定,而是利益的博弈和平衡。
早在2009年9月初,衛生部部長陳竺在介紹新中國成立60年來衛生事業發展成就發布會上就表示,有關公立醫院改革的文件,正在制定的最后階段,不久就將頒布。按計劃,公立醫院改革方案應該在去年年底前出臺,而在今年1月召開的全國衛生系統工作會議上,各地方衛生廳長也并沒有如預期的一樣等到公立醫院改革的明確思路與方案。各界盼望已久的公立醫院改革方案并沒有如期出臺。一時間,公立醫院改革擱淺的言論甚囂塵上。
雖然公立醫院改革方案出臺推遲被炒得沸沸揚揚,但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樣的結果似在意料之中。
推遲不是擱淺
這次公立醫院改革方案推遲,是因為“一些重大的、基本的問題沒有達成共識”。中國改革進行到現在,很多領域都面臨難以達成共識的困境,不同利益集團博弈激烈,這也是改革難以進一步推進的主要原因,因此,當公立醫院改革同樣陷入這個困境時,悲觀論調自然出現。
在1月12日召開的衛生部新聞發布會上,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否認了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方案擱淺的報道,并稱試點方案已修改完畢、報送國務院審定,一旦國務院審定通過,就可以立即下發執行。但是因為并沒有清晰地解釋人們最關注的問題,即公立醫院改革進程為什么推遲,是否遇到了關鍵性的障礙,到底是什么障礙,也沒有給出試點方案出臺的時間表。鄧海華在公開否認了關于公立醫院改革方案“擱淺”和“推遲”說法的同時,也坦言“這是醫改的一個重點,也是一個難點”。所以輿論依然對公立醫院改革是否擱淺心存疑問。
和中國諸多領域都面臨進一步改革難以推動困境不同的是,新醫改方案是在中國陷入醫改不成功的泥淖4年多之后經過多方博弈和討論才推出的,在新醫改3年規劃的五項任務中,建設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和推進公立醫院試點改革是公認的難點和重點,而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最終確立,有賴于公立醫院改革的推進。基本藥物目錄(擴展版)也將配合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出臺。公立醫院改革的擱淺幾乎意味著新醫改的破產,當醫患關系已經劍拔弩張,百姓對醫療怨聲載道,作為新醫改的核心,公立醫院改革不可能停滯。
其實早在新醫改方案公布之初,已有業內人士斷言,公立醫院改革將非常之難,很可能不會按時間表走,而是有所推遲。國家基本藥物目錄本來計劃和新醫改方案同時推出,但實際上晚出臺了一個半月。因為不管是基本藥物目錄的制定,還是公立醫院改革方案的確立,涉及的利益博弈都無比復雜,平衡各方利益困難重重,推遲應在意料之中。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很快出臺一樣,公立醫院改革方案雖然推遲,但應該也不會太久。因為公立醫院改革試點能否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良性道路,將關系到整體方案何時才能全面推行。
在衛生部公布的《2010年工作要點》中明確提出,今年要推進基本藥物制度實施和開展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等九項重點工作,切實減輕群眾基本用藥費用負擔。衛生部表示,今年是全面推進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關鍵之年。國家推進新醫改的決心可見一斑。
公立醫院改革方案出臺推遲之所以引發諸多猜測,除了公立醫院改革的核心重要地位使人們格外關注之外,另一大原因則是因為公眾對改革缺乏足夠的知情權。據知情人士透露,在新醫改推出之前,有關討論特別是公立醫院改革的討論已經持續有年,但這只是在一個小圈子內,公眾并不知情。從新醫改方案的出臺,到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制定,再到新醫改方案確定,所有新醫改中的關鍵環節,公眾能看到的只能是最終出臺的方案,最多是對草案發表看法,而整個政策制定的過程,遠沒有放在公眾的視野之下。正因為公眾不知道有關公立醫院改革方案到底是如何討論的,有關利益集團到底持何種態度,博弈有多激烈,所以才會對方案出臺的推遲有諸多猜疑。
醫療體制改革和公立醫院改革都是專業性很強的宏大命題,由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和專業人士進行內部斟酌當然是必要的。但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只有以透明和公開的方式進行,并放到全社會的視野下加以權衡,才能保證少走彎路。公立醫院改革遇到困難在意料之中,多方利益博弈可能面臨瓶頸,如果能夠把困難擺上桌面,讓利益博弈曝光在公眾視野中,讓公眾有暢通渠道發表意見,也許輿論壓力會促進各方最終達成共識,解政府不能解之困。實際上,這也是一切公共政策出臺的最佳路線。
不同的嘗試
實際上,盡管中央層面的公立醫院改革方案并未出臺,各地方的醫改方案基本已經到了收尾階段。鄧海華指出,公立醫院改革的原則,一是要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質。二是公立醫院必須納入衛生行政部門的統一監管。三是要正確理解和實踐管辦分開的原則。全國大都已經進人公立醫院改革的實施階段,各地根據自己的不同理解和當地的實際情況,選擇了認為適合自己的不同改革方案。
一些地方成立了醫管局,醫管局和衛生局彼此獨立,業務上前者負責醫院的人財物管理,而后者只從宏觀政策上予以調控。當出現社會性公共衛生問題時,衛生局代表政府向醫管局“采購”醫療服務。從而真正保證公立醫院管辦分離的實現。管辦分離也是新醫改的要求。目前有不少地方實行了這種辦法。其中成都和上海類似組織歸屬地方國資委,而北京醫管局歸屬北京衛生局,比后者低半級。一些城市為此專門成立了獨立的事業單位。
但在一些地方,對于醫管局的出現,當地醫院似乎并不十分歡迎。認為是“又多了一個管事的婆婆”。而很大程度上,不管是成立醫管局,還是成立獨立的事業單位,都變相擴張了政府規模,這和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方向相悖,如不是必須,實無必要。有些地方可能確實適合這種模式,但不排除一些地方不過是借機增加編制,安置富余人員。據專家介紹,“醫管局模式”出自香港,但香港的公立醫院完全由政府埋單,而內地的公立醫院是需要通過競爭來爭取醫保“付賬”的。
新醫改方案中說:“積極探索政事分開、管辦分開的多種實現形式”,“落實公立醫院獨立法人地位”,“建立和完善醫院法人治理結構”。這些被抽出來的話語合在一起,被一些地方解讀為公立醫院法人化,因而便有了類似于國企改革的公立醫院改革措施。而這顯然并不完全正確。鄧海華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公立醫院的資產不是經營性資產,所以公立醫院不是國有企業。不能照搬、照抄國有企業改革的做法來進行公立醫院的改革。”改革開放30多年的經驗表明,不能照搬、照抄國有企業改革的做法來進行公立醫院的改革,這樣才能避免進一步削弱公立醫院的公益性。雖然在一些地區“醫管局”的設置級別、名稱各不相同,但這并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它代表誰來管理醫院。倘若歸屬國資委,
就意味著接下來很可能按照國企改革的路子走。醫管局建立后,各個院長職權大大增強,有獨立的人事權和財務權,會實行法人責任制,給醫院定目標,定任務,和國有企業法人有點類似。
支持民營資本參與公立醫院改制是另一些地方的選擇,一些地方出臺了允許民間資本入股等一系列措施。廣東省就比較支持民營資本參與公立醫療機構改制,并于日前出臺了《關于加快廣東省民營醫療機構發展的意見》。但不同的是,廣東省計劃將部分公立醫院轉制為民營醫療機構,鼓勵社會資本以收購、兼并、托管等形式,參與公立醫療機構的轉制重組。
還有些地方實行委托大醫院管理中小醫院的模式等等。各地實行的公立醫院改革模式千差萬別。
各地實際情況不同,難以實行統一政策,大可以分類改革。中央層面沒必要出臺具體的實施細則,但大的框架還是要盡快出臺,雖然早已明確公立醫院改革“首先要堅持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質”,保障百姓利益,保證醫療公益性,但在中國現實環境下,缺少明確的方案指導,各地難免各自為政,以至有些地方為了小集團利益或對醫改解讀失誤而走入改革歧途。
補償機制不容回避
和中國所有有待推進的改革一樣,公立醫院改革難的不是合理方案的制定,而是利益的博弈和平衡。公立醫院改革的最大目的是要實現其公益性,核心問題是解決財政補貼來源。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全國不同地區的公立醫院復雜的權屬關系以及隨之而來的補償機制不到位,是令“方案”不得不向后延期的主要原因。各級各類醫院由誰來補償,補償能否到位,補償方案能否促進醫療資源的最大效率發揮,都可能成為各方爭論的關鍵。
這些年中國醫療市場化的結果是,政府對公立醫院投入少,政府投入只占公立醫院成本的8%,大型三甲醫院可能只占6%。只夠發醫院的退休金。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建立和藥品“三統一”的實行,使公立醫院藥品利潤加成被大幅壓縮,一些醫院因為成本控制不好,甚至虧本,公立醫院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如果不允許醫院像以前那樣通過經營性運營賺取利潤,那么必須由政府財政補上醫院的財政窟窿。
醫療轉向公益,首先是對政府財政的沖擊。當時中國把醫療推向市場,正是因為政府財力不足。雖然現在中國財政已經比較充裕,但各項改革的推進都需要大筆的財政支出,金球經濟中中國為了應對危機而采用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也使財政緊張。當醫療轉向公益,所有的醫療支出都需要政府埋單。這就意味著不得不放棄大量可供選擇的經營性策略,同時也意味著持久而高昂的財政支出。在現行財政體系下,維持一個龐大的公益性醫療機構,實際上意味著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責任的重新分配。不同財政層級在醫療問題上所擔負的支出、所承擔的責任到底如何界定,是個難題。對北京、上海、浙江等大城市和富裕省份來說,這筆錢不成問題,剛剛出臺的《深圳市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稱,深圳醫改3年將投人近196億元。但對中西部一些地方來說,這會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部屬醫院中央財政出的錢比較多,市屬和區屬可能是同級財政出大頭。地級市的醫院根本拿不到充足的財政投入,怎么辦,只能自己想辦法,那就又回到了當初醫療市場化的老路。有專家認為地方不存在財政不足的問題,只是看把錢花在什么地方。問題是,如果把錢都花在醫療改革上,其它領域的改革怎么辦?對一些相對落后的地方來說,財力不足絕對是補償難以到位的原因之一。在這些地方,如果政府補貼始終不能明確,地方政府只有自謀出路,一些地方政府醫院的公益性將難以得到保證,甚至被迫再次走上市場化的道路。
補償機制是必須的,既然如此,那么晚出臺不如早出臺。
當然,補償到位了,也并不就能完全保證公立醫院的公立性,補償的問題,還和制度與模式有關。如果不在擴大醫療保障覆蓋面的同時改革扭曲的醫院運行機制,再多的投入都有可能被醫院吞掉。雖然財政投入是改革的核心問題,但并不是維持醫院公益性的唯一方式。許多公益行為不需要額外成本,如不濫用專業特權、合理檢查、合理用藥等。
醫改專家、北大教授李玲認為,對于醫療保障制度而言,提高覆蓋面和覆蓋水平要靠制度建設,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則要靠公立醫院的改革,否則保險方和醫院會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斷博弈,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得到最佳利用,甚至形成保障水平越高、資金浪費越嚴重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