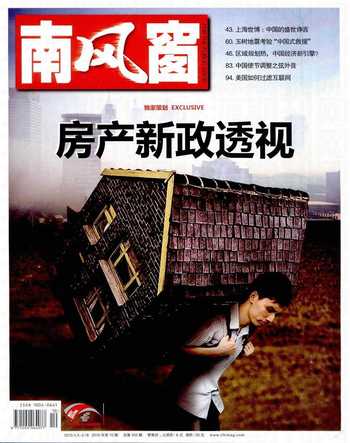政府轉型,迫在眉睫
趙 義
一方面。沉重的吃飯財政,日益增加的剛性支出,追求GDP的職能沖動,最終使得部分土地和房屋變成瘋狂運轉的財政抽水機。另一方面,圍繞房地產行業的幾乎每一個角落,腐敗空間都被充分挖掘。中央政府也不得不祭出對高房價遏制的行政問責的大旗。
和任何轉型中國所面臨的尖銳的社會經濟問題一樣,高房價問題已經走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反復治理下總是出現反彈;背后的利益結構已經相當固化;民怨已經積累到一個相當危險的階段。其中,中央政府扮演的是道義上和民眾站在一起的角色,而地方政府的角色卻是負面和復雜的。在高房價中,地方政府普遍被認為是和房地產商捆綁在一起的利益共同體。而隨著公務員福利房問題、保障性住房落入富人手中、限價房被官員拿來倒賣等現象被廣泛曝光,人們對于高房價的怨憤已經更多的和對政府的不信任聯系在了一起。
可以說,高房價問題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社會層面,都成了一個亟待突破的瓶頸。正如著名的政治學者鄭永年所說:在中國,房地產被視為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而非社會政策的一部分。把房地產視為單純的經濟政策領域,其CDP功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被凸現出來,而其社會功能(社會成員對住房需求和人們的“空間權”)就被忽視。遏制高房價是要預防日益顯化的危機,而實現每一個國民的居住權則是中國房地產新政最終要實現的目標。
遏制高房價,可以用很多即時能采取的政策,比如用信貸政策打擊炒房。要實現最終目標,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進程就必須加快。從房地產行業來看,影響地方政府轉型的重要因素包括土地財政和官員腐敗等。如果無法從體制機制上鏟除地方政府對于高房價的依賴和腐敗利益鏈條的再生產,房價反彈的可能性就不會消失。而即使房地產行業真走到無法持續的地步,只要地方政府對于預算外收入的依賴不減,腐敗利益鏈條的再生產能力依然存在,地方政府總要尋找另外的出路。那個時候,另一個社會經濟問題將和房地產一樣,進入一個發酵、積累和爆發的新周期。
日益多的剛性支出
在記者以往的采訪中,一些地方官員對于高房價是這么看的:我們也知道房地產業不可持續,但沒有辦法。第一個問題就是吃飯財政。
“吃飯財政”是指預算內收入只能用來發工資,沒有財力做別的事情。對于“吃飯財政”的批判,讓人印象最深的是前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1998年記者招待會上談到機構改革和科教興國時的話:“科教興國是本屆政府最大的任務……但是我們因為沒有資金,貫徹得不好。錢到哪里去了呢?政府機關龐大,‘吃飯財政,把錢都吃光了。”
以往人們常用“吃飯財政”來形容縣鄉財政。比如發改委的報告說,全國平均每個縣的赤字約1億元,全國赤字縣占全國縣域的比重達3/4,縣級財政基本上是“吃飯財政”,縣鄉政府的債務風險仍未得到根本性控制。或者是指中西部特別是基層的財政。比如2010年全國“兩會”來自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大代表就說:少數民族地區的財政仍是“吃飯財政”,還是在國家加大了財政轉移支付力度的情況下,運轉才基本保證正常。到今天,雖然政府改革進行過多次,但“吃飯財政”已經是無論發達還是不發達地區的一個普遍性問題:預算內收入的分成只是用來維持政府運行。
吃飯財政的繼續和成型,說明中國的政府機構改革一直沒有解決人員日益臃腫的問題。相反,隨著公務員金飯碗的持續走俏,吃飯財政日益固化。比如黨政機關自身開支占公共財政開支的比例,官方的說法是19%,智囊機構給中央政府回報的數字是25%,而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對外披露的是37%。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說,我國的機構臃腫和人員膨脹在某種程度上講已到了極限,財政成為“吃飯型”的財政,財政再分配的其他職能大受制約。“吃飯財政”衍生了大量的社會政治問題,包括費多如牛毛,從土地等方面挖掘預算外收入,重新國有化等。對于很多地方來說。吃飯靠財政,建設靠國土,已經是一個普遍現象。吃飯財政已經固化,其他收入渠道日益膨脹。而就在吃飯財政日益固化,矛盾日益凸顯的時候,另一種剛性的財政模式也在成型,就是維穩財政。維穩,常常是一票否決的事項甚多,官員不敢怠慢。中國社會科學院于建嶸教授認為,維穩財政支出越來越大,已經影響經濟社會發展。盡管目前還沒有權威的全國維穩成本統計,但僅就部分地區的情況來看,維穩支出每年以兩位數增長,維穩經費相當于甚至超過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為普遍現象。據公開的信息,某副省級市2007年社會維穩支出44億元,比社會保障就業資金35,2億元還要多出許多。并且很多時候一些維穩經費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額外支出,比如攔截一個上訪群眾的花費。增加的財政支出并不由官員個人承擔,而是由納稅人來埋單。
吃飯財政和維穩財政的日益固化,將可能決定政府從社會過度汲取財富的進程不會減緩,而這一點將更加重中國社會的矛盾和危機。比如釣魚執法,拆遷自焚,圈占耕地導致農民上訪等。在吃飯財政艱難向公共財政轉變過程中,日益增多的剛性支出將加重其轉變困難。
另外,土地之于地方政府,除了再杠桿化功能(貸款)外,實際上也是在以地養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劉守英曾經介紹說,地方政府供應的土地也不都是一本萬利的。政府征地的30%左右要劃出去用作基礎設施等公共用途,另外30%左右是工業協議用地,這部分政府要搞幾通幾平,對企業基本是成本供應;剩下的30%左右才是真正的房地產用地,但是其中一半是保障性用地。他認為,地方政府實際上是在用15%~20%招拍掛的土地出讓收入去養另外80%不掙錢的供地,結果必然加大房地產用地的稀缺性,成為助推高房價的原因之一。
沉重的吃飯財政,日益增加的剛性支出,追求GDP的職能沖動,最終使得部分土地和房屋變成瘋狂運轉的財政抽水機。人們現在討論物業稅等問題,在目前的政府支出框架下,新稅種的出臺似乎不能代替這種抽水機。因為,正如經濟學家周黎安所說,中國經濟當中軟預算約束問題的主體已經主要不是企業,而是各級地方政府和準行政組織。政府總會感到“錢不夠花”。責任向下、財力向上之后,弱勢的一方一定會祭出“債務向上”的武器。
腐敗鏈條
這些年,栽在房屋、土地、規劃上的腐敗官員層出不窮。可以說,圍繞高房價“泡沫”已經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腐敗利益鏈條。
就以土地出讓為例。據王煉利《無辜的地價》一文介紹,1995年上海待開發土地面積是6521.7萬平方米。1996年到2008年上海房地產商總共購置了7900萬平方米,而完成開發的土地為4200萬平方米。所以,待開發和正在開發的土地面積和是10721.7萬平方米。不過,2007年和2008年的所謂高價土地,最多只占總面積的4.6%。也就是說,在政府出讓的95.4%的“便宜土地”上造出的房子和最初的地價無關。房地產商的主要得益之處在于炒賣土地包括炒賣土地上的附著物——令無數人心碎的房產。
在土地出讓中,巨大的利潤空間逐漸衍生出兩種交易——公開的土地交易和桌底下的交易。上海市房屋土地資源管理局原副局長殷國元為主的腐敗窩案的爆發絕不是偶然的。
而具體到房屋,公務員炒房已經是一個屢禁不止的現象。最近一段時間,農業部被曝分800套限價房、深圳部分公務員被曝住豪宅騙取保障房、山西忻州市公務員倒賣限價房等無一不是新聞熱點事件。如果說公務員炒房還只是龐大的投機性需求的一部分,公務員福利房涉及不同群體的不同的住房制度問題,倒賣限價房和騙取保障房等做法就是名目張膽的“化公為私”。
更重要的是,這些現象說明,圍繞房地產行業的幾乎每—個角落。腐敗空間都被充分挖掘。近些年曝光的腐敗案件,悄然間,有多少房產已經是一個日益頻繁出現的字眼。在地方財政嚴重依賴土地的情況下,部分官員的腐敗使得其背后的利益鏈條更難撼動。中央政府也不得不祭出對高房價遏制的行政問責的大旗。對于“內外交困”的行政首長們來說,頭頂上的“烏紗帽”是沖破各種阻力的最強大的動力之一。
一個引人注目的消息是,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主題之一就是審議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于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進一步完善了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明確規定領導干部必須報告本人婚姻變化及配偶和子女移居國(境)外、從業等事項,本人有關收入事項,本人及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房產、投資等事項,細化了報告程序,使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制度更加全面、更具有針對性。
會議認為,這個規定是促進領導干部和國家工作人員廉潔自律、回應社會關切的重要舉措和制度創新。的確,官員的房產問題現在已經是一個中央政府不能不給予社會明確回應的敏感問題。當然:人們期望除了這種內部申報之外,還會有更多的有用的制度來約束官員的腐敗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