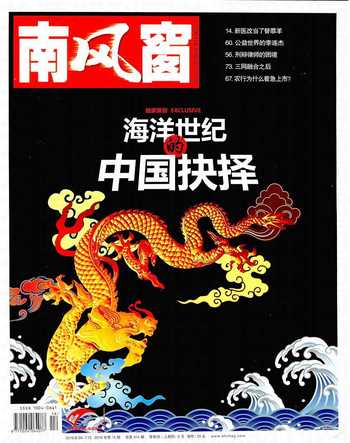人力資源大國的起跳短板
章劍鋒

我們國家現在非常困惑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整個經濟模式發展轉型過程中,一個是勞動者素質不高,一個是高技能型人才嚴重缺乏,還不是一般性的缺乏。而沒有高素質勞動者、沒有一大批應用型和技能型的人才,不能算是人力資源強國。
中國政府正在嘗試進行經濟增長結構與增長方式的雙重轉變,這在經濟危機之后尤其明顯。但在這種轉變過程中,如何確保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力能夠順利轉崗而不失去就業能力與機會,也是一個不得不去面對的問題。為此,官方提出了一種新的平衡辦法——大力提倡職業教育。
關于這一點,5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里已經寫得明明白白,“發展職業教育是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就業、改善民生、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緩解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關鍵環節,必須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問題是,遠水是否解得了近渴?對于這樣一項荒疏多年的教育事業而言,要想使之瞬間即可為我們這個人力資源大國“排憂解難”,這似乎并不像“霍格沃茨魔法學院”里的教授們舉舉魔法棒那么輕而易舉。陶西平是國家教育督導團現任7位省部級總督學顧問之一,他讓我們意識到,重振職業教育遠比想象中要復雜。
職業教育與人力資源強國
《南風窗》:職業教育就是就業教育,對此您作何評價?這種提法,是不是有一些功利化了?
陶西平:從2003年到現在,應該講是越來越強調這一點。解決就業問題當然是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任務,所以有人提出來說職業教育就是就業教育,這是對的。職業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兩個,一是解決從業人員的就業問題;一是解決從業人員就業以后的繼續發展和提高問題。因此職業教育最主要的一個是人格的培養,一個是能力的培養。我不想提功利化,但說實話,如果都就不了業,都鬧起來成了一個社會大問題,也沒有辦法。
《南風窗》:怎么理解職業教育與解決就業問題的關系?許許多多的勞動力接受了職業教育以后,就一定能就得了業嗎?
陶西平:從現在來看,整個職業教育方針是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就有一個怎么理解“服務”和怎么理解“就業”的問題。目前存在的偏向是,更多地關注了就業,而且更多地是一次性就業。如果只是拿一次性就業率到底有多少來評價一個學校,就容易忽視學生實際素質的提高,而是比較重視學生一進來就想辦法給他找出路,聯系什么地方能要他,只要能要他就完了,甚至于就出現一些所謂的“被就業”現象。要想提高就業率,根本是要提高學生的就業力,提高學生的人格培養和能力培養。
《南風窗》:我們知道現在經濟增長方式與結構的調整還沒有起色,職業教育在這方面能起什么作用?如果職業教育短時間內不能適應和跟上這種調整步伐,后果是什么?
陶西平: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依靠職業教育;勞動力整體素質的提高和專門技能人才的培養,需要職業教育;廣大勞動者就業問題的解決,需要職業教育。其實我們國家現在非常困惑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整個經濟模式發展轉型過程中,一個是勞動者素質不高,一個是高技能型人才嚴重缺乏,還不是一般性的缺乏。現在找一個工程師容易,找一個高級技師很難,特別是在有的領域里面,是更難的。在這些方面,近幾年政府越來越重視職業教育的發展,應該講職業教育會有一個恢復性發展。
經濟結構調整對于職業教育來說,既是一個動力,也是一個考驗,特別是我們新的經濟發展方式又要是綠色的、低碳的。這個就業形勢,我估計會越來越嚴峻,因為現在農民工進城以后,一個是就業崗位減少,一個是轉崗問題。如果不接受培訓,再加上一些職業的要求越來越高,他轉不了崗。
《南風窗》:就此而言,職業教育是整個經濟轉型成敗的關鍵?
陶西平:應該講,我們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使得更多人有了就業機會,特別是農民工。現在要使他們再轉化成具有較高素質的勞動力,職業教育起著很關鍵的作用。
我們現在要從一個人力資源大國向一個人力資源強國轉變。到底什么是人力資源強國,我覺得就是要有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這個專門人才里面,相當一部分是應用型和技能型的人才,然后還得有一大批拔尖創新人才。沒有高素質的創新人才,也就出不來大師,我們不能算強國。但是只有大師,沒有高素質勞動者、沒有一大批應用型和技能型的人才,同樣也不能算是人力資源強國。而高素質的勞動者和專門人才的培養,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職教解決。只是以普通教育為主體,我們很難成為一個人力資源強國。
要優化教育結構
《南風窗》:職業教育現在面臨的情況還是比較尷尬的。在整個教育結構的比重中,有點受到冷遇的意味。
陶西平:前幾年我就提到,要維護職業教育的尊嚴。我們現在對于整個職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認識還是很差的。他們的社會地位相對是比較低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的觀念,我們把學術型人才和管理人才說成是白領,把技能型人才說成藍領,然后就覺得后者層次要低一些。另外,以學歷為本的人才任用制度,也制約了所謂藍領技能型人才的地位。
我們的職業教育體制,在一段兒時間里面又是一種“斷頭體制”,就是職業教育分成初等、中等和高等,而最高層次在大專就完成了。而現在很多地方規定了,如果要升處長,必須具有本科學歷,那等于說,如果走職業教育這條路的話,畢業了這一輩子也不要想當處長,因為還不具備這個學歷。
《南風窗》:一開始并不是這個樣子的吧?
陶西平:也是有一個起伏的。建國后一段時間,中等專業學校是很受重視的,培養出來的人才被當作寶貝來用的。90年代中后期以前中等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也跟我們重視它有關系。高校擴招后,帶動了普通高中的擴招,中等職業教育就變成了高中階段教育的一個補充。一直到2003年以后,中央才開了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重新提出來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來加快職業教育的發展。
《南風窗》:照這么說,職業教育是被學歷教育擠出了。
陶西平:我感覺我們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的職業教育體系,在兩次分流(小學和初中)過程當中,把一部分沒有接受普教能力的人分流到職教中來了。我曾經在北京市做過8年教育局長,進行過一項改革:第一志愿你也可以報普高或中職,然后同時進場錄取。我覺得最可怕的不是社會上看不起職業教育,而是教育部門自身看不起職業教育,這是最大的問題,實際上現在存在著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自身就把職業教育看成是二等教育,這是對技能型人才的價值的一種低估,缺乏真正的認識。
技能型人才的培養方式,自身應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教育體系。我們的中等職教和高等職教雖然是銜接的,但是高等
職教還要解決普通高中的升學問題,甚至于首先解決普通高中的升學問題,然后再解決中等職業教育的升學問題,所以我們教育部原來的一些領導同志就講,中等職校畢業生主要就是直接就業,不要升高等職校。這都是他們內心潛在的一種對于職業教育不重視的反應。
《南風窗》:這種情況有沒有好轉可能,連國務院的綱要里面都單列了職業教育一章?
陶西平:應該說是一個好的開端,但要使職業教育真正發展起來,還是要做很多努力,實行免費教育和補貼,會起重要影響,但不會起決定性作用。必須優化教育結構,現在的主要問題就是并沒有形成一個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并重、并舉的局面。簡單地規定接受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構成比例,可能也是在一個特定階段為了推動職業教育發展所采取的措施。所以應該重視政策引導跟輿論引導,我們政策的每一點調整,實際上都有助于職業教育地位的提高。
因需而變
《南風窗》:中國的職業教育供給與市場需求的脫節到底有多嚴重?
陶西平:由于投入不夠,我們的職業學校對于一部分不需要多少設施、設備的所謂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專業設置比較多,而特別需要的那些技能型人才的培養,由于設備、設施不夠,專業設置是比較少的。比如財會、法律、外語,這部分專業開得很多,現在就業也比較難,因為不需要那么多人。
我們通常評價一個創新國家,用的是創新綜合指數,一個是科技貢獻率比較高,一個是研發投入應該比較高,一個是對外的技術依賴率應該比較低。大概是這么三個要求。從我們現在來看,還沒有真正進入創新型國家的前列,至少前20名我們進不去,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的技能水平不夠作為一個創新型的國家。現在大家都覺得,德國的創新能力非常強。德國掌握的很多東西關鍵技術不給我們,有很多技術問題我們解決不了,所以我們的汽車工業雖然很發達,但是我們的對外依存度非常高。創新型人才的技能培養,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大差距。
《南風窗》:培養方式上面是不是也存在問題?
陶西平:德國的國家法律規定企業必須承擔培養技能人才的責任,費用由企業出,工資由企業出,等到學員畢業了,到哪里工作由學員自己決定。這是一種企業責任。在美國和澳大利亞,企業在職業教育方面也承擔著重要責任,校、企之間的一體化合作是非常明顯的。有的學校把他的實訓地放在了企業里面,有的企業是把一部分車間辦在學校里面。
我們經歷了一個周折,當國有企業改革的時候,提出要把與企業發展無關的社會職能剝離,在剝離過程中就把基礎教育、把職業教育也剝離出來了。本來一些學校是由行業、企業辦的,剝離出來后,行業和企業反過來再從社會上招人,這些人不再是他們自己培養的。這樣一看,好像是減輕了企業負擔,實際上是降低了勞動者的素質和適應性。
《南風窗》:中國有民辦教育,民辦教育在職業教育領域可不可以發揮一番?
陶西平:民辦教育在職業教育領域能發揮最大的作用,他們的限制比較少,不在教育部門注冊,一般是在工商部門注冊,市場適應能力比較快。比如北京有一所職業學院,就是以休閑體育作為專業,比如高爾夫的球場管理,汽車比賽服務管理,如果在普通高校里面要設這個專業,是要有很多道審批程序的,這所學院看準市場,馬上就可以設置專業,一招生就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