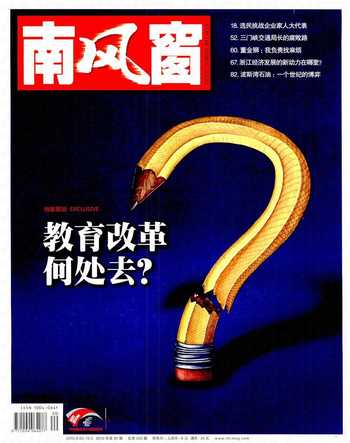關于村委會的立法爭論
仝志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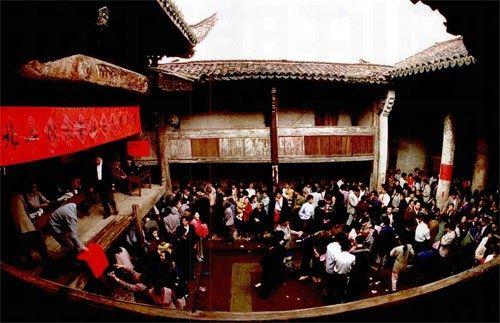
2009年12月和2010年6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訂草案》,草案還公開向社會征集意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審議本來是有關村民委員會設立和內部管理的一部法律,但是,由于草案充實了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事項。“拔出蘿卜帶出泥”,委員們進一步的爭論是否要將村民委員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不同主體性質和相應的管理職責明確分開。在已經公開的常委會成員意見中,壓倒性的意見是要分開。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經研究認為,這個問題涉及的情況比較復雜,各地做法也有差異,擬在進一步調研的基礎上提出意見。有的委員將其理解為“在此次修訂草案中對此問題存而不決了”。
委員們提出在法律上明確村民委員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不同性質,甚至要界定兩者關系,起因于在現實中要明確集體資產管理的主體是誰。在10月份可能的17次常委會三審中,這仍將是一大焦點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全國近60萬個村莊的村級組織制度設計,對于相當比例的村莊中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現實權益將直接帶來影響。對于一項事關農村基層治理、村民自治和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重要法律,靠兩次常委會會議上各半天的審議,也很難討論出一個周全的意見。此時,對此問題細致、深入的討論應該成為必須。
對多數村莊而言,維持現有規定并無問題
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和村民委員會的成員邊界和管理內容是如何出現差別的?搞清楚這一點,也就搞清楚了人大常委會上明確兩者區別的辯論日益激烈的原因。
1986年的爭議是主要出于對組織性質問題的辨清而起。因為那時的村委會對全國絕大多數村莊而言是一個擬議成立的組織,因此,需要把它和已經存在的“集體經濟組織”辨清關系。1998年九屆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村組法時,對爭議做出維持試行法規定則是因為實踐中問題暴露還不很激烈。1998年11月,民政部有關官員在《中國社會報》發文《村委會組織法修訂中的四大爭論》,將“村委會是否應當有管理集體經濟的職能”作為四大爭論之一。當時的情況是,“在這個問題上,絕大多數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為村委會應當有管理集體經濟的職能。”因此,當時通過的法律只對試行法中的個別用詞進行了修訂,沿用了試行法“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這一規定。
現在的情況則是,村委會在全國絕大多數村莊已經建立,但已經有40%的村莊中單設了集體經濟組織,60%的村莊則是村集體經濟組織與村委會“合二為一”,“合二為一”的村實際上并無集體經濟組織更多的經營管理活動,除了土地發包以外沒有其它集體經濟組織活動。集體經濟組織在60%村莊中已經“名存實亡”。
在60%的村莊中,土地承包、宅基地分配這樣的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活動由村委會代為行使,并不會產生多少問題。因為,以往存在的村干部多留機動地、任意調整土地、專權分配宅基地、侵吞承包費和宅基地使用費的問題在村民自治制度下也是不容許的,如果貫徹村委會組織法中有關由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決策和監督的程序規定,就不會出問題。而且,土地承包和宅基地分配作為與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每家每戶都有關的更強調公平和公正的事務,也是適用于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這樣的民主規則的。
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的性質區別和職能劃分問題,更多是在40%的村莊中才成為問題的。也就是說,只有在本村村民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差異較大,或者在工商業活動發達的集體經濟組織中,才有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分設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組織的必要。
這樣的村莊在今天中國的村莊中,畢竟還是少數。因此,拿一種并不多見的情況來要求做法律修改,第二次提交審議稿未作回應也在情理之中。
“無風不起浪”
村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委員會在管理集體財產上是否需要明確權力性質、歸屬和產生方式的問題,主要出在以下兩個場合:一是集體所有的工商業資產發達,管理活動變得復雜;二是集體土地因為城市化帶來升值和新農村建設對于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而使得可分配收益數量巨大,如何分配收益變得復雜。
在以從事工商業為主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由于事實上屬于村莊集體組織成員的既得利益巨大,產生了僅僅只是擁有本村戶口但不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有無分享資格的問題。由于村莊工商業發達,擁有本村戶口的村民的數量多數情況下就會大于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數量,多出的村民可能是長年在村里打工或經商的人,或是來村莊中買房置業的人。工商業發達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會進行明確的股份合作制改造或者通過村規民約,規定集體經濟組織收益的分享資格和比例。擁有分享資格的村民即為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有擁有本村戶口的村民,在現行法律規定中是村民自治組織的成員,但是,其中有些則不被村集體經濟組織接納為成員。
這個時候,村莊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成員不相重合,兩者的職能自然也就有所區別。自然的,村民選舉的村委會就會被“剝奪”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的權力。而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者則可以由黨支部書記充任,或由黨支部任命,或者聘任本村經濟能人擔任,甚至可以通過人力資源市場從村外招聘,而并不必然走選舉程序。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者的管理方式也就脫離所謂民主管理,而變成更加符合市場經營要求的企業管理方式。應該說,集體經濟組織的民主管理不一定就沿用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和監督制度,而是需要符合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活動的民主參與方式。在這個場合下,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者的經營不善、中飽私囊等問題,則要通過建立合理的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制度,而不能追問村民自治制度的失當。
在這種場合中,集體經濟組織是否和村委會分別明確職責,多半是一個在實踐中已經解決的問題。因為工商業活動的復雜和經營決策的特點,使得村民自治的民主和直接參與原則并不適用,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了更好地參與市場活動,多數都會明確成為工商業法人,為了內部管理,也會建立不依賴于村民直選制度的集體所有者組織(如董事會或理事會)和經營者團隊。
當下,隨著資本下鄉步伐的加快,如何協調外來資本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利益,如何進一步規范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者的權力,如何界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格和權利,正在農地流轉、開發區占地、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等多個領域對立法提出迫切要求。但是,這是一個不同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另一部法律的立法。
另外,涉及集體經濟組織產權改革、村改居等更為根本的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重大事項,現有的村民自治決策和執行程序是否能解決問題呢?這類事項,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之類的組織決策制度,則不一定能保證村民的長遠利益。這類事
項影響到村民幾代人、同時對全社會利益也會產生重要的外部性影響。因此,并不能完全由村民自治原則來解決。中央和地方政府完全有必要通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經營管理條例》之類的法律來進行規范,而改變當前由地方政府單方面制定臨時政策,或者利用村民多數人決定的投票程序來決定。
關于農地收益的沖突類型
土地是中國農村中更多出現沖突的場合,也是最需要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村民自治組織中村民身份的場合。由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招商引資或者國家規劃的交通設施和重大產業項目,在城鄉結合部的村莊中需要大量征收土地,或者一些農業產業化企業或項目下鄉,有關村莊會發生農地的大規模流轉,這都會產生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其中相當部分被以征地補償、土地流轉租金的形式歸屬集體土地所有者。這時,誰是集體土地所有者也即誰是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就不僅需要明確界定而且必須有合理“說法”。
這時的成員資格不僅僅是一個有無農地承包權的問題(農地承包權帶來的僅是微薄的農地收入和社會保障,有成員資格就有可能得到征地補償費和流轉租金),而是一筆相比高于若干年農地種植收入好多倍的貨幣收入,有些地方還附帶著社會保障、就業安置等長遠福利。在中國的很多村莊中。正是由于誰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無法定論而造成了曠日持久的爭吵、訴訟和上訪,而由于缺乏村莊內部的共識形成和裁決機制,使得這些爭吵、訴訟和上訪成為矛盾沖突的導火索。
這些涉及農地轉非農用的增值收益分配而致的集體成員資格爭議和沖突發生在以下幾類主體之間:
第一類,承包地被征用的農戶與承包地未被征用的農戶之間。失地農民要求把有關征收補償全數歸自己所有,但是同為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要求分享征收補償,理由是我也是集體土地的所有者。現有法律和政策并不明確支持失地農民的要求,因為被征用土地的是村集體經濟組織,而不是某些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經濟組織的全體成員有權通過某種集體決策程序決定征收補償在成員間的分配范圍和數量。
第二類是承包地被流轉的農戶與承包地未被流轉的農戶之間的沖突。現有法律支持承包地被流轉的農戶獲得全部流轉收益,因為流轉的是基于農戶承包權的農地使用權。但是,共居一地、同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沒有被流轉的農戶則沒有機會享有流轉收益。當這種流轉是所謂大規模流轉,并不與自己地里種什么和土地質量有關,而只與偶然的土地位置有關時,后者的意見將會更大。往往這種大規模流轉又要依靠村干部乃至鄉干部做很多工作,這就更增加了后者有意見的理由。流轉租金低了,土地被流轉農戶要求重新調整土地;流轉租金高了,未被流轉農戶要求分取租金。
第三類是失地農民、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村委會(或村集體經濟組織)、鄉鎮政府以及更高級別政府之間的矛盾。由于征地補償標準不由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村集體經濟組織決定,土地流轉租金很多時候也不能很好體現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利益。而是依據國家有關法律和地方政策,由地方政府或用地企業單方面決定,農民應得大大低于土地的市場價格,農民會產生嚴重的被剝奪感。這時候,在補償和租金發放中如果不能做到公開、公平和公正,就很容易產生沖突。
以上這三種基于不同主體之間利益差別的矛盾,都提出了要明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并由具有相當合法性的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者按照公開、公平、公正原則分配集體土地收益的問題。
這種情況下,是否需要通過分設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的方式解決可能出現的沖突呢?
如何看待村民自治
從分配土地收益所需要的決策程序和執行程序的性質來講,作為集體土地共有者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每個人都有參與有關分配方案討論和決定的權利,決策活動是關于數量明確的存量收益的分配方式問題,完全可以通過討論、協商或者投票方式來解決,決定的分配方案應由得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授權的管理機構來執行并受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監督。如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和村民自治組織成員基本重合,而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選舉產生的村委會能正常履行職責的話,沒有必要單設集體經濟組織,來處理集體土地的收益分配事宜。也就是說,目前的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小組會議等的運行程序完全可以解決這類問題。
土地收益分配的問題非常具體而復雜。完全失地的農民想擁有全部征地補償但是還想從未失地農民那里得到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平均調整來的土地,而沒有失地農民則想分取土地收益但是不愿把地調給失地農民;縣、鄉政府想截留土地收益彌補財政赤字,村級組織想多留集體公益金用于發展事業,而農民基于經濟利益和對干部的不信任要求將土地收益完全分到戶。而個別村民的很多具體情況使得其提出超出一般村民的特殊要求,另有一些村民(出嫁、戶口空掛、土地轉包等)到底有無資格分享土地收益,這些問題需要得到細致甄別和個別處理。這些矛盾和問題無疑需要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村民通過民主方式來決定,其決定方式已經蘊含在現有的村民自治制度之中,并不因為新設集體經濟組織的管理組織而得到更為妥善的解決。
在現有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中,發揮現有村民自治制度的優勢,則可解決好多數村莊中農地承包和宅基地分配、社會公益事業興建之類涉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之類的事務,而不必另起爐灶。
為什么不能處理好這類事務,絕大多數是因為沒有發揮這一制度優勢的問題。事實上,只要利用好現有的制度渠道,基于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方面的問題的多數就可以得到解決。目前,關于明確村委會和村集體經濟組織不同性質,分設兩者不同的管理組織的提議更多表現的是對村民自治方式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既源于對村民的自治能力的不信任,也源于對選舉出來的村民自治組織的管理者的不信任,或換句話說,對精英為民服務的意愿和能力的普遍不信任。
需要明確的是對于村莊集體經濟組織如何管理的問題,的確不是在《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修改中能夠徹底解決的問題。筆者只是在于提醒人大常委會委員和社會公眾,現有的村民自治的制度資源中仍有巨大空間,村民自治的有關規定完全可以通過充分利用或者稍加調整,用以解決相當部分村莊中的集體資產的處置和管理問題,即使是征地補償和農地流轉這樣較為復雜的事務。
——關注自然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