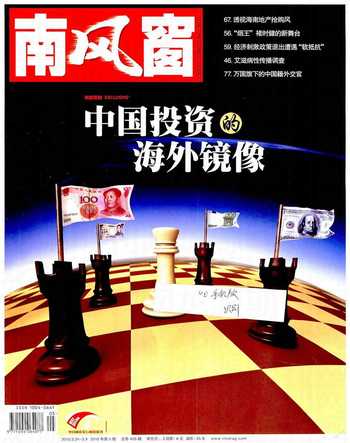萬國旗下的中國籍外交官
趙博淵

若將為聯合國工作的中國人比作一支軍隊,那就是一個將軍,幾個校官,一堆士官和寥寥小兵的失調比例。
1·12海地地震讓創建65年的聯合國遭遇了史上最慘痛的人員傷亡,然而秘書長潘基文宣布的聯合國遇難者名單并不包括在聯海團總部大樓內遇難的4名中國駐海地維和警察,因為后者代表中國,并不屬于聯合國雇員,這就如同中國駐聯合國大使不能算作聯合國編制人員一樣。那么,真正的聯合國工作人員中,有多少是中國人?他們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在聯合國這樣一個特大型國際組織中,除了秘書長和一些機構首腦需公選產生外,中層多為任命,基層的一般人員是聘用。較高級別官員需所在國政府推薦,過程同樣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利益置換和政治博弈,因為無論誰做聯合國秘書長,都需要會員國的選票。而在聯合國大廈里有多少位子可坐,能坐上什么位子,恰恰是一國軟硬實力在國際事務上的體現。
秘書處里的中國人
聯合國內部機構設置,類似于股份制公司的布局:聯大是最高審議機關,相當于股東大會;安全、托管、經濟及社會事務這三個由大國主導的理事會相當于董事會;國際法院相當于監事會;而負責聯合國日常行政事務,并給其他機構提供服務支持的秘書處則相當于經理室,秘書長等于是聯合國的CEO。
聯大一年開一次,托管理事會1994年起事實上就停轉了,安理會和國際法院不常有事發生,經社理事會事務相對多一些,但真正日常性行使權力的只有秘書處。若其他機構暫停,聯合國還能運轉;秘書處一旦停業,聯合國肯定全線歇菜。
為聯合國工作的中國人,多數都集中于紐約總部的秘書處。秘書處的國際職員有1.2萬名,其中來自中國的有約300人,但真正中國籍的只有200余人,余者為海外華人,不乏1971年之前就在職者。港澳臺人士雖是中國人,但用本埠護照,只有在占用中國名額時才在聯合國工作期間換用中國護照。這些非大陸人士卻多擔任較高級別或專業性職位。大陸職員只要不是借調類,多從事翻譯工作,占秘書處100余名中文翻譯的絕大部分,少數擔任各辦公室秘書。
除了這些P級(專業人員)和G級(一般服務性人員)職員,高級(D級)或決策職位上的中國籍官員只有11位,包括1名副秘書長和10名D級官員。由于副秘書長一職五大創始國都能分得至少一個,缺乏可比性,所以真正能體現國家地位和影響的還是D級官員的數量。在這一領域,中國排名第七,落后于美、德、英、法、俄、印度。
與P級和G級職員基本通過公開考試選拔,然后列入后備人才庫“候補”不同,D級官員主要按地域分配,各國享有不等的名額區間。這樣的關鍵性職位共有2700多個,除了朝鮮等國,177個成員國均有權推薦人選。秘書處的考核對于少數高官或中層來說只是一個形式,因為這些人都是由所在國政府推薦,通過借調方式選拔上來的,本質上是政治任命。
由于地域分配的都是關鍵職位,很容易引起國家間扯皮,所以聯合國采取了“多出錢,多占位子”的做法。當然,會費不是想出多少就出多少。聯合國三年一普查,參照該國國民生產總值、人口和支付能力決定其分攤比例,并設22%上限。中國在2007~2009年三年期承擔2.667%的會費,有60余名地域分配人員,今年則升至3.189%。
陌生的中國籍副CEO
D級官員人數眾多,不便詳述,倒是前后7任中國籍副秘書長的履歷值得把玩。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中華民國的胡世澤是曾參與創建聯合國的副秘書長,但只能稱之為第一位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華人了。
新中國第一位聯合國副秘書長是唐明照,1972年至1979年在任。這個廣東人幼年隨家遷居美國舊金山,后來回國在南開讀完高中,之后考入清華大學政治系,與喬冠華、章漢夫、章文晉、齊懷遠等未來新中國的外交骨干成為校友。九·一八事變后,唐明照加入中共,任北平市委組織部長;1933年返美考入加利福尼亞大學,后加入美共,還在美國政府做過翻譯。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肆虐,唐舉家返國,從此成為中國外交部的干將。他既是老黨員,又在美國待過,可謂又紅又專,加上年長,故而成為副秘書長的不二人選。
唐明照在秘書處政治部執掌殖民地和托管地事務,而其后三任中國籍副秘書長——畢季龍(1979至1985年)、謝啟美(1985年至1991年)、冀朝鑄(1991年至1996年)都在技術合作發展部擔任副秘書長。其中,畢季龍、謝啟美都畢業于中央大學,家世都不錯。畢曾在國民政府任職,但1941年加入中共,后帶職赴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深造,朝鮮戰爭爆發后回國加入外交部,先后參加板門店談判、第二次日內瓦會議。謝外交履歷相對簡單,只在瑞士、英國、瑞典和美國外駐過,但其兄乃中共傳奇外交家章漢夫(本名謝啟泰)。謝啟美主管技術部期間,該部一度面臨財政危機。至于冀朝鑄,9歲時因山西淪陷隨父母赴美,1948年考入哈佛化學系,兩年后因朝鮮戰爭回國,在清華學化學,1952年調至朝鮮戰場擔任翻譯,回國后擔任周恩來的翻譯近17年之久,人稱“紅墻第一翻譯”。
第五、第六位中國籍副秘書長,都是在秘書處主管聯合國大會和會議管理部。金永健(1996至2001年在任)北外畢業后人外交部,先后派駐肯尼亞和尼日利亞,后駐聯合國和日內瓦。陳健(2001年至2007年在任)畢業于復旦大學英語系,之后又在北外翻譯班進修,1966年進入外交部,就職于冷衙門國際司。1971年中國重返聯合國后國際司走俏,陳健的外交生涯開始與聯合國聯系在一起,除了依制回國任職和1998年駐日,其余時間都在聯合國度過。
相對來說,中國籍現任副秘書長沙祖康的知名度比幾位前任高得多。沙1970年畢業于南京大學,從駐英使館科員做起,1988年起派駐聯合國,1993年銀河號事件中表現突出,此后成為多邊外交的主力,長期負責軍控事務,2007年被任命為經濟社會事務部副秘書長。
七人七張臉,但大體可以分為兩派——前四位稱作老派,后三位稱作新派。老派多出自家境殷富的上層家庭,有三人在美國接受教育,海外閱歷很豐富,又在政權更迭的亂世經受了政治歷練,其功力不言而喻。而新派的青春歲月是在新中國封閉落后的前30年度過,也打上了那個特殊年代的烙印,相對來講缺乏老派前輩的圓融和練達,這一點在最小字輩的沙祖康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譬如他那毫無邏輯感可言的著名“人權好五倍”言論,雖然不確定是否真如他所言有人鼓掌喝彩,但若有人拿2200萬人口的朝鮮和360萬居民的新加坡作比以示反詰,真不知沙副秘書長該如何作答。當然,用他的話說這叫風格。
雖說都是堂堂地球副CEO,但公眾普遍比較陌生,知名度也是越往前溯越低。這

固然有信息渠道的時代差異性制約,但主要原因有三:首先,聯合同人員的“國際性”模糊了政治屬性,各國新聞報道中聯合國歷來只是較重要的配角。其次是歷史原因,聯合國功能延伸、影響擴大也是冷戰結束后的新現象,而中國在1970年代對聯合國的定位是話語平臺,真正開始重視其功能也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所以宣傳報道長期不足。最后,聯合國機構繁多,平均出鏡率低,公眾視線主要給了秘書長。除非出現全球性熱點問題,相關機構長官才能混個臉熟,譬如朝核、伊核危機就捧紅了巴拉迪。
母國利益和國際主義
在聯合國,“國際職員”須奉行政治中立的國際主義。據聯合國規定,無論原來從事何種工作,過去是官或民,一旦受聘于聯合國秘書處,理論上就成了“世界公民”,須和原籍國“劃清界線”,不能接受任何國家或政府的任何津貼或指令,而要宣誓只效忠于秘書長,只為聯合國效力。政治任命的決策者職位畢竟是少數,占聯合同職員多數的仍是P類和G類,工作以專業主義為第一評判標準。因為勞動合同一年、兩年一簽的居多,考慮到豐厚的薪酬、退休待遇以及榮譽感,本就是層層嚴格選拔上來的職員都會力爭飯碗的長期化,所以絕大多數人都能做到專業至上,政治中立。
理論上如此,現實中多少還是會遇到難以完全拋開政治影響的情況,譬如1980年代初技術部的中蘇籍職員光是同處一室彼此都感到尷尬。在聯合國歷史上還出現過有些職員肩負本國授予的“特殊使命”的事情,至于領取別處津貼的也不乏其人。總之,職員的母國利益與聯合國的國際主義原則總會有磕碰的時候。一般來說,決策者遭遇的幾率更大一些。
無論卸任的還是在任的聯合國中國籍官員,被問及此時,回答似乎都一樣,那就是不偏不倚。倒是前任副秘書長陳健2007年接受央視訪談時說得實在一些:心里會有權衡,但是嘴巴上不能說出來,不能代表中國政府說話。至于如何操作,還要看自身權限和具體情況而定。總之,就算有心維護本國,可操弄空間也不大,而一旦弄巧成拙,就得不償失了。
正因如此,以沙祖康牙舌之利,去了聯合國后也變得安靜多了。
國家力量決定任職情況?
每當提及中國人在聯合國系統的任職情況,外交界人士的回答總是中國特色的一波三折范式:先說成就和進步,認為國家實力上升,國際影響力擴大才有此進步;接著一個“但是”,又開始抱怨中國職員總數和官員數量仍太少;最后總結呈辭,認為隨著國力增強情況將會越來越好。
從大趨勢來說,這個結論是沒有錯的。
如前文所述,地域職位分配是以會員國繳納會費額為準,但這不是全部。只有55%的名額以會費額為準;40%看會籍因素,但這是各國皆享的待遇;最后是5%的人口因素,對中、印這樣的人口大國有利,但微近于無。最初,中國按臺北政權承擔的4%份額繳費,在聯合國普查后方重新修訂,逐年減少,以0.72%觸底后隨著1990年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繳費額又逐年上升,而中國的地域分配名額也經歷了這么個U字形勒跡。
然而,這僅僅是總數目的增長,如果考慮到職位質量,恐怕還會發現有縮水的情況。
首先,按地域分配的D級類職位畢竟是少數,剩下的名額也不全是專業類P級,也有服務類G級,譬如打字員或警衛。服務類職位不由外交官擔任,而在聯合國,英語、法語又是排名前二的工作語言,所以服務類反倒不是中國人的強項。而D類,中國人迄今最高紀錄是同時占有10個職位,剩下的專業類人員大部分又是翻譯,缺乏中堅力量。若將為聯合國工作的中國人比作一支軍隊,那就是一個將軍,幾個校官,一堆士官和寥寥小兵的失調比例。自周恩來時代起,外交部就格外重視翻譯,多數外交官都出自北外,出現翻譯扎堆的局面不足為怪。可是,翻譯本身只能起到一個工具的作用,難成大氣候。何況,這些專業類職員里還有不少非大陸人。這更說明中國在人才培養上的不足。
在聯合國,有不少國家會費額遠低于中國,雖職員人數少,但D類數量仍與中國接近,甚至超過。這其中既有西歐的福利小國,也有非洲的貧窮國家。如果再把在職數超額的22個國家算進去,中國的職位縮水更嚴重。以2009年聯合國數據為準,在D類職位領先中國的六個國家中,俄羅斯和印度的會費額都遠低于中國——俄1.2%,印0.45%,而俄的D類官員高達14人,印度為13人。如此一比,中國相形見絀。
其次,聯合國部門繁多,總會有核心和邊緣、熱門和冷門、實權和虛權之分。就以秘書處下轄各部來說,行政部、政治部、經濟社會部、裁軍部、維和部、人道主義部都是實權部門。1970年代,世界仍存不少殖民地,考慮到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和超脫地位,聯合國任命唐明照管政治部,負責殖民地、托管地事務,這是中國人在聯合國系統獲取過的最核心職位;到了70年代末,殖民地已經寥寥無幾,再加上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缺錢缺技術,于是瞄上了技術合作發展部,中國人連續三任掌管技術部。雖說技術部長期半死不活,但該部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援助對于當時還很落后的中國仍然很有吸引力。進入i990年代中期,中國坐起了冷板凳,金永健、陳健被派去會議部。聯合國會議多,布置會場、打印文件之類的庶務就是會議部的事了,事多而雜,但無實權。會議部如其名,就是一個服務機構,后來在陳健要求下將部門名稱中“服務”字樣刪去,改成“管理”。看上去是牛了,可性質沒變。
2007年沙祖康任職經濟社會部似乎是個良好的開始。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政治任命從來都是和利益置換和政治博弈聯系在一起。潘基文秘書長當年元旦履新,2月就任命沙祖康。潘得以當選,論功勞五常中以中美為甚。論功行賞時政治部給了美國,經社部給了中國。問題是,潘基文是出了名的好好先生,缺乏科菲·安南那樣的能力和手腕。任職三年來,負面評價居多,事實上也沒什么政績,連任怕是無望。一旦如此,中國人是否還能穩坐經社部就兩說了。
最后,國家實力真正能決定的只是少數政治任命的職位,如果中國僅僅將能否坐大辦公室作為評判國家影響力的唯一標準,那么中國的影響力很難提升層次。在聯合國秘書處,職員數超過1000人的成員國有9個,其中只有美、法是發達國家,余者皆是阿富汗、剛果、蘇丹這樣的落后國家。顯然,落后國家按會費額計算的地域分配職位極少,多數人都必須通過考試選拔進入聯合國。相比之下,通過考試進入聯合國的大陸籍中國人只有幾十名,這個數字或許最能客觀反映中國公務員的國際化程度。
在聯合國秘書處,職員數超過1000人的成員國有9個,其中只有美、法是發達國家,余者皆是阿富汗、剛果、蘇丹這樣的落后國家。顯然,落后國家按會費額計算的地域分配職位極少,多數人都必須通過考試選拔進入聯合國。相比之下,通過考試進入聯合國的大陸籍中國人只有幾十名,這個數字或許最能客觀反映中國公務員的國際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