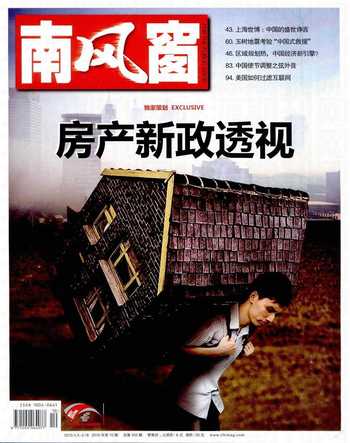股市風暴:“327事件”始末
縹 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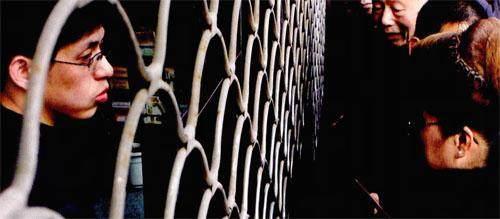
滬深300股指期貨在4月16日正式掛牌交易。重讀“327事件”,對于股指期貨有非常警示意義。股指期貨的系統問題畢竟關系到整個資本市場的安全與穩定。一旦某個合約發生無法交割的情況,一定是雙輸。爭取了那么多年來之不易的股指期貨仍有可能“萬劫不復”,中國資本市場再次發生“倒退”若干年。政府政策首先要看資本市場的玩家是什么態度,反對還是支持;政府層面要有固定的非常匿股票、債券、金融的專家班子,特別是來自機構的專家班子,實戰性的市場意見應該得到政府的尊重。
1995年2月23日,當天上海國債期貨市場發生了驚心動魄的歷史事件。此事對于我國的資本市場,震動之大,堪比美國的“次貸危機”,這就是“327國債期貨事件”。
困獸猶斗
1995年2月23日,是國際期貨市場的一個重要交易日。當時,亞洲貨幣日元大幅震蕩,同內通貨膨脹形勢也很嚴峻,債券市場一度流傳關于財政部對前幾年已發同債加息的消息。
當日上午,財政部提高“327國債”利牢的傳言終于得到證實,財政部發布公告稱,“327國債”將按148.50元兌付。當天開盤,國債期貨市場多頭借此“利好”,率先動用80萬口(期貨交易單位)將前日148.21元的收盤價一舉推高到148.50元;接著又以120萬口推高到149.10元,100萬口再上攻到150元。1分鐘內,漲了2元;10分鐘時,漲3.77元,下午更沖到151.98元。
當時上海交易所共有33家會員,其中北京和其他地方的機構有9家,其他都是上海本地機構,最大的3家分別是萬國證券、申銀證券和海通證券;其中萬國證券公司一家的股票交易總額,占股票交易總額的一半左右。滬市有100多只股票,當天滬市只有13.5億元的成交量。與股市相比,債市盡管低迷,但每天的成交量仍在800億元左右。
以當時“327國債”萬國證券的持倉算,“327國債”每漲1元,萬國證券虧損約為12億元!
收市前的8分鐘,萬國證券忍無可忍,開始反擊。先以50萬口把價位從151.30元壓到150元,然后再把價位壓低148元;最后一筆730萬口,將“327國債期貨”,一直壓低到147.40元,直至收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最后這筆730萬口的賣單,接近中國1994年國民生產總值(GDP)的30%。
當天,其實無論多頭的成交,還是空頭的成交,下單的量,均超過“327國債期貨”的發行規模(按理,國債期貨交易的單筆成交是有限量的,開市初期,一級會員,限2000口;后逐步加至5000口,1萬口,2萬口,平時,萬口以上的單子也很少見)。當時混亂程度可見一斑。國債往事
國債期貨是怎么開始的?上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國債的發行利率,普遍為15%左右,但是發行并不順利。100元面值的國債,發行兩年之后,按理即使存銀行也應該值126元,可當時市場的交易價格卻只有70元。
1992年12月,上海交易所經國務院批準,開通國債期貨和國債回購兩個交易平臺,放開資金入市,由此理順了國債品種的二級市場,這促進了國債價格理性回升。
當時國債期貨的保證金定在2.5%(根據投資實力確定,艋中會有些出入,實際上更低的保證金比率也出現過),實行“會員制”。
1994年,以1992年發行的5年期國債為準,價格幾乎翻了一倍,從78元漲到150多元,到1994年秋天的時候,國債已成為相當熱銷的投資品種。
后來出事的所謂“327品種”,就是特指1992年發行的3年期國債的期貨合約的交易代號;是交易所成立后,第一批國債交易品種。
由于是3年期,所以,應在1995年2月底到期,因為價格低,令實時利率明顯高于基礎利率。
并非“對賭”
現在很多人以為,“327事件”,是中經開與萬國的對賭,中經開開的是多倉,萬國證券開的是空倉,其實這個理解有誤。
當時雙方雖有各自的交易立場,但是區別不大。這要從1994年的通脹說起,1994年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約為36%;CPI(消費價格指數)約為22%;當年銀行的“定期利率+保值補貼”約為14%。
這種情況下,加之股市交易低迷,“327國債”的面值100元,現貨的價格波動區間,非常驚人;對此,損失最大的人,當然是持有國債的一般投資者。
在上交所的會員里,9家外地機構,實力最強的是代表工、農、建席位入市的華夏、南方、國泰;但這3家,由于持有大量的現貨,所以,很少染指國債期貨。
剩下的6家,規模很小,以財政部為背景的中經開是6家里最大的一家;一般人也不太在意中經開的動向,但萬國與中經開不是對手關系,因為他們都是“做市商”。
為了穩定債券現貨,中經開自覺地開通國債現貨,并且主動進行“平準式”的交易,低買高賣,維持價格的穩定。
由于財政部頭寸大,有一段時間,在個別品種上,中經開的交易量,一度接近萬國證券。中經開的操作邏輯是,在低價位“核銷”一部分現貨,財政部會給他一定差值補貼。
與中經開不同,萬國證券是基于中小散戶的立場人市交易的;雙方“角力”的地方,不是做多頭還是做空頭,而是對于國債現貨的利率究竟定位于多少才是合理的利率?
在這一點上,雙方的認識,其實是一致的,彼此均是“做市商”,否則,“327國債期貨”這個品種也不會從初期上市時的70元左右,一路猛漲到“327事件”爆發時的150元。
從根本上說,萬國與中經開,本來就不是對手的關系;也不存在“多空對賭”的必然,因為,如果萬國抬高了債券的實際利率(沽空價格),對誰更有利呢?當然是中經開當時的重要股東之一——國家財政部;同樣,如果中經開壓低了債券的實際利率(拉高價格),對誰更有利呢?當然是持有現貨的老百姓。
問題是出在利率的突然調整上。1995年央行的貨幣政策,是收緊資金,回籠貨幣;市場內的存量資金,極度緊張。
萬國與中經開,如果選擇拉高現貨,就可以通過回購,兌現更多的差價。但是央行希望國債的交易價格與回購價格差價再少一些;財政部則與央行的立場相反,因為差價大一些,有利于通過新券的不斷發行,逐步擴張融資規模,發新券還舊券。
1994年,財政部對于下一年的國債發行量,要求不能低于上年;由于物價不穩,債券發行非常困難。“利率殺傷”
事件的起因,是由于“327國債”的保值貼補率(其實就是直接加息)。事實上,調整債券的利率,對于可交易品種的殺傷力極其巨大。
當年政策有沒有問題?有多大的問題?看看今年以來的市場走勢,就可以略知一二。
2010年1月7日,新年第一周,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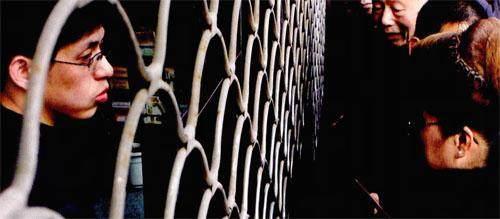
在公開市場發行了600億元3個月期央票,同時進行了300億元的91天正回購操作,利率分別為1.3284%和1.36%,分別較前期上漲了4個基點和3個基點。區區三四個基點,引發市場各方的多少關注,多少猜測?再看看期貨市場,1月7日那天,一共有多少個交易品種,曾被打到“跌停”的價位?當日,股市也曾較大跌幅,上證指數跌70點,跌幅達到1.9%,破位形態明顯——這可是最近發生的事。
要知道,這次央票利率僅增加了三四個基點;市場都有如此波動,當年“327事件”,財政部相當于加了整整500個基點,這就等于把大家都逼上了絕路,“327事件”的后果會是什么?無論多頭,還是空頭,你能逃得過去嗎?
如果不是當年管金生審事詳明,處事果斷,“327事件”的殺傷力,只會更大,不會更小。
草地成了“斗獸場”
按理說,“327國債”是杠桿交易的標的,雖然是浮息債,但也不同于其他債種,因為這是期貨交易品種,利率完全市場化的,在結算之前,如果加息,就等于改變了最早的交易基準。
任何人,作為管理層,你必須尊重交易規則,慎重行事,多聽一聽市場的意見,更不能硬性地干涉、扭曲二級市場的交易價格,否則,對于場內交易的雙方,無論多頭,還是空頭,均有風險(嚴重影響交易雙方的損益)。原本悠閑的各路資本玩家,突然發現,原先一片祥和的草地,驟然成了斗獸場。
正是由于這次“突然加息”,原先很正常的國債期貨,突然成了國債“欺貨”,市場一片嘩然!
“327事件”之中的多空對決,萬國直接的對手盤,不僅有中經開;也有政策面,特別是當交易品受到利率政策嚴重干擾的時候,對于資本市場的交易品種,比如國債期貨交易的后果,到底有多嚴重,現在大家不難想象;如果券商的利益受到損害,特別是當此產品的收益,遭遇“超預期”的“調整”之后,那么,什么是相對合理的“操作策略”,什么是相對正確的“操作選擇”,都值得市場深思。“327事件”的關鍵在于政府貼息,此前,世界銀行也有專家反對搞保值貼補,這種做法,現在稱為“指數化”,就是利率和一種定量指標掛鉤。
當時,在決策層面,也是兩種相反的意見,因而遲遲難做決定。這邊越是遲疑不決,市場的風險就越大,炒作就越激烈。當補貼的決定宣布時,“327”已經進入“死角”,風險陡然爆發。當時不但萬國很苦,場內的所有機構,做得都很苦,中經開同樣做得很“苦”。
市場經典:“空殺多”
后來,不少業內高手以及專家,曾經多次復盤過“327事件”的交易過程,大家其實也相信,在當時那種狀態之下,管的決策,其中確有教訓,但也情有可原。
對于商品期貨來說,大行情,從來都是多頭行情。為什么?就是因為,相對于現金來說,任何商品現貨,再大,也是小品種,而現金是無窮無盡的;多頭想殺空頭,水遠游刃有余。
但在金融期貨而言,“多頭必勝”這個結論,卻是不充分的;因為金融期貨的杠桿率太高,“裸空(無倉拋空)”的成交率非常高。特別是由于“末日結算(最后一個交易日,限制其他交易者進場)”、“生死交割”的存在,多頭不能保證,當場吃掉空頭。
1998年震驚世界金融證券界的“港匯大戰”,港府也是多殺空,但也不敢賭“末日結算”,事實是放了空頭一馬;將“T+0”結算,改為了“T+2”結算;給了空頭返券、交割后離場的機會。很多人不滿意,認為應當“趕盡殺絕”;這是完全不懂期貨的“菜鳥兒”的主張。
“327事件”之所以經典,就在于它是“空殺多”;而且在規則允許的范圍之內的、超大規模的“空殺多”,遍觀資本市場歷史,這種案例,非常罕見;值得今天的我們,認真進行總結、管金生個人錯誤?
管金生撤職后,曾有一段時間,對于“327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市場評論頗多。但是其中有何內情,卻很少有人認真地研究;“327事件”,從此竟然成了一個“市場之謎”,知道的人不說,說的人不知道;而這是有問題的。
我們知道,最后萬國的那筆被取消的730萬口賣單,面值極其巨大;這說明,當天的交易是不可交割的。對于商品市場的期貨交易,理論上不太可能發生不可交割的情況。比如說原油持倉再大,也能在市場上買到足夠的現貨交割。
但恰恰“327國債”這個品種雙方持倉遠遠大于實際可交割的倉位。這不能不說是市場的問題,交易所無論如何應該在某個時點限倉,絕不能發生理論上不可交割的情況。可以想象以當時的認識和市場監管水平,對于“裸空”的風險,缺乏足夠的警惕。
但是,光責備市場機構,是不公平的,真正的問題,還是出在“場外”;期貨市場上交易的價格反映了各方對價格的預期,如果場外人士,比如財政部在調整保值貼補率的時候,不考慮市場價格;超預期增加“保值貼補率”,交易哪里還能正常進行?還不如直接關閉市場呢!
今天的我們應當相信當時管會金生想利用規則挽救市場;理性符合邏輯:“當閃電劈下的時候,你必須在場。”——并非“十足的賭徒”。
有一點,當時不管是證監會,還是上交所,對管金生都是非常客氣的,并沒有在公開報刊上,公布管金生和萬國的名字;很有把管金生保下來的意思,畢竟人才難得;苦心經營萬國,白手起家,建立了當時我國最大的券商。
管金生這個人,當年曾經的中國金融市場之王。無奈的是,他只看到了開頭,卻沒看到結尾。不久后,上海國債期貨市場被關閉;萬國交給申銀接管;對于萬國,可以說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對于資本市場,“再回頭已是百年身”。
沒有真相的悲劇
對于“327事件”,原上交所總經理尉文淵曾經有過一些評論:“我做夢都沒想到會貼息,回頭想想,這算什么事呀!美聯儲調利息時,都是0.25個百分點地調,咱們這一下子就是5個百分點!我記得高嶺講過,當時我買的是泥飯碗,你卻讓我還一個金飯碗,我怎么還得起呀!”
據說,當時高層考慮的,大多限于國庫券的發行和兌付,根本就沒顧及,這個國債的下面,還有個國債期貨市場。國債利率“浮動”,期貨市場“暴動”。尉文淵后來總結說:“從當年的管理者角度看,萬國和中經開的行為都是錯誤的,只不過中經開當時逃過了懲罰,而讓萬國單獨受罰,這是不公平的。”
在當年模糊的風險意識以及低下的市場監管水平下,“327事件”引發的市場和機構的震蕩只能說是歷史的必然。管金生和闞治東曾經是當年的上交所總經理尉文淵的左膀右臂,尉文淵這樣評論這段歷史:“由于管金生的行為讓一批人的命運隨之改變。但對他個人而言,又是一個悲劇,其實‘327事件是個非常復雜的事情,現在卻變成了單單由于管金生的賭博失誤而讓市場崩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