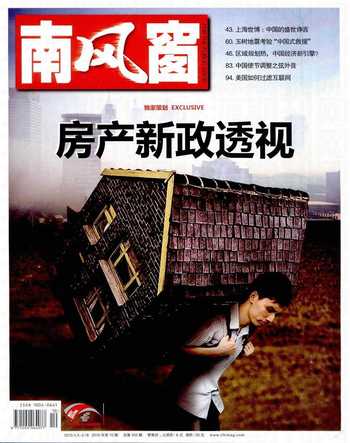中國使節調整之弦外音
趙博淵


建國后一代執掌外交大權,其紙面象征意義要多過政治實際意義。部分人的工作調動所透出的弦外之音,倒是更能折射決策層的外交思維。
2010年頭3個月,中國外交部人事變動陸續曝光,先是領導層新老更替:崔天凱、傅瑩(女)、翟雋3位新人取代何亞非、武大偉兩位老副部長,而部長助理也多了吳海龍、劉振民、程國平3位新手,使得北京總部形成1正7副4助理的領導架構;接著駐外使節大調整,張業遂、程永華、劉曉明、張鑫森、劉洪才分別派駐美日英韓朝五國(早前李輝、孔泉、吳紅波各出使俄、法、德),而李保東、何亞非則各到聯合國總部和日內瓦辦事處任代表。
經過此番調整,包括外長楊沽篪在內,目前外交部領導層和重要駐外使節全部為1950年以后出生,媒體稱之為“‘共和國一代領軍中國外交”。這讓筆者想起了2002年看過的一幅漫畫,畫面上小泉純一郎歷史性地訪問朝鮮,在機場與金正日親切握手,旁邊一個大嘴記者唾沫橫飛地介紹著兩人的“共同語言”——諸如都是1942年出生,都是卷發等花絮。
竊以為,建國后一代執掌外交大權,其紙面象征意義要多過政治實際意義。尤其,1950年生人在思維邏輯和行為模式上比1948年生人更具先進性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青春經歷——人格和價值觀的成長及成型期都正好趕在畸形的“文革”10年。真要談什么政治意義,部分人的工作調動所透出的弦外之音,倒是更能折射決策層的外交思維。
何亞非謫遷,張業遂履新
不妨先說說何亞非。
在1月4日的大調整中何亞非被免去副外長職務,引發外媒關注。在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何亞非態度強硬,當場指責美國代表斯特恩“極為缺乏常識”。問題是當德國總理默克爾提出2050年發達國家減排80%的時候,何竟不假思索地加以回絕。奧巴馬據此認定何說話做不得數,進而有了后來闖入中國會場找溫家寶總理私聊的反常舉動。如今年僅55歲的何亞非被免職,他的去處自然為外媒猜測。根據他任職美大司、駐美公使的履歷,駐美大使或駐聯合國大使是最大的可能。總之,要么華盛頓,要么紐約,都在美國。結果,兩個都落空,何3月被派去瑞士日內瓦。
就資歷而言,2008年才升任副部長的何亞非,比2003年即任副部長的張業遂自然要差一截,落選駐美大使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但相比在日內瓦任職之前僅做過駐贊比亞大使的李保東,何亞非無疑更有資格接張業遂留下的駐聯合國大使一職。可是,根據《維也納外交公約》第四條規定,駐外大使的人選要經接受國同意方可赴任,接受國若否決亦無須說明理由。紐約亦在美國境內,倘若美國不樂見何亞非到來,中方也無可奈何。而將何派往日內瓦,決策層向美國示好的意圖也就不言自明了。
由于何亞非的缺陣,張業遂在無競爭背景下從紐約轉到了華盛頓。
作為駐美大使,張業遂有8位前任。在中美關系平淡的前期,除了首任柴澤民,駐美大使都做過副外長或部長助理,且多在聯合國工作過,與美交涉多偏重國際而非雙邊問題。進入1990年代中期,隨著中美貿易的升溫以及摩擦的加劇,決策層在駐美大使的人選方面越來越注重在華盛頓的派駐經驗。當然,紐約和華盛頓的經驗兼具則最好不過。張業遂除早年在英國做過使館隨員,外派都是在駐聯合國代表團,對美工作經驗局限在任禮賓司司長期間負責的江澤民、克林頓互訪。說到底,張所長者是多邊外交,并非美國問題。聯合國近200個國家,各有各的立場和小算盤,正是其縱橫捭闔的好場地。現在一下從紐約轉到華盛頓,猶如把一個跆拳道選手放到狹小的拳擊臺上,光靠注重協調包容的作風顯然不夠。
張業遂履新后一面斷言“中美關系已經轉入正軌”,一面主張“國之交在于民相親”,顯示其“兩面下注”的思路。而在美國媒體看來,張業遂曾長期主管軍控和裁軍事務,是中美之間溝通伊朗核問題的極佳人選。鑒于中美最近10年的國際合作偏向反恐及維護區域安全,張業遂的履新應該能給中美關系注入新的動力,但是雙方能好多久,仍然不確定。
傅瑩模式的先進性和局限性
外交人事調整中最奪人眼球的當屬傅瑩由駐英大使晉升為副外長。女性、蒙古族這些元素使她在一眾黑、灰西裝男的包圍中猶如萬綠叢中一點紅。她是中國第二位女副外長,考慮到第一位王海容履職年代的特殊性,傅瑩應該算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
傅瑩的晉升,可謂題中應有之義,因為在過去兩年中,她在英國的表現堪稱優異。最重要的是,與中國外交官普遍的講究紀律、缺乏親和力不同,她的公關工作做得很好,以至于國內出現“傅瑩模式”的說法。傅瑩的晉升也是當局對傅瑩模式的認可。
多數中國官員習慣于灌輸和威壓,見到外國人總會下意識地挺一挺腰板,過于刻意做作。傅瑩模式是一種說話的藝術,要訣在于傾聽和溝通,這可說是近年來中國外交官用西方公關學與西方人交往的少有典范。概括而言,傅瑩模式包含了三方面。
首先是形象。或許是身為女性的便利,她一反中國官員慣常的沉悶死板,穿衣著裝很是時尚高調,形象氣質不錯。其次是多層次外交。傳統外交主要是和所在國政商界人士打交道。屬于高層外交,公共外交概念提出后,與當地社會中下層人士交流也成為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對照傅瑩2004年駐澳大利亞至今的種種積極表現,大致與中央在非典危機之后對公共外交的倡導同步。第三,是對媒體有選擇性的利用。傅瑩正是從2008年在英國媒體上撰文反擊藏獨之后才逐漸為國內公眾熟知的。在發稿方面,傅瑩并非專找大報,而是根據文章內容和英國報紙的受眾特點有意識地選擇合適的報紙。這是很聰明的做法。
傅瑩個人無疑是成功的,但這不代表傅瑩模式能夠在中國外交戰線大面積復制。傅瑩的成功無外乎個人實力、性別優勢和英國媒體的影響力。傅瑩年輕時就愛好舞文弄墨,英文寫作也不錯;在中國的駐外使節中,女性本就少,自然更容易出彩;而傅先后派駐的澳、英都是有影響力的西方國家,這種優勢放大了她在當地媒體上的聲音。換言之,學她并不容易。不過,大使為駐在國媒體撰文先例一開,其他外交官所受的限制也就少了。
技術進步難脫根本被動
張業遂也好,傅瑩也罷,以他們代表的中國外交官在近幾年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一進步主要體現在公關活動和形象包裝上,屬于技術層面的小進步。如果指望通過技術層面的小進步就能夠扭轉外交上的根本被動態勢,恐怕是要大失所望了。
事實上,被國內熱捧的傅瑩模式在英國所收到的回應遠不像國內媒體描述的那樣樂觀。政商界更多地是將傅瑩的言行視作中國與國際接軌的一種積極表現,至于刊載傅瑩文章的媒體,態度則審慎得多。美國史上臭名昭著的麥卡錫善于鼓動利用媒體,但登過他文章的美國報紙恐怕沒誰會認可他的主張——美國媒體后來感到被麥卡錫愚弄了。
外交技術的進步對中國有益,但不能代替戰略層面的改良。1995年希拉里出席世界婦女大會時指責中國人權,國內針對極具煽動性的美式演講法拋出過一個“熊蕾式演講法”應對,但效果微弱。胡錦濤主席去年提出要改善我國的道義形象,楊潔篪部長今年初也提出了影響力、競爭力、親和力、感召力“四要求”,這些都不是在外媒發幾篇文章就能搞定的。譬如一個馮正虎事件,就得外交部解釋半天。作為中國外交的具體執行者,外交部在技術層面改善提升是分內之事,至于擺脫外交被動,就要決策層多花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