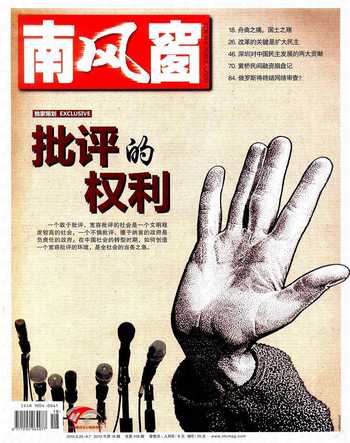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邏輯
曾 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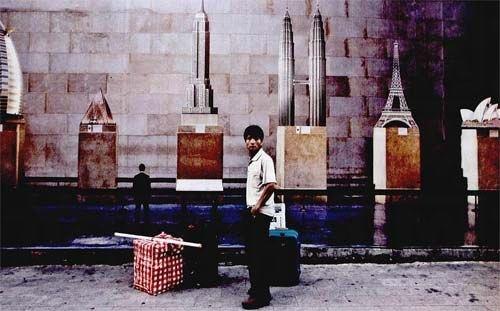
如果把“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看成是一幢房子的話,那么這個房子的頂層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地基是“經濟重大轉型期”,墻體是“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梁柱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后危機時代,金融海嘯將逐步消退,全球經濟格局將面臨調整,中國經濟發展也將面臨轉型。當“十二五”時期即將到來的時候,有四個“詞匯”在國內經濟界尤為耀眼:經濟重大轉型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以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它們在不同的場合頻繁出現,令人目眩神迷。
事實上,從戰略角度出發,它們基本反映了“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基本內容。如果把“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看成是一幢房子的話,那么這個房子的頂層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地基是“經濟重大轉型期”,墻體是“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梁柱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戰略邏輯的“頂層”
十七大報告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代替了1995年提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這標志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一次重大改變。在“十二五”時期即將到來的時候,中央政府頻頻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性,并按照這一思路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略部署,使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步“顯性”成為“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邏輯的核心內容。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內容,但是與經濟增長方式不同,經濟發展方式還要求在經濟高質量增長的同時,保證自然、社會、文化和人類的全面發展。因此,“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將越來越多涉及社會發展等更高層次的問題。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應該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要注重經濟增長的平衡性,也就是“權衡”好經濟發展中當前矛盾和長期問題,保持經濟高質量和持續增長;二是注重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關注社會公平和人的發展,讓社會個體公平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和成果;三是注重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友好,即在經濟增長中注重資源使用節約和自然環境保護,處理好人和自然的關系。第一個層次保證了經濟實體本身的“健康發展”,第二個層次保證了作為經濟發展主體人類的“持續發展”,而第三個層次則保證了作為經濟發展載體自然的“穩定發展”。作為“十二五”時期經濟發展戰略的核心,這三個層次的內容將形成未來5年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頂層設計”。
全球的經濟轉型期
“十二五”時期是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發生潛在轉變的重要5年,國內外經濟發展將發生重大轉型,這是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背景和依據。從需求層面看,中國和世界經濟將處于“經濟重塑平衡”階段;從供給層面看,中國和世界產業將步入“產業升級創新”階段。
未來一段時間內,全球經濟可能進入全面轉型的時期,世界經濟發展將步入“結構再平衡”和“新產業革命”階段。首先,全球經濟將處于逐步從失衡向再平衡轉變的適應期,將面臨需求結構的深度調整。一方面,這些國家的儲蓄率將逐步回升,而消費率可能進入下降通道,這將“倒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不得不降低儲蓄率和提高消費率,由此引發全球消費與投資需求格局的重大變化。另一方面,作為各國國內需求變化的“鏡像”,隨著全球消費與投資需求格局的變化,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進口將銳減,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不得不通過擴大內需尋求經濟發展的內源動力,世界經濟面臨再平衡的調整。全球需求結構的變化,使得國際市場的有效需求很難在短期內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全球需求總量將進入一個“收縮”區段。
其次,全球經濟將處于逐步從產業全球化向產業去全球化轉變的劇變期,全球產業格局將面臨激烈競爭和重新洗牌。一方面,金融危機“催發”了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包括新能源、物聯網和生物技術在內的新興科技行業,成為各國競相爭奪的戰略性產業領域,這導致全球“產業戰爭”一觸即發。另一方面,為了在擠出虛擬經濟泡沫的同時,強化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部門的基礎地位,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開始極力推行“再工業化”戰略和“鼓勵出口貿易、創造國內就業”政策,促使世界產業聯系將從之前的產業鏈合作轉變為產業鏈競爭。產業格局的變化,將促使全球產業發展進入“創新經濟”時代。
對于中國而言,“十二五”是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將進入“結構優化調整”和“產業升級創新”階段。首先,中國經濟將處于從內外失衡向內外平衡轉變的過渡期。一方面,金融危機之后,隨著外部需求的急劇緊縮,中國傳統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如何擴大國內有效消費需求,減少國際貿易順差,從而尋求“內外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將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征。另一方面,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城市化”也正在加速推進,可能止步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跨越這一陷阱的關鍵在于提振國內居民消費,使得中國經濟內部調整的壓力增大,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更為緊迫。外部沖擊和內部約束已經成為中國持續發展的障礙,中國將在朱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處于“經濟結構”漸進優化調整的階段。
其次,中國經濟將處于從低成本產業階段向高附加值產業階段轉變的過渡期。一方面,“十二五”時期,中國將處于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工業體系的逐步升級和服務業迅速發展。另一方面,隨著全球產業革命的興起,中國產業也必然融入這一潮流,通過自主創新實現產業體系的升級也將成為未來中國產業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征。“升級”和“創新”已經成為未來產業發展的重要主線,中國將逐步進入“產業升級創新”的“高速通道”。
經濟結構如何優化
“十二五”時期,世界和中國的轉型可以理解為兩個部分,一個是需求的轉型,也就是市場的轉型,表現為需求結構的轉變;另一個是供給的轉型。也就是生產的轉型,表現為產業結構的調整。結構的矛盾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因此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將成為“十二五”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主線,而這一主線的“分鏈”要從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兩個方面進行理解。
首先,中國需求結構失衡的關鍵在于內外結構失衡,而中國的投資需求往往是與外需聯系在一起的,所以需求結構優化的重點在于擴大消費需求。同時,在消費需求內部,居民消費率的下降速度最快,從1990年的48.8%下降至2008年的35.3%。從這個角度來說,需求結構調整重在擴大居民消費。“十二五”時期,擴大居民消費必須緊握兩個“抓手”,一個是推進“城市化”,另一個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根據相關研究,中國城市化率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有1000萬到1200萬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約拉動最終消費增長1.6個百分點。而按照錢納里城市化率與經濟
發展階段關系,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城市化率應在36.4%~49.9%之間,工業化后期城市化率提升為65%左右。而在2008年中國城市化率為45.7%,按照工業化中期城市化率標準衡量,仍有4.2個百分點的提升空間;如果“十二五”期間,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階段,城市化率至少要提高到55%左右,那么將有9.3個百分點的空間。所以,加快城市化進程將是“十二五”時期中國釋放居民消費和擴大內需的重要戰略。
根據筆者計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呈下降態勢,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91.7%下降到2007年的53.4%,對城鎮居民消費率變動的貢獻約為-300%;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從1978年的35.7%下降到2007年的20.3%,對農村居民消費率變動的貢獻約為~44%。而居民收入份額的逐步減少對居民消費快速下降的貢獻率為60%。這也就是說,如果居民收入份額上升1%,那么居民消費將上升0.6個百分點。因此,通過逐步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傾斜,將極大促進中國消費需求的擴張,進而提升內需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
其次,中國產業結構滯后表現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偏重加工制造,產業結構失衡,現代服務業發展緩慢;二是創新能力不強,產業附加值低,難以控制全球價值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產業結構升級必須從推進工業化進程和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兩個方面入手。相關數據表明,中國服務業占GDP的比例僅為40%左右,低于中國所處工業化中期的“標準水平”,不但低于整個世界超過6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低收入國家43%的平均水平。而高端服務業產值雖然已經占中國GDP的20%左右,但這一比例也還大大低于全球平均40%以上水平。因此,加快推進工業化從中期向后期演進,提高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在GDP中的占比,是促進“十二五”中國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重要途徑。
根據相關研究,近幾年,中國制造業增加值率一直處于20%左右的水平,大大低于美國31%的水平,也低于世界2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中國主要制造業的高加工度系數不但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水平,這說明中國產業附加值很低。另外,中國產業的技術指數一直維持在較低的水平,制造業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僅為美國的1/4,而高技術產業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更只有美國相應產業的1/8。
這些數據說明,中國產業整體質量較差,缺乏自主創新,位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所以,通過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相關產業優化升級,并提升國內整體價值鏈的技術高度,將是“十二五”時期中國產業優化升級戰略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從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
從理論上說,經濟結構失衡在本質上是市場機制扭曲的結果,而市場機制扭曲的根蒂在于經濟體制滯后。改革開放的前30年,中國進行的是“增量改革”,即通過改革使計劃機制讓位于市場機制,打破束縛經濟要素投入效率的經濟體制,釋放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高速增長。“增量改革”是一個“皆大歡喜”的經濟活動,它是一個“做蛋糕”的過程,使社會的大部分人受益,所以推行起來比較容易。但是,“增量改革”的“紅利”正在逐步褪色,由經濟總量“超常”膨脹帶來的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層出不窮,所以中國的改革正逐漸步入“存量改革”的階段。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暫停了中國改革的進程,所以“十二五”時期,隨著外部影響的消退,中國“存量改革”的大幕即將拉啟。
“存量改革”的本質是全方位推動整體經濟體制的改革,是一個“切蛋糕”的過程。由于涉及利益分配問題,“存量改革”是一個“眾口難調”的經濟活動,它必將損害一部分社會成員的已有利益,推行起來將會面臨舉步維艱的境遇。然而,“經濟存量非合理”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原罪”,也是妨礙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沉疴”所在。
從經濟結構調整任務的不同層面出發,“十二五”時期,中國要把“創造內需”和“調優供給”作為“存量改革”的兩個輪子。從調整需求結構的角度來說,要做好兩項改革:一是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釋放中低收入階層消費需求。二是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農民工轉化為市民的進程,深化城鎮化進程,調整城鄉二元結構,啟動城鄉“雙極”消費沖動。
從優化供給結構的角度來說,也要加快推進兩項改革:一是,加快壟斷性服務行業的改革攻堅,加快銀行、保險、鐵路、民航、郵政、電信等壟斷行業領域的改革步伐,加大引入民間投資力度,提高效率,優化產業結構調整的市場環境;二是改革要素價格體系,特別是資源價格體系,使資源價格反映資源稀缺程度,改變我國“低成本”產業發展模式,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而所有改革推進的前提是政府轉型,沒有政府轉型的突破,改革就難以深化,經濟結構難以調整,發展方式難以轉變。因此,“十二五”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推動政府從經濟建設型到公共服務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