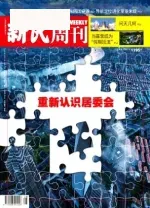政改不能寄希望于鄉政府
于建嶸
中國的政治改革有一個問題,從哪里改起?從中央改,還是從地方改,從司法制度改,還是從選舉制度改,或者從其他什么地方改?有時候,人們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基層的領導人身上,希望他們能闖出一條新路,然后可以得到肯定和推廣。就像最近四川巴中白廟鄉公布了政務開支明細,大家就在探討此事在更高層面和更大范圍上的可能性。但我認為,我們不能把政治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地方的基層官員身上。
這是三個原因決定的:第一是地方改革的動力不足。地方領導進行改革的動力無非三種。第一種是壓力,當地人事關系復雜,派系斗爭激烈,社會管治困難,地方官員只能搞改革;第二種是個人因素,不少地方政治改革中都可以看到那些有政治理想和抱負的基層官員的身影;第三是出于政績方面的考慮,如果一個地方由于各種各樣的條件限制,經濟搞不上去,官員出于政績考核的需要,會想辦法從其他方面下功夫,包括政治體制改革。
地方搞政改,空間也有限。搞政治改革有風險,因為你不知道底線在什么地方。政治改革不同于經濟改革,后者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有一個硬指標,也即GDP作為考核的依據,政治上的剛性限制很多,隨時可能被否決。比如步云縣搞鄉鎮選舉,就有人說他們違憲。地方官員搞政治改革,與其說是試驗,不如說是試探,試探底線在哪里。
第三是制度化程度低,人走政息。地方政治改革不可避免地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主事者的個人因素太大,改革措施不能制度化,下一任官員完全可以不理前任的這一套。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改革才有幸存下去的希望:前任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最高層面的肯定;或者前任官員升遷,直接領導現任官員;或者媒體、學者和上層不斷關注,改弦更張的成本較高。
20多年來,各地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探索,幾乎都沒有保存下來,正是由這些原因決定的。在今時今日,政改需要中央做出安排,沒有這個環節,中國的改革就只能是一種媒體和知識界內部的共識,無法轉變成普遍的社會行動,最終只能變成五年一輪回的心理安慰。
這個過程中,建立兩個共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在憲法的基礎上解決權力來源和權力監督問題。第二,改革的當務之急是監督基層的權力運作,改變基層政權的權力來源。
政治改革之所以應該把目標定在基層,因為上層和中層的改革很困難,不僅沒有動力,也沒有路徑。過去20年里,我們談政治改革,注意力都在村一級,但村不是一級政權,鄉鎮的權力也不完整(起碼沒有司法權),所以我認為應該把縣作為中國政治改革的起點。
中國的縣是很特別的。縣以上的官員都是管官的官員,不用和民眾直接發生關系,只有縣政權是直面民眾的權力。這一級政權沒什么錢,財力大多被上級或更上一級政府抽走了;也沒什么人,官員流動性很強。我去過的有些縣,所有的縣委常委都不在當地生活,都住在鄰近的大城市里,一到周末,一個人都找不到。看上去,縣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無足輕重,權力很小,但實際上,有些縣委書記什么事情都敢干,擁有無邊的權力。
這些年來有一個明顯的趨勢,很多群體事件都是在縣里發生的,縣政權是群體事件中人們訴求的主要目標。縣里的壓力很大。以維穩為例,不管是省級還是市級政權,維穩的壓力不會涉及所有官員,唯獨縣里存在一票否決制。縣里的官員,在維穩的問題上,人人有份,誰工作做不好,誰就要丟烏紗帽。
這種壓力已經迫使我們要盡快改變縣級權力的來源方式,盡快完善縣級權力的監督。第一步應該從人大制度開始,縮小縣人大的規模,讓人大代表職業化,排除官員當人大代表,以便人大監督政府。第二步要讓縣級法院和中級法院在人、財、物上與地方政府脫鉤,用獨立的司法來制衡縣政府的權力。
當然,我們用人大和司法來制衡縣政府的權力,也應該把本地事務的決策權還給縣政府。
最后還應該檢討目前異地為官的任職回避制度。本地官員不由本地人士擔任,這種制度在皇權時代是有效的,也不無必要,因為官員代表的是皇帝的權力,這種權力必須與地方利益切割開來。有這個制度,很難培養對地方有責任有感情的地方政治家,老百姓說“第一年換人,第二年撈錢,第三年調動”,每一任官員都要重新熟悉情況,有百害而無一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