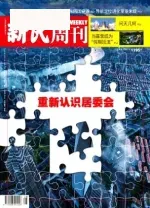別撿了芝麻,丟了西瓜
楊紅旭

從現實情況來看,通過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住房租賃市場不足,但絕不能奢望能借此取代對住房租賃市場的規范和完善。
近段時間,關于公共租賃住房的話題多了起來。上海市領導表示二季度將拿出一個政策草案,面向社會征求意見。北京市官員聲稱要將探索公租房土地供應新模式,不再通過招拍掛出讓土地,而是通過“年租制”每年收租,以降低土地成本。重慶市長黃奇帆更加高調,宣布今年重慶將啟動500萬平方米公租房建設。
中央層面,2009年建設部制訂《公共租賃住房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今年出臺的“國十一條”中,明確規定各地應把公共租賃住房列入本地2010-2012年住房建設規劃。地方層面,深圳、北京、常州、廈門、重慶等少數城市已率行進行實質性的嘗試。社會層面,那些既沒資格享受住房保障政策,又買不起商品住宅的本地中低收入家庭——“夾心層”,以及暫時購房有困難的小白領、外來務工人員,莫不翹首以待公共租賃房。
以上海為例,從居住主體上劃分,住房體系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產權式住房,另一類是租賃式住房。租賃型住房包括廉租房、未房改的老公房、將要實行的公共租賃房和市場化的租賃房。公共租賃房既要向下對接廉租房,又要向上對接市場化的租賃房,而與老公房的關系不大。目前廉租房運作模式已經相對固化并趨于成熟,而市場化租賃房則較散亂。
實際上,目前上海市的住房租賃市場總體供應量并不小,根據筆者的測算,全市市場化住房租賃面積為3100萬平方米左右。而且未來很多年,隨著新建商品住宅面積的持續增長,租賃型住房的可供應面積還將相應增加,與發達國家相比,上海市場化租賃住房比重偏低,基本不必為供不應求而擔擾。問題在于兩方面。一是供應結構不合理。中低租金的中小戶型住房供應不足。住房租賃需求主體是來滬從業人員、大學畢業生、引進人才和上海本地的中低收入家庭,多數需要租金水平較低的中小戶型。部分外來務工人員或少數剛畢業的大學生,急需低租金的集體宿舍或藍領公寓。況且,經營住房出租業務的企業和機構太少,導致住房供應的集約化水平極低,市場非常不成熟。
二是市場失序和管理缺位。住房租賃市場處于放任狀態,房東出租行為存在不規范之處,比如限制房客對房屋的裝修裝飾等,合同期內要求漲租金,甚至以各種理由驅趕房客等,造成了租期的不確定性和短期化,房客難以長期租賃。另外,上海還存在嚴重的群租現象,如同牛皮癬一樣久治難愈;而房產租賃市場準入門檻較低,部分中介門店存在亂收費、違規操作等不良現象。
理想的情況是,在住房租賃市場健全的條件下建立公共租賃住房制度。但這一條件當前并不具備,退而求其次是一邊完善和規范住房租賃市場,一邊構建公共租賃住房體系。從現實情況來看,通過發展公共租賃住房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住房租賃市場不足,但絕不能奢望借此取代對住房租賃市場的規范和完善。否則會出現這樣的糟糕局面:租賃住房空置嚴重、浪費社會資源的同時,政府卻源源不斷地在公共租賃住房上投資或補貼企業。
當然,筆者對公租房還是心存顧慮。1998年房改之前,我國實行的福利化分房制度,正是低租金的公共租賃房,如今重新大興公租房,是否會“開歷史倒車”?因此,發展公租房的前提,是堅持住房消費的市場化方向,需要大力規范和支持住房租賃市場的發展。市場為主,計劃為輔,公共租賃住房只是對住房租賃市場的“補位”,而非“奪位”。(作者為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綜合研究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