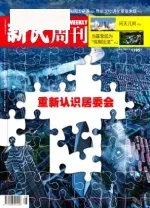賀強:低碳不能停留在口號上
楊江


我們已經過慣了高碳的生活,一定要養成自覺的低碳習慣,從一點一滴開始做起。你會發現,只要你有心,完全可以在保證原本生活品質的情況下實現低碳。
今年的兩會,低碳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很多代表、委員的提案都涉及“低碳”,兩會臨近閉幕,圍繞低碳的討論仍在熱烈展開。談及低碳經濟以及社會上出現的“低碳風”、“偽低碳”現象,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賀強表示,很多人對低碳的概念認知不清,甚至可以說比較糊涂,尤其在一些商業領域,只是把低碳當作了一個標語、口號。
這位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發展的專家早在去年的兩會上就遞交了關于低碳經濟的提案,只不過,去年他遞交低碳經濟的提案時,低碳還沒有引起廣泛的關注,短短一年,關于低碳經濟已經引起了人們如此之高的關注,這讓賀強頗感欣慰。
在這一次的兩會上,賀強一共遞交了五個提案,其中就有兩個關于低碳經濟,一個是變革經濟發展方式,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一個是建議將北京作為低碳創新城市。賀強甚至提出,應該建立低碳評估體系,與各級政府的政績掛鉤,以此促進低碳經濟。
作為一名專家委員,賀強的提案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以至于3月2日下午,他在自己的研究所召開了一個小型的新聞發布會對媒體集中闡述他的觀點。
他直言不諱,現在低碳風流行,包括很多代表、委員在內,真正能身體力行做到低碳的并不多。3月11日深夜10點30分,結束完一場關于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討論后,剛剛回到駐地的賀強接受了《新民周刊》長達一小時的專訪。
“要促進低碳經濟,首先就要正確認識什么是低碳,為什么要重視發展低碳經濟,然后便是端正態度,如何去推動低碳經濟。”賀強說。
發展低碳經濟是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唯一途徑
賀強:現在科學界關于低碳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大部分推出低碳結論的思路是看到氣候變化、全球變暖,原因被認為是二氧化碳排放過多了,所以各國都要保護環境、降低碳排放。但是這個觀點,科學界存在異議——有人認為這是發達國家的一場國際陰謀;有人認為,地球從長遠來看,是變冷而不是變暖;還有觀點雖然認可地球在變暖,但認為是地球變暖導致了二氧化碳過多,而不是二氧化碳過多導致了地球變暖。這就有點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味道。
這些觀點,我認為都不足為評。我的思路與一般提出低碳結論的思路是不同的,你首先要看到,甭管是不是發達國家的一場陰謀,污染就會增加碳的排放這是毋庸置疑的,一切的污染都可以歸結為碳排放,雖然有點絕對,但也可以這么說了。污染很復雜、多種多樣,但碳排放是可以計量的。
《新民周刊》:那么,您為何提出發展低碳經濟是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唯一途徑?您的思路不同在哪里?
賀強:通過長期研究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我們發現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是越走越窄,無路可走了。因此必須變革經濟發展方式,找一條全新之路。為什么這條路就是低碳之路呢。這次兩會,很多人談到變革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以及低碳經濟,但這三個概念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稀里糊涂,特別是變革經濟發展方式,為什么要變?往哪變?怎么變?很多人孤立看待這三者,不知道它們有怎樣的內在聯系。
我們提出發展低碳經濟是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唯一之路,是因為我們現有的經濟發展方式幾十年來得了一種病,忽冷忽熱,我把它叫做“打擺子”。
經濟運行忽冷忽熱與政策調控有關系,我們每年都在追求GDP增長,但稍微一快我們就遇到兩大瓶頸——資源瓶頸與環境瓶頸。
資源有限,經濟增長一快,超過12%,甚至11%,煤電油全面緊張,這就是所謂的經濟過熱,發燒了。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用政策調控收緊,把它調下來。比較典型的就是2004年浙江一周停五天的電,那還怎么生產啊,亂套了。迫不得已,政策必須調控,但政策一收緊,經濟就滑坡了,跌到8%,甚至像2008年跌到9.6%,經濟又過冷了。
很多人搞不明白,多年來,我們一直在喊“保八”,為什么呢?8%的經濟增長速度,在各國都是很高的,很多國家都達不到。但為什么在中國8%就過冷了呢?因為在中國,經濟增長低于8%就遇到三大瓶頸——每年新增人口壓力、新增就業壓力以及新增老年人口壓力。
獨生子女政策已經實行了30多年,在1976年普及獨生子女政策之前,1970年前后我查過人口增長率的情況,大概有5年我們幾乎每年生出一個澳大利亞,比如說1970年一年的新生兒就是2300萬,我們是承受不了這種人口的大幅度增長。后來我們實行了只許生一個的政策。但是即使如此,實行了這么多年,在2000年以后,我們每年新生兒還1000多萬。只是2008年、2009年有所下降,但是最少也五六百萬。每年的新增人口跟新增GDP肯定是相關的,他要吃到GDP,它不會產出。有專家算過,我們每年新增人口會吃掉經濟增長的7%,因此,經濟增長一旦降到8%,甚至到9%,我們就受不了了。
第二個瓶頸,也就是每年新增老年人口的比重,我們現在已經進入老齡社會了,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達到1.6億,估計到2050年,老年人比例會達到40%至50%,壓力是很大的。因為老年人沒有工作能力了,也是消耗GDP,不會產出的。
第三個瓶頸——每年新增就業的壓力。我們經濟如果不斷下滑,就業崗位就會越來越少,滿足不了每年大量增長的新增就業的要求,最典型是在去年,580萬大學畢業生、幾千萬農民工都要找工作,可是經濟受到美國沖擊下,我們所能提供的崗位很少,出現了就業難。
《新民周刊》:這三個瓶頸總體來講都是人口瓶頸。
賀強:上有瓶頸,下有瓶頸,經濟既要較快增長又不能增長太快,這不是很大矛盾嘛,所以,我們的經濟只能在狹窄的空間里運行,才能穩定。這種運行我把它叫做中國經濟的剛性運行,沒有任何彈性可言,而且這個狹窄的空間還在不斷變窄,再過一二十年可能就無路可走了。
經濟發展冷熱病的根源就在于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上,別看經濟體制改革了,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幾十年來卻沒有改革——在總體技術水平不高的前提下,我們只是依靠外延的簡單擴大也就是通過擴大生產規模來推動GDP增長和經濟發展。
這種模式下,必然大量消耗資源,因為你技術水平不高,能源轉化率很低。這必然導致大量破壞環境,造成嚴重污染。
《新民周刊》:您的意思就是我們的行為一直是高碳?
賀強:是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仍然依靠外延的簡單擴大,就更會加劇資源的消耗與環境的破壞。總體而言,這種經濟發展方式是粗放式的,沒有前途,必須變革,走一條重視總體技術水平不斷提高前提下的,依靠技術進步、技術創新推動節能環保等新興產業發展來推動經濟增長的道路。
這條道路簡單來講就是集約化經營、內涵化發展。內涵化發展的特點是總體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水平的提高來推動GDP。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我們就可以節約資源,減少對環境的破壞。這樣才符合我們資源短缺的國情。
這條路其實就是低碳經濟之路。
重大技術突破是低碳之路的關鍵
《新民周刊》:其實,在國際上,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了一種新潮流。
賀強:是的,能源、環境和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所面臨的三大問題。為了有效兼顧三者利益,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京都議定書》中首次提出排放權交易制度。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世界各國雖然未能就減排目標達成一致意見,但都殊途同歸走上了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低碳經濟之路。
說是陰謀,其實在低碳方面,各國已經取得了共識,我認為各國走低碳經濟道路,不是簡單地應對氣候變化、全球變暖,也是考慮到他們國家的經濟發展。
《新民周刊》:那么,我們的低碳經濟之路又如何實現呢?難點在哪里?
賀強:在低碳技術領域上我們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差距是不大的,有些方面,我們甚至領先。不像傳統產業。對我們而言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關鍵就看我們能否抓住。可以說在低碳經濟道路上大家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關鍵就看誰起跑得快,轉變得快。
有不少企業提出來,我不賺錢,搞什么低碳啊。這就是一個如何正確認識的問題。我們選擇了低碳之路,不意味著我們沒有瓶頸與障礙。但這個瓶頸不像人口與環境瓶頸那樣不可打破,不能遇到一點障礙我們就打道回府了。
平心而論,我們的新興節能環保產業目前確實都處于投入期,技術不成熟,產業化也比較落后。投入大、產出小,成本高、受益低,這是主要的障礙。要打破這個障礙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新興產業領域一系列的技術上,3到5年內必須要有重要的突破。
溫家寶總理這一次在政府工作報告里關于發展科學技術這一段連續用了三個突破——在關鍵技術上突破、在與民生有關的技術上突破、在戰略發展技術上突破。
在節能環保領域,重要技術突破的意義非常重大,很可能某一項重大技術的突破會導致一場產業革命。
比如電動汽車,我們現在搞的電動汽車就像電動玩具一樣,跑幾十公里就不行了,只能采用雙模混合動力系統,還得燒汽油、天然氣,并不能有效起到節能環保的作用。雙模混合動力系統本身很復雜,越復雜,故障率就越高,而且成本增加,也不利于普及。成本高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種高碳的表現呢?
我們現在的電動汽車其實只是停留在概念。核心技術是電池,怎么樣才能通過技術使電池的容量更大、充電更快,使汽車跑得更遠、跑得更快?如果這塊有技術突破,蓄電池充一次電可以跑四五百公里,甚至可以在后備箱備一塊電池,跑長途,一兩千公里。那就不得了啦,那么用不了5年滿大街跑的都是電動汽車了,10年,在馬路上找汽油車都可能找不到了。
所以技術突破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就像小平同志講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新民周刊》:問題是,指望通過企業自身的動力去推動這個技術突破會不會過于樂觀?
賀強:不,很多企業其實都組建了自己的研發團隊,因為他們也知道一旦實現了重大技術突破,將給他們帶來無窮的利益。前不久,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組織到臺灣考察,我們考察了一個技術研究院,臺灣的科研水平很高,而且科研成果迅速產業化,迅速產生經濟效益。
我們的問題恰恰就在于科研成果的產業化是相當落后的,這次兩會一名政協委員講我們的科研成果產業化是5%,而發達國家是80%。因此,我們要走低碳之路,重點就是要大量地向節能環保領域的研發、產業化花功夫,通過政策和資金支持他們,爭取兩三年內實現重大技術突破。這樣,我們的低碳之路就打通了。
我們現在面臨著一個擴大投資、防范美國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滑坡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但遺憾的是,我們投入的大量的錢都砸在鐵公機上,鐵公機可以拉動GDP,但這是短暫的。其實完全可以拿出一部分投入到節能環保產業的技術研究、技術產品的產業化上。那就不得了。你把錢砸到這方面,也會產生GDP,而且一旦產生成果還能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產生持久的動力。
所以,我認為大家的認識還是不到位的。
走出低碳風與“偽低碳”的誤區
《新民周刊》:您剛才講了很多,都是關于低碳經濟的重要性,但其實關于什么是低碳經濟,低碳經濟包含哪些內容,很多人也是稀里糊涂。
賀強:確實如此!低碳經濟,我認為,首先最重要就是節能環保、新能源等新興產業才是它的龍頭產業。既環保又能產生效益,經濟才能持久發展。但低碳經濟不僅包含這些,還包括我們現在全部的產業甚至包括個人,比如個人的低碳生活。
低碳是一場革命,改變人們的觀點與生活方式。發展低碳經濟,首先人們固有的高碳觀念都要改變,有人開玩笑地說,低碳就是少喝酒、多喝茶,少吃肉、多吃素。
這一次政府工作報告上提到一個非常新的詞語——森林碳匯。真正的低碳生活,發展低碳經濟有一個很重要的碳中和的概念,比如坐飛機是高碳行為,下了飛機你可以買幾棵樹,種樹中和。
碳中和不僅是企業與個人所要做的努力,甚至我認為,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碳排放權交易都是一種碳中和的表現。
《新民周刊》:您的意思是,在做不可避免的高碳行為的同時,要去有意識地做一些低碳行為來彌補?
賀強:是啊。低碳經濟的內容方方面面,包括各行各業、每個人,表現形式有多種,比如煉鋼廠,過去煉一噸鋼需要兩噸碳,現在通過技術進步,降低到一噸碳,這也是低碳經濟。
《新民周刊》:非常感謝您剛才為我們厘清了低碳經濟的概念,現在低碳風流行,能不能為我們診斷一下,我們走進了哪些誤區?
賀強:我認為誤區在于人們對低碳經濟缺乏研究與思考,狹義化、籠統化、標語口號化了低碳的概念。
《新民周刊》:在一些高碳領域,比如房地產業,營銷時什么詞流行用什么詞,前幾年流行節能、環保,于是它們就打出了綠色地產的概念,現在一夜之間又都打出了低碳地產的旗號,其實,我們知道,房地產業的低碳技術目前還沒有成熟,它們的地產離真正的低碳地產還相去甚遠,這種行為被業內很多人批為不過是一種名不副實的營銷噱頭、是一種“偽低碳”行為,您怎么看?
賀強:是不是“偽低碳”我持保留意見,它們肯定有一點低碳元素,出于商業目的如此炒作,這種現象并不奇怪,節能環保肯定是低碳,但節能環保并不是低碳的全部,即便節能環保,企業還存在一個是否真正落實到實處的問題。
當然,我反對這樣的行為,這是企業的短視行為,想賺快錢,真正有戰略眼光的企業是不會這樣的。要制定低碳標準,加強監管,甚至完善這方面的法制。我考察了臺灣一家芯片廠,每個車間門口都掛著牌子——本生產流程能排放多少碳,通過某項技術能降低多少碳排放。你可以看到臺灣都落實到實處,在低碳方面,企業一定要自覺。
《新民周刊》:剛才您講的低碳,執行的主體,我把它分為了三類,國家、企業、個人,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您認為有哪些誤區?
賀強:我們已經過慣了高碳的生活,一定要養成自覺的低碳習慣,現在出現了所謂的低碳達人,當然也沒有必要像他們那樣,每個人只要適當改變一下生活方式,做到低碳還是很容易的。
我要強調的是,低碳與生活品質并不矛盾,有人說為了低碳從此不開車、不吃肉、少買衣服,走極端或者低碳秀,我看完全沒有必要,比如開車,你可以從一周開七天變為一周開五天、三天,在不需要開車的情況下,盡量選擇軌道交通或者騎自行車,這不就低碳了嘛。
比如抽煙戒不了,怎么辦?盡量少抽行不行?比如請客吃飯,別浪費糧食行不行?隨手關燈行不行?從一點一滴開始做起。
你會發現,只要你有心,完全可以在保證原本生活品質的情況下支持低碳。
《新民周刊》: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