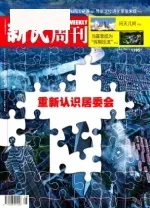兩會,一場房地產大會?
張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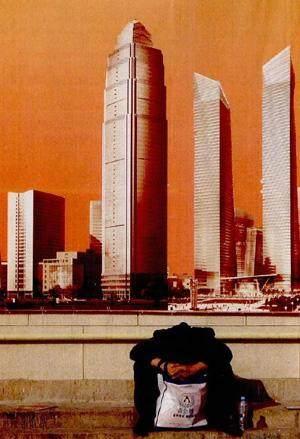

當人人都在為房子奮斗終生,這就不只是一代人的杯具。
黎叔在《天下無賊》中有一句名言:“21世紀什么最貴?人才!”如果放在當下,幾乎所有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房子!
2009年,突如其來的房價飆升,裹挾著一部火上澆油的《蝸居》,刺痛了全國人民的心。這讓今年兩會,幾乎毫無懸念地開成了潘石屹夫人所料的“房地產大會”。
任志強魔咒
“現在住房不是一般的民生問題,已經變成了第一民生問題。無論是上海代表團,還是我在兩會中接觸到的人大代表,對住房問題都很重視。”來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咨詢部主任張兆安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說。
雖然代表們不負眾望,但兩會究竟能帶來多少希望?
有句時評道出了在高房價的多年調教下,人們的某些慣性思維:“房地產的最大莊家是政府呢。想著房價降?刁民們做夢吧。”梁季陽委員在前兩天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么在房價下跌的時候,地方政府總會或明或暗地托市、救市?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地方政府是房地產交易中最大的獲利者。據統計,2009年全國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已經超過1.5萬億元,不少城市的土地出讓金已經占地方財政收入近50%。”
可以說本屆中央政府執政這7年,也是房地產宏觀調控的7年,與地方政府動態博弈的7年。
眾所周知,房改自1998年始。如果非要為這輪房地產狂熱尋找一個理由,最遠可以追溯到上世紀的那場金融危機,隨后房地產被賦予了“拉動內需、重啟經濟增長”的歷史使命。正如高房價也不是一年兩年了,今年像捅了馬蜂窩一般,也是因為一場突入其來的次貸危機,導致房地產變成了政府冀望重振經濟的“救命稻草”。歷史的某些相似性與輪回,總令人唏噓不已。
著名學者、獨立評論人袁劍講過一個故事:“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產崩潰之后被迫北上的朋友,憑著他對政策一貫敏感的嗅覺告訴我,房地產可能要轉勢了。隨后,他毅然重新南下,開始了一次極其成功的地產生涯。現在看來,這不僅是我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轉折,也是中國最近一次房地產狂飆的一個標志性的起點。”
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盛華仁說,1998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入不過為67億元,而從2001年到2003年,這個數字魔術般地漲了近135倍,變成了9100億元。在住房交易中,土地費用占房地產價格20%——40%,政府稅費收入占30%——40%左右。總計起來,地方政府在房地產上的收入占整個房地產價格的50%——80%。
袁劍有見地之處,是指出了在地方與中央的宏調博弈中,土地扮演了“過橋”的角色。在“朱镕基時代”,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權力幾乎被悉數上收。但由于批出的土地轉手就可以從銀行抵押貸款,實際上地方政府又重新從中央政府手上奪回了某種貨幣發行權力。
可以說,新一屆中央政府從2003年上任伊始,便接手了一座“活火山”。早在2002年,朱镕基已經不無擔憂地指出:“深圳的明天是香港的今天。”這已是他在一年中第二次發出警告:“內地部分城市的房地產過熱。”而央行在2002年年底的一項調查發現,房地產貸款中的違規金額比例高達24.9%。
以2003年6月央行出臺121號文件為分水嶺,中央政府對房地產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121號文件將全國的投資高增長歸罪于房地產,并認為泡沫是全國性的,是普遍性的。這一定調對房地產商來說不啻為“致命一擊”。華遠集團董事長任志強的反應最為激烈,一連起草了兩篇聲討“檄文”:萬言書《“冬天”來了》和《仇富政策》,潘石屹則是徹夜難眠。
然而一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121號文件,事后證明不過是一場“茶杯里的風波”。隨后國務院一紙“撥亂反正”的18號文件,再度令中國這一“新富階層”笑逐顏開。
據袁劍回憶,2003年年初,上海人見面寒暄變成了:“買樓了嗎?”而到了2005年初,一位投資界的朋友給他打電話的時候,劈頭就是:“不得了,上海人手上已經沒有現金了,全用來炒樓了。”
2005年3月16日,央行宣布取消住房貸款優惠利率,并提高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18天之后,新華社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加強宏觀調控穩定住房價格》,據稱用辭之嚴厲,只有《人民日報》那篇《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可與之相比。一個月后,傳說中的“國八條”正式出臺。不僅將房地產帶來的“金融風險”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而且繼新華社基調,指出地方政府必須對高房價負責。
然而現實的尷尬卻是,房價就像應了任志強魔咒一般,“政府越調房價越漲”。2005、2006、2007年,反而成為中國房地產最熱的三年。
“政府對房地產行業的宏觀調控從一開始就走錯了路。房地產的問題需要通過一個結構化的產業模式來解決,一部分完全市場化、一部分半市場化,還有一部分非市場化,政府在其中做好資源調配。讓有錢人住好房子、投資房產,帶動區域土地價值的提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產商都賺錢了,帶來一個負效應,房價會越來越脫離部分老百姓的購房能力。這時候,政府應該通過行政法規的規定,將土地出讓的溢價部分,拿出一半去做保障性住房。在推出的土地中,一定要有一部分不賺錢,或者微利,來做半市場化的普通商品房。”高策地產顧問機構的董事長李國平告訴記者。
“但反觀中央的宏觀調控,最初兩年的主要手段是抑制需求。每次短暫的觀望之后,都是開閘泄洪式的需求釋放。而另一方面,標志著房地產正式市場化的‘招、拍、掛制度,客觀上造成了土地供應的瓶頸,使得供求關系的進一步緊張。”
結構化的萌芽,在2006和2007年的房地產政策調控,曾經一度出現。“住房民生與保障終于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已經意識到調控不僅僅是調需求,還要調供應;不僅要增加供應,還要改善供應的結構。中央政府開始意識到在房地產產業中必須引入非市場化以及不完全市場化的補充模式,開始推出大力建設保障性質的廉租房和限價房的政策。其中對行業影響最大的則是2006年5月引發熱議的90/70政策,這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政策。”
當中央政府把所有的調控手段用盡,到2008年年底,在資金鏈緊繃的壓力下,降價、通過銷售回款自救,終于成為房地產全行業的共識。
“2008年底,深圳的房價下降了50%,北京一些地方下降了30%-40%。政府有了一次實現結構化運作房地產的機會。不幸的是,它沒有被抓住。”
李國平當時提出的觀點是:“政府應該救經濟,但不要救房地產。”中央政府應該正確引導那些優先獲取流動性貨幣資源的央企、國企,將4萬億主要用于保障性住房以及半市場化的普通商品房建設。一樣拉動上下游產業,為GDP做出貢獻。
然而真實的故事卻是,這一輪勢頭大好的調控,卻在接下來如過山車一般驚心動魄的市場震蕩和全球金融危機中戛然而止。“政府現在要來重新調整房地產的結構,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更高的代價。”“今年政府面臨著更為困難的局面。政府當初慌不擇路,一味放貸款。巨大的流動性轉變為央企的高價拿地,地方政府的投資運作平臺有了充裕的資金而失去推出土地的壓力。而高地價又帶來房價上漲的預期,使得開發商的降價迅速觸底反彈,短期內全面清貨解套。更何況去年地王頻出,很多開發商有錢了之后還拿不到地。手上有錢,存貨還不多。如果說2008年他們可以撐半年,這一次開發商起碼能撐一年,看誰熬得過誰。

所以我覺得今年的房價不僅降不下來,還會出現一個政府更不愿意看到的情況:觀望氣氛濃厚,交投兩淡,開發商還不著急,拿地意愿不強,GDP上不去,看你政府怎么辦。現在連王石都說了:我們可以慢下來。政府不敢讓房地產垮。這是任志強唯一看到的正確的東西。等到了下半年,政府一看形勢不對,一定會重新來刺激房地產。今天政府所議的所有難題,都是它自己一手造成的。”正如一位網友調侃:“在一個意外的牛年之后,管理層已不得不騎在虎背上。”
自古降價一條路?
房價飛漲在部分社會成員中間激起不滿。為了應對憤怒的滔滔民意,宏觀調控的主旋律基本上都圍繞著“打壓房價”進行。
2月27日,溫家寶總理在北京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表示:“我有決心,本屆政府任期內能把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價位。”
民間也有類似的心聲:“房價不降,天理難容!”“哪個地方政府支持高房價,就要嚴查哪個。”
然而解決中國房地產難題,是否只有“降價”這條硬道理?
“整個房地產市場,不是一個簡單的市場化行為,也不是一個簡單的非市場化行為。現在等于前面全部市場化,發現出問題了,又開始提出全部非市場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李國平說。
時至今日,中國早已出現了利益分化。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幾乎所有的已購房者,這些年都分享到了房價暴漲的盛宴。“我身邊很多朋友對于房價其實看法都各不相同。買了房或者手里有兩三套房的人其實希望房價漲,從中投資的收益能夠得到更大化的提高,還沒有買房的希望房子不要漲。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結構性的看法。”新浪財經的主持人權靜說。
“我不希望房價跌,因為我剛買了房子,打壓房價不是讓我的房子資產縮水嗎。”一家房地產機構即將履新的區域經理也坦言相告。
“讓市場的歸市場,讓政府的歸政府。”房地產兩條腿走路,愈來愈成為一種共識。“大家所感受到的矛盾焦點是高房價,但實際上真正核心的問題是不是房價太高了,而是有很多人買不起房,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假設如果說中國的房價再翻一倍,但是所有的老百姓自己都有房子住,我想今天房價的問題就不會成為社會的一個矛盾的焦點。”北京聯達四方房地產經紀公司董事總經理楊少鋒說。
調控房地產的政策,從去年12月初就開始陸續出臺。作為對“國四條”的細化與完善條例,“國十一條”似乎是2005-2007年間已經開始萌芽的多元化思路的重新出發:實現房地產在國家戰略上的雙重目標,既拉動增長,又保證“居者有其屋”。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贠小蘇也在私下透露,2006年出臺但未能堅持的“90/70政策”將在不久后回歸。
“今年中央準備財政補貼600多個億建保障性住房,我認為去年做得那么差,今年只增加百分之十幾,能根本性改變問題嗎?另外,去年地方土地收益的溢價部分就已經有3000多個億,拿一半出來做保障型住房都是應該的,為什么只拿10%?明顯的雷聲大雨點小。”李國平認為。“去年年底開了兩次會,主要定調者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三強調進一步鼓勵住房改善性需求,目前最大的任務是調結構。但此后到了國務院層面,會議精神變成抑制投資性需求,到現在已經演化為要抑制改善性需求。由此可見,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找到一個系統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如果無法形成合理的政策和結構體系,房價上漲和解決大多數居民住房問題的矛盾,無疑會越來越激烈。這讓我們對于這一輪調控政策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很難有一個樂觀的預期。”
“被房子垮掉的一代”
住房保障體系,到目前為止僅覆蓋到了低收入階層。而這屆“房地產大會”一個亮點,便是集中關注到了“夾心層”,不知這是否拜《蝸居》所賜。
張兆安認為:“中國的住房結構,實際是一個橄欖形。最上端,更多通過市場化手段解決。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兩限房,主要是解決橄欖的最下端,政府一定要把對這部分人群的“托底”先做好。現在麻煩的是中間這一段該怎么辦?”
中央智囊團在這個問題上顯然啟動得更早。2009年8月13日,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淮以個人身份表示,“十二五”期間(2011年-2015年),在基本解決了低收入群體住房的問題后,住房保障體系重心應適度上移,我國救助型住房保障要逐步提高到有一定能力和工作收入,但是其收入和買房子差距非常大的群體。
《蝸居》之后,《蟻居》大熱,80后有了一個新稱號“被房子垮掉的一代”。一年飆升80%的房價(據統計局數字),更讓一部分原本可以夠得上商品房的“邊緣人”,重新退回到無房者的大部隊。
當人人都在為房子奮斗終生,這就不只是一代人的“杯具”。“如果我們國家的年輕人都沒有安全感,都不能有歸屬感,這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是有問題的,我們正丟失最核心的競爭力。”李國平說。
楊少鋒認為:“中國房地產行業借助銀行,扮演了一個向中產階層掠奪財富的角色。房價如果繼續漲下去,最終的結果是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目前房地產的繁榮是以未來20年的發展為代價。”
從2007年開始,北京開始建立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限價房、公共租賃房在內的多層次的保障性住房體系,已完成配售的5萬套經適房、限價房和累計通過審核申請的11萬戶相比,比例基本是1:2。
地方政府顯然是缺少積極性。全國政協委員、武漢百步亭集團董事局主席茅永紅提供的數據顯示稱,目前在全國城鎮的低保家庭中,各級政府已通過各種方式緩解住房困難的僅占7%左右;在全國已開展廉租住房的城市,其覆蓋面僅在1%左右(個別大城市除外)。
而在執行的細節上,也存在“一刀切”的現象。
李國平透露:“現在保障性住房是地方政府不得不做,做的時候亂做。90/70這么好的一個政策,卻在執行細節上出現了致命的錯誤,許多土地根本不適合做90/70。廣渠路15號地,里面還要求配一萬五的廉租房,這是一個典型的幾方傷害。土地價值可以更高的,現在做不上去;在CBD建廉租房,人為增加了低收入群體的生活成本。本來是政府行為,轉嫁給了開發商,又是一個政府的不作為。”
保障性住房的高門檻,也把夾心層拒之門外。以北京市為例,申請廉租房的一人戶家庭月收入為580元及以下,申請經濟適用房家庭月收入約為1890元。既買不起商品房又不符合經濟適用房申請條件的“夾心層”,正處于“舅舅不疼,姥姥不愛”的尷尬。“由于整體立法的滯后,住房保障誰來保?保多少?怎么保?保障房怎么造?造多少?給誰造?怎么分?政府、民眾、企業,各自有哪些義務和權利?有哪些責任和收益?現在都沒有一個權威的依據和標準。”帶著《國家住房保障法》議案進京的張兆安呼吁,要盡快將國民住房保障納入國家法制化的軌道。
在他的提案中,公共住房制度,也就是李國平所言的半市場化的普通商品房,體現了兩處亮點:“公共住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的供應對象不受戶籍限制”、“國家將房價收入比作為城鎮中等收入家庭住房狀況考核的重要依據。以戶型建筑面積90平方米為參照,一線城市須控制在8倍以下,二線城市須控制在7倍以下,三線城市須控制在6倍以下,小城市和建制鎮須控制在5倍以下。”
如何防止“經濟適用房經濟了誰,適用了誰”的悲劇不再重演?全國兩會期間,由政府和住戶“共有產權”這一制度設計引發了強烈關注。張兆安也在他設計的《國家住房保障法》提案中提出:“經濟適用住房不得作為商品住房上市交易,若出售須由地方人民政府回購或在指定的經濟適用住房交易平臺進行交易,售價不得高于當地政府確定的該樓盤公共住房最高限價,購買對象僅限于符合購買經濟適用住房條件的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經濟適用住房出售后5年內不得再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