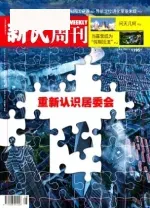麻省理工女校長:中國是金礦
金姬 陳文俊

每個月,MIT開放課程網站有上百萬訪問量,其中21%來自中國,可見中國學生旺盛的求知欲。
這個夏天對于59歲的蘇珊·霍克菲爾德(SusanHockfield)博士而言非常忙碌,這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校長在上任5年半以后第一次如此長時間地訪問中國——8天內與北京、上海、香港和臺北的政商學界密集會晤。她上一次以MIT校長身份來中國演講還是2006年,當時中國只是她“亞洲之旅”的一站。
對于MIT而言,中國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過去20年,有5000名中國學生在MIT就學。而在MIT今年招收的1萬名(本科4000人,研究生6000人)學生中,就有近500名來自中國。霍克菲爾德對中國生源也是贊譽有加:“中國學生之前的準備、學習精神和才華讓他們進入MIT后繼續保持優等生的狀態。”霍克菲爾德在向廣大中國聽眾傳播MIT理念的同時,不時對這個崛起的東方大國給予高度評價,因為在她看來,“我們與中國各界越來越多的合作至少可以在三個方面進一步推動MIT應對人類的巨大挑戰,幫助恢復可持續的、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增長。”
百年中國緣
當霍克菲爾德在上海外灘三號“三言舍”活動上做演講時,她的嗓子已經因為連日勞頓而有些沙啞和咳嗽,但這沒有影響她與中國聽眾“套近乎”,霍克菲爾德開門見山地表示:“其實,MIT和中國人民算是老朋友了。134年前,第一批中國學者去了MIT。他們在MIT學習數學、采礦、化學和機械工程。”也許是巧合,霍克菲爾德在上海說出這些話時,這座遠東第一大都市正在舉行2010年世博會;而1876年第一批中國學生來到MIT時,那時的美國恰逢建國100周年,留美事務局的清朝官員帶領平均年齡12歲的113名幼童參觀同年在費城舉行的世博會,引起西方轟動。其中,來自廣州、廈門、澳門和上海的8名幼童鄺詠鐘、方伯梁、鄺賢儔、薛有福、宋文翙、鄺景揚、鄧士聰、楊兆楠進入位于馬薩諸塞州波士頓(1916年遷往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當時清政府稱為“波士頓機器大書院”)學習,當時這所私立高等學府剛剛招生11年,在自然科學和工程領域獨樹一幟。
“自此之后,很多中國畢業生無論留在美國還是回到中國,都發展得非常好。”霍克菲爾德舉例道,“1930年代,李郁榮(后為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與MIT知名教授、控制論創始人諾伯特·維納(NorbertWiener)一起進行開創性研究;錢學森從我校獲得博士學位后成為MIT歷史上最年輕的全職教授。他是美國NASA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創立人之一,后來又創立了中國的太空項目。”
改革開放以來,MIT加強了與中國高校的雙向交流。例如15年前,與復旦大學開始合作的中國-MIT管理教育項目,外灘三號主席林美金女士也是該項目領導委員會成員。最近,MIT又與上海交大開展中國制造業領袖項目的合作,通過該項目,中國的政府、企業和學術領導前往MIT,深層次了解當今世界能源和環境挑戰。
以人為本
有人稱MIT為“瘋癲精神病院”。對不知內情的人來說,第一印象或許如此。然而,MIT的最成功之處在于它獨特的教育方法,“最基本的注意點是研究,即獨立地去探索新問題”。例如,有一門課是這樣進行的:學生們每人得到一個裝滿彈簧、電機等元件的箱子,課程要求簡單而明確——自行設計、裝配一臺機器。恰恰是這種奇異、怪僻、與眾不同的環境,造就了一大批獻身教育事業、頑強拼搏且成就卓著的科學家。也正因如此,才使MIT成為全世界有志青年衷心向往的“麥加圣地”。
霍克菲爾德認為,研究和教育的根本還在于個人。MIT與中國的很多合作是在“個人”這個更小的規模上展開的。其中有一個合作要歸功于33位中國出生的MIT教職人員。中國建筑大師張開濟的孫子、建筑大師張永和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上海世博會企業聯合館的設計師,霍克菲爾德在上海參觀世博會時特別去看了張永和的作品。“另外還包括我們代表團成員、MIT最大的研究中心電腦科學與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舒維都(VictorZue),大腦研究項目先驅MITPicower學習和記憶中心主任蔡莉慧以及眾多其他教職人員。”此外,現在60多位MIT教職人員在研究城市規劃、經濟學、能源、云計算和認知科學時,都將中國包含其中。
4年前,MIT斯隆商學院畢業生、來自中國香港的唐裕年(Martin Tang)成為第一位不在美國的MIT校友協會主席。唐裕年的爺爺唐星海和父親唐驥千也都是MIT獎學金獲得者,唐家三代共有90年的MIT求學歷史。
MIT仍然是許多中國學生的“求學圣殿”,每年有限的招生名額似乎已經不是問題。霍克菲爾德表示:“在21世紀,MIT又有了另外一批學生,他們可能永遠都不會親自前往MIT校園。很多中國學生通過MIT的開放課程領略MIT。學生通過開放課程可通過網絡免費獲得MIT超過1900項科目的材料。每個月,開放課程網站有上百萬訪問量,其中21%來自中國,由此可見中國學生旺盛的求知欲。”
對話MIT女校長
《新民周刊》:美劇《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在中國很流行,雖然劇中提及的是加州理工學院(就是唐駿“博士”最近牽扯到的那所學校)的4位理科男,但是似乎對于理科生來說很有代表性。不知MIT的學生是什么樣的?
霍克菲爾德:我沒看過這部美劇,但是我想說的是人們對理科院校可能有些誤會。例如以為理科生多為男生,其實在MIT的本科生中,有45%是女生;另一方面,理科生不是“書呆子”,MIT的學生然成績優異,但是他們必須要熱愛學習,而且必須文理兼通,興趣廣泛。例如,MIT的很多學生都是音樂愛好者。作為一名關注大腦發育的神經科學家,我本人也是波士頓交響樂團監督員。
《新民周刊》:二戰以來,MIT校長或多或少會充當美國總統的智囊角色。不知您從2004年12月就任以來,是否也給白宮建言獻策?
霍克菲爾德:和許多美國高校校長一樣,我每個月都會抽一天去華盛頓。其實不僅要和總統等在任官員打交道,我也要和在野黨處好關系。例如2008年美國大選期間,我就去了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競選總部,讓他們了解科學和技術對于美國未來的重要性。MIT在1861年成立之初是為了加快美國工業化,而現在則是最先提供科學和技術教育,為年輕人今后發明創造做好準備。奧巴馬總統推崇的能源研究,就是部分采納了我的觀點。
《新民周刊》:多數經濟經濟學家認為,二戰之后的半個世紀,美國約一半的經濟增長都是技術進步的直接結果,而很多技術成果都來自于大學研究。MIT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霍克菲爾德:MIT和多數大學一樣,將培育和傳播新知識作為自己的使命之一。但是,MIT的獨特之處在于,我們也將培育創新和創新的人作為自己的使命。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如今在世的MIT畢業生共建立了約25800個現在很活躍的公司。這些公司在世界各地共雇用員工330萬名,產生年收入約2萬億美元。無論是從事制造業,還是生物技術、軟件、咨詢,很多公司在新科學、新技術和新工程方面都做出了一定貢獻。
《新民周刊》:MIT為何如此重視與中國各界的合作?
霍克菲爾德:首先,中國提供了一個了解世界最棘手的技術問題的獨特視角;其次,中國將繼續涌現一批最棒的解決方案。現在中國在超高壓電網傳輸和高強輕型鋁摩天大樓方面已有很多進展。將來能源、公共衛生和電子通訊方面新的技術、新的解決方案將首先誕生在中國;第三,中國將涌現更多的合作者和同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數據顯示,1993年中國獲得科學和工程博士學位的人數為2000,2006年就增至22000。在不久的將來,中國高質量博士生人數將超過美國。此外,1995年到2007年間,中國的英文科學論文數量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長。
最終MIT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必須與中國各界緊密合作。解決當今全球的問題必然牽涉到解決中國的挑戰。因此,我們希望MIT能在中國建立最重要的全球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