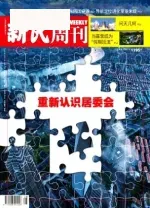開征新稅,誰說了算?
李煒光
眼下,物業稅已成待發之箭,街頭巷尾、廟堂之上,大家都在談論著這個稅啥時候開征,會不會引起房價下跌之類的話題,不過還很少聽到有人問上一句:這樣一個涉及億萬家庭私人財產權的新稅說征就征了,其間是不是有什么問題被忽略了?
憲法學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國家稅收直接關系到對納稅人的自由和財產權的限制或剝奪,凡涉及可能不利于國民或加重其負擔的法律規定,須由人民選舉出來的立法機關制定,而不能由政府單方來決定。因為政府既是稅收利益的獲得者,又是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務的執行者,如果僅依照其自立的行政法規來規范其征稅行為,可能會導致其征稅權力的不合理擴大和提供公共服務義務的不合理縮小,故必須以法律約束之,以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僅僅是可能性。這是當今世界各國的稅收立法機關大都嚴格保留稅收立法權的理由。
這就是說,開征新稅——物業稅更不應例外,應嚴格受制于立法程序,凡未經立法的稅收,就不具有合法性,任何行政機構、任何人,不管權力有多大,都不能例外。
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理論上說,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就應該代表全國人民當家理財,像稅收立法這樣的大事,理應由人大開會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這是我國《立法法》明文規定的條款,稅收立法權自然也屬于我國立法機關的專屬權力。顯然,即將開征的物業稅,應該走在這樣一條法治的必經之路上。
可現實情況卻不很樂觀,雖有憲法規定,又有《立法法》作保障,我國的稅收立法卻時常受到來自行政權力的干涉,難以實現自主立法。目前的20多個稅種,經全國人大立法的只有《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和《稅收征收管理法》等三部,也就是說,85%以上的稅法是由政府機構自我授權,以條例、暫行規定等行政法規的形式頒布實施的,而人大卻被撇在了一邊。這種狀況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已經維持既久,一直未能加以改變。這說明,除了憲法和法律之外,我們國家還有另外一套"規則"存在,且運作自如。
不僅如此,很多時候一些實施細則之類的制定權還被轉授給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較低層次的政府部門,如2007年和2008年兩次對印花稅率的調節,即是由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自行實施的。推而論之,如果需要,政府想征多少稅都可以做到,中間沒有任何制約和監控的政治環節,長此以往,會演變成這樣一個結果:政府每年的預算都需要拿到全國人大去審核批準,而政府決定新征稅種或提高稅率卻不需要全國人大來批準,人大成了只管出、不管進的權力機關。
稅收立法權的轉授不是不可以,但有以下幾點不應忽視:第一,授權應該是具體、細致的,凡涉及稅率調整幅度、行使方式、立法程序等,一項一項具體進行,認真討論、聽證,不能給人一種“你看著辦”的感覺。未經過這些必要程序的授權,等于權力的放棄。第二,在權限上應當有個明晰的邊界,如授權的時效性,何時執行,何時終止等等生效條件,都應該做明確規定,不能給人以“隨便怎么都行”的感覺。須知,無界限的授權也等于權力的放棄。第三,權力既然可以授出,也應該可以收回。如果不能收回,或不得不授予,只能說明那個權力原本就不在你手里。
目前,我國應制定一部稅收基本法,將稅收事項集于一部法律中予以確認,以統領、約束各稅收單行法;應杜絕行政機關自行添加新稅種的做法,讓設立新稅的權力回歸到人大及其常委會的責任和掌控之中;應在憲法的框架之內轉授稅種及其細則的制訂權,且這種授權應當是具體和細微的。也就是說,今后在新稅種的開征問題上,除了國家立法機關的正式立法外,一切文件或規章都不算數。
應該說,目前我國人大的改革還是個相對遲緩的領域。人大開會,本是對政府一年來工作的審查,卻變成了只是對《政府工作報告》的審議。代表們經常放著開征新稅這類人們更關心的話題不說,卻花費大量時間暢談“大好形勢”。由于選舉制度存在弊端,個別代表素質較低,影響了自身形象。人們期待著,今年的人大開會,這一切能否有所改變?(作者為著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