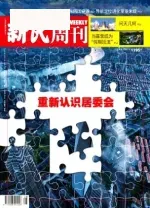誰為地方治理的潰敗買單?
夏佑至
礦難之后還有礦難,爆炸之后還有爆炸,決堤之后還有決堤,塌橋之后還有塌橋,警察打人之后還有警察打人,報復行兇之后還有報復行兇。夏天的天災人禍如此頻仍,不怕重復,先是讓人緊張、焦慮,接著讓人感到無奈和無力,終于變得麻木起來。
這些災禍無不和地方治理的敗壞有關。以6月被大水沖垮的江西撫河唱凱堤和7月被大水沖垮的河南欒川湯營大橋為例,前者作為江西省撫州市最重要的圩壩,多年受困于防洪標準低,整修堤壩年年見諸當地政府工作計劃,但因為地方財政無力承擔整修所需的費用,修繕計劃不過是一紙空文。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為撫河堤壩,撫州城區一段的“景觀工程”、“亮化工程”投資就高達3000萬元。面子工程不能當飯吃,大水一來,唱凱堤決堤300多米,導致下游4個鄉鎮10萬人受災。
地方官員漫不經心的態度和馬虎了事的作風十分相似。河防與交通關系國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并不足以讓他們投入更多的關注。毫無例外,他們感興趣的總是事情的表面。湯營大橋位于河南洛陽的欒川縣,已經于2009年發生過一次垮塌。和撫州市的“景觀工程”如出一轍,欒川縣政府沒有對這座危險的橋梁加以根本修繕,只是重鋪了柏油路面,加裝了漢自玉欄桿。7月底,大橋在大水沖擊下垮塌,死者超過50人,還有數十人失蹤,至今未能尋見。
這些悲慘的事件背后是體制性的運轉不靈。在農業中國,用來形容治世的成語是“海晏河清”,用政治術語說,即有效地治理水患,是衡量政府治理成效的標準;水利是政府對國民的政治承諾,是政府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患導致人民失去生計,流離失所,往往是王朝更替的前奏。在現代,治水仍然是衡量政府治理成效的標準之一,但不再像農業時代那樣是最高標準,其優先性排序不僅落后于創造GDP,落后于“維穩”,甚至落后于“景觀工程”和“亮化工程”。90年代初的分稅制改革之后,治水還涉及到政府間財權和事權的分配。大江大河的治理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諾,撫河這種區域性河流,是撫州市的地方事務,無法得到中央資金的足夠支持。同理,2008年以來用以刺激經濟的數以萬億的政府投資,催生了新一輪交通建設熱潮,各地“鐵公雞”(鐵路、公路和機場的縮略俗稱)紛紛上馬,卻絲毫不能施惠于湯營大橋——究其原因,湯營大橋雖然也有一個“大”字,卻偏于一隅,只是一座小小的鄉村橋梁。屬于欒川縣的地方事務而已。
地方事務的支出主要應由地方承擔。如果地方財政不足以支撐治水或修橋的需要,地方政府要么向省級和中央政府申請資金,要么就只能因陋就簡——正如唱凱堤的情形。可怕之處在于,“跑步錢進”和“面子工程”并行不悸,用于治水的資金劃撥到地方之后,也沒有用于治水。這是地方官員的一場豪賭。賭的是任期內不會決堤,不會塌橋。賭注卻是百姓的身家性命。
其結果,水利部部長陳雷提供的數據是,一般年份中小河流洪澇災害損失占全國的70%~80%,死亡人數占壘國洪澇災害死亡人數的2/3。
決堤和塌橋顯示出地方治理的潰敗,誰來埋單呢?財政收入作為權力,可以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分割,公共事務作為義務,也可以在中央和地方之間進行分割,但權力和義務是對等的。通過控制財政收入,中央控制地方的能力大大加強,也隨時要為地方治理的潰敗買單。
所以,修建、維護唱凱堤和湯營大橋的法律責任在地方,堤壩決口和塌橋的政治責任卻在高層。其實,決堤對地方政府來說,既是風險,也是機會。因為決堤之后,相關權力就可以重新劃分了。洪水退去后,撫州政府宣布,將按照50年一遇的高標準重建唱凱堤:壞事就這樣變成了好亭。此前治水不力的責任一筆勾銷,接下來的重建加固勢必有上級財政埋單。這是所謂“富中央、窮地方”的政治安排的必然結果。
唱凱堤和湯營大橋的故事并不是第一次上演,恐-怕也不會是最后一次。中國有幾萬條區域性河流,在這些河流之上,湯營大橋這樣的橋梁更加不計其數。地方治理的質量決定著堤壩會不會決堤,橋梁會不會倒塌。而只要事權和財權不對等的局面不變,只要財政資金的使用得不到監督,地方治理的改善就遙遙無期。為之埋單的是中央政府,也是生活在危堤和危橋之側的萬千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