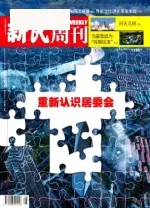《華爾街2》難續輝煌
王倩


就好像電影里的高登所說的,我以前總是說貪婪是好事情,現在貪婪已經是游戲規則了。真是這樣,人們把貪婪看成了精明和智慧。
戈登沒變,華爾街變了
2001年,戈登刑滿釋放,走出了聯邦管教所的大門。當年他因為證券欺詐和不法牟利等多項罪名入獄,現在他已經不再是華爾街之王,蓬頭垢面,一頭亂發,沒有人為他接風,孑然一身,成了金融界的局外人。
這是《華爾街2:金錢永不眠》的開頭一幕。戈登是上世紀80年代好萊塢電影為金融業創作出的最著名的虛擬人物,是美國文化中歷久不衰的人物,也是大銀幕上最被人記得住的壞蛋之一。他的名言“貪婪不好聽,卻是好東西”即使到了2007年,還在“最偉大的100句臺詞”評比中排名第70位。“貪婪,抱歉我找不到更好的詞,貪婪是好事。貪婪是對的。貪婪是有用的。貪婪可以闡明一切,披荊斬棘直搗演化的精髓。貪婪存在于一切的形式上——對生活,對金錢,對愛情,對知識的貪婪——貪婪激發了人類向上的動力”,奧斯卡影帝邁克·道格拉斯在《華爾街》里的這段演講至今都是電影史上的名言,而且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貪婪是好的”這句戈登名言更是經常性地出現在媒體上,人們輕易忘不了戈登——大導演奧利弗·斯通在1987年的《華爾街》中塑造的一個壞蛋。
《華爾街》里,曾經翻云覆雨的股市大亨戈登不擇手段地操縱股票行情,最終敗在了一位依然具有些許良知的年輕股票交易員之手,鋃鐺入獄。邁克·道格拉斯因此片獲得了奧斯卡影帝,這之前他通常飾演愛情片或者喜劇片的男主角,這是他第一次演一個壞到骨子里的家伙,“在我演過的眾多角色之中,人們最常跟我提到戈登。戈登讓他們印象深刻,這點讓我很驚訝,因為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壞蛋!”
反面角色拿到奧斯卡可能不稀奇,稀奇的是,戈登的個人魅力,他在交易時趕盡殺絕的作風,還有累積財富時毫不留情的做法,都意外讓他成為現實社會里許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和金融界的傳奇。華爾街的年輕人不只留起了戈登的招牌長發,穿起吊帶褲,更重要的是,他們打從心里相信戈登的名言“貪婪是好的”。戈登在報紙跟雜志的文章中出現的次數太多,已經變成了一個指標性的角色,而奧利弗·斯通在《華爾街》里造出那個金融中心里的文化——不管在行為或是穿著上,它實際上真的對在那里上班的人形成了一定的影響。
直到今天都有人在問斯通,觀眾這么熱愛戈登這樣一個壞蛋是否讓你意外。最初幾年他驚訝不已,而等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他更是發現,“過去這幾年,這部電影似乎越來越受歡迎。我把《華爾街》當成一個道德寓言故事在拍,結果卻是很多人都誤解了它。多年來不斷有人跑來跟我說,我到華爾街工作都是因為看了你的電影,這真的很神奇。很多人現在都已經三四十歲了,而且在華爾街做得不錯。”
貪婪沒變,貪婪的人變了,以前的那樣一個戈登在現在看起來已經微不足道。拍完《華爾街》后的23年里,全世界發生了自1931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海嘯,金融大亨也變得越來越有錢,“我覺得最夸張的就是這些財富累積的速度,從90年代到現在,這些數字不斷飆漲,幾百萬變成了好幾十億,而貪婪的戈登被貪婪的銀行徹底擊垮。”奧利弗·斯通說。
到了2008年時,戈登這樣的人已經沒辦法生存了。那種海盜般的人物已經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過去曾經謹守本分的金融機構。過去銀行是銀行,保險公司是保險公司,不過這一切都慢慢改變了。隨著金融開放,這些不同功能之間的防火墻一一垮下,這就是《華爾街2》和《華爾街》相隔23年里的金融世界。
連續三部電影《亞歷山大大帝》、《世貿中心》和《小布什傳》反響不佳后,奧利弗·斯通一直鉚足了勁在尋找各種題材,韜光養晦。2009年他讀到了擁有交易員執照的編劇阿倫·勒布(Allen Loeb)所寫的劇本之后,有了拍攝新《華爾街》、讓劇中人物卷土重來的想法。于是,戈登出獄了,8年后他出了暢銷書《貪婪不好嗎?》,正在美國四處巡演,他告誡臺下的“三無一代”(無財產,無工作,無未來),投機客猖獗,過度舉債的惡質金融系統,將帶著美國經濟走上絕路。戈登還會成為青年人羨慕的偶像嗎?
戈登變了,奧利弗·斯通也變了
阿倫·勒布最初寫《華爾街2》劇本時,奧利弗·斯通并未介入這個電影項目,道格拉斯已經表達了重新飾演戈登的意愿,但前提是劇本要好,所以交給阿倫·勒布的就是如何為戈登定調——出獄后的戈登會改頭換面嗎?這回他是贏家還是輸家?——總之,戈登要讓道格拉斯點頭,現在他不再是好萊塢的毛頭小伙子了,演砸一兩回無所謂,影帝自然有高標準,包括角色的道德觀。最終打動道格拉斯的是一個感人的家庭故事:戈登在獄中多年后不但改頭換面,也變成了遠離華爾街的局外人。
太太跟他離婚,兒子過世,女兒薇妮不搭理他,因為她認為全家分崩離析都是戈登的錯。邁克·道格拉斯說,“戈登在前一部電影里意氣風發,現在他在這部影片一開始卻如此慘淡。”戈登努力想重建自己在華爾街的地位,他還想讓家庭團圓,贏回女兒的愛,哪怕中間過程稍顯那么點兒缺德。
影片的結尾是如此“美好”,以至于很多人覺得這樣的結局欠缺邏輯,顯得劇情非常地“二”。劇中主創曾多次說過,希望《華爾街2》引起的反響能比20年前更多,但從目前的市場反應來看,似乎并沒如愿,反而有金融人士覺得對華爾街的描述不真實,要知道1987年的《華爾街》對每一個華爾街老鳥來說都逼真得不得了,很多人覺得奧利弗·斯通老了。
80年代華爾街的一切對奧利弗·斯通來說是熟悉的,他的父親就曾經是華爾街上的一名股票交易員,在《華爾街》上映一年前去世。當時市面上并沒有太多的商業電影,做了一輩子交易員的父親也常說市場上沒有好的金融電影。于是在1987年《野戰排》為其贏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項后,斯通把鏡頭轉回國內,拍一部金融叢林里的戰爭,“我是紐約人,我想回到家鄉,回到原點,觀察華爾街動態,希望拍出一部讓我老爸引以為傲的電影。”
《華爾街》的靈感其實來自于斯通為《疤面煞星》(1982年)寫的劇本,“故事發生在邁阿密,里面充滿了拜金主義、貪婪和可卡因,最讓我詫異的是整個佛羅里達州都是年輕人在賺大錢。回到了紐約,發現那兒也是年輕交易員在賺大錢。在我爸爸那個年代,年輕交易員還在慢慢往上爬,他們還沒辦法賺大錢,所以這種現象很新鮮,我想,太好了,拍成電影一定很有趣。”
《華爾街》成功后,奧利弗·斯通又回到了熟悉的越戰題材,“越戰三部曲”(《野戰排》、《生于七月四日》和《天與地》)和《刺殺肯尼迪》等政治題材電影一舉奠定了他一流大導演的地位,并把對政治和戰爭的鮮明觀點打造成自己的性格標簽。到了2000年后,奧利弗·斯通一直繼續著政治題材電影的探索,但人們對他在電影里的表達逐漸冷淡了,譬如《世貿中心》和《小布什傳》都沒有取得好的票房和口碑。可以說,奧利弗·斯通回到金融街,重新找回戈登這個人物,既合乎情理,也略顯悲涼。尤其是他最終給了戈登事業家庭雙豐收的好結局,很多人認為他不再那么銳利,也沒以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了。
奧利弗·斯通肯定不會接受這種說法,“我想我可能是更寬容了,但它的結局對我還是有同樣的意義。電影仍然以華爾街遭受重創結尾。可能大家認為以前的我更犀利、更有批判性,但我認為現在的我視角更寬廣,那些泡沫和不幸一次又一次地發生,但生活依然繼續,我們總得熬過去。人性是貪婪的,這使我們坐在一輛失控的列車上,面對一個瘋狂的世界。華爾街的心態已經變成了一種賭場的心態,這種心態也影響著大眾。我們喜歡貪婪,就好像電影里的高登所說的,我以前總是說貪婪是好事情,現在貪婪已經是游戲規則了。真是這樣,人們把貪婪看成了精明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