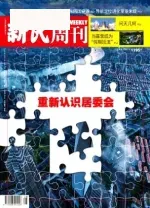托爾斯泰在中國:一個世紀的“托兒”?
河西
時過境遷,在社會主義思想摧枯拉朽般歷史推車面前,無政府主義很快成了過眼云煙,可是托爾斯泰并未就此過時,他似乎變得更為復雜,在他長老般的濃密虬髯下,那博愛如圣徒般的心靈,如大象般緩緩走過一百年的塵埃。
幸福的考生都是相似的,不幸的考生各有各的不幸。
2010年,一篇山東省高考0分作文題目在網(wǎng)上流傳,題目叫《托爾斯泰是個托兒》。不管今年11月20日正好去世100周年的托翁是不是真是個托,這位考生拿高考和托爾斯泰來抨擊中國當下的教育制度,至少證明,李戡也不是臺灣地區(qū)的專利,你看他寫得有多么激憤:“沒錯,托爾斯泰就是中國教育馬面換牛頭的托。但換來換去,頂多就是要么一個禽,要么一個獸。”
如果這位考生不是拿青春來賭明天,就是對中國教育已經(jīng)深惡痛絕到了不吐不快的程度。其困獸之掙扎的內(nèi)心,托翁在天之靈當可明鑒。想來托爾斯泰也不會見怪,冒犯一次而已,在《復活》前引《馬太福音》的文字中,耶穌不是對彼得說:他要饒恕得罪他的人到七十個七次嗎?
念安娜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在中學課文中刪了些魯迅,多了托爾斯泰、蒙田、帕斯卡爾、海明威、海子和余華,使思想和文本變得更為多元(雖然很多還不是必讀篇目),這本是好事,怎么又跳出許多橫眉冷對的“托兒說”來了呢?
真的是十年如一日換湯不換藥嗎?李戡出了龍?zhí)队秩牖⒀?亦可一哭矣!
連格非這樣的作家都沒搞明白安娜?卡列尼娜為什么一定要自殺不可,這篇《安娜之死》的節(jié)選課文卻赫然出現(xiàn)在人教版的高中教材中。前不見奧布朗斯基公爵家的混亂,后不見卡列寧的所謂虛偽冷酷和醉心仕途。斷章則取義,估計從教師到學生,都只能人云亦云,倘不能學一點安娜“私奔到國外”的本事,也只能“念安娜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安娜已成往事。2010年7月18日上午10點,85歲的謝素臺躺在病床上,身體逐漸失去了溫度。在托爾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的年份里,這位1950年代被周揚叫來一同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的翻譯家,終于安詳?shù)亻]上了雙眼,一個屬于安娜和謝素臺的時代隨風而逝,令人不勝感慨嘆息。
署名周揚和謝素臺合譯的《安娜?卡列尼娜》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人,事實上這本書周揚在30年代就已經(jīng)翻譯完成了。1938年的益陽,周揚夫人吳淑媛收到了丈夫托一位女共產(chǎn)黨員從延安輾轉(zhuǎn)捎來的禮物:《安娜?卡列尼娜》,周揚譯本。吳淑媛一邊讀著《安娜?卡列尼娜》,一邊給丈夫制作他喜歡的甘草梅子,這已經(jīng)是第四壇了。還有一件紫紅色呢外套,給他的長子周艾若。那些年的冬天,周艾若就穿著它在桃江、修山腳下外婆家到處玩耍。兩年后,外婆去世,吳淑媛悲痛欲絕,每天拉著還年幼的周艾若,半月中,天天,走很長的路去墳前哭訴,如果此時有周揚陪在她的身旁,有一個可以依靠的肩膀,也許可以解除一些她心中的苦楚。但是此時,她的身邊,在風中,只有一冊《安娜?卡列尼娜》。
解放后,周揚有時間重新審視自己的婚姻和早期譯稿。他對自己的翻譯并不滿意,于是他從中宣部資料室調(diào)來了俄文頗佳的謝素臺,幫助他翻譯《安娜?卡列尼娜》,主要是對早期譯稿的修訂,改正錯誤和使文字更為通順。草嬰說周揚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從英文版譯來的,只說對了一半。最初周揚確實是從英文版翻譯了《安娜》,但是謝素臺參考了蘇聯(lián)俄文原本,此稿又經(jīng)著名俄文翻譯家蔣路全面校訂,一個英譯本能成為傳世之作,譯者所下的功夫,亦可想見。
誰能理解托爾斯泰?
周揚并不是第一個翻譯托爾斯泰的中國人,托爾斯泰、莫泊桑、屠格涅夫等人的小說都曾出現(xiàn)在《新青年》上。商務印書館于1921年出版了共學社叢書,皆為俄國文學翻譯,其中包括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耿濟之譯)和《教育之果》(沈穎譯),耿濟之還翻了《托爾斯泰短篇集》,同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談論托爾斯泰在當時毫無疑問是一種時髦。1921年,張聞天和陳望道、沈雁冰在《民國日報?覺悟》上就有過一次短暫的論戰(zhàn),因為托爾斯泰。
1921年3月底,張聞天住在杭州西湖邊的智果禪寺,在寺里,張聞天不讀佛經(jīng),卻迷上托爾斯泰。他在《小說月報》上發(fā)表的《托爾斯泰的藝術觀》是其翻譯生涯的第一部作品。同時,他也接受了托爾斯泰的思想,相信“不以暴力抗惡”才是救世之道,而他的朋友沈雁冰和陳望道則持相反態(tài)度,雙方你來我往,最后,以張聞天放棄自己的立場告終。
一場溫和的戰(zhàn)爭以和平收場。郭沫若曾根據(jù)德譯本翻譯過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1935年由光明書局出版。但是這位浪漫主義詩人顯然過于自信了,翻譯過《靜靜的頓河》的金人提出了這樣的質(zhì)疑:“對于郭沫若氏的譯文,很早我就懷疑,不論是《浮士德》,不論是《戰(zhàn)爭與和平》,甚至于《煤油》與《屠場》,我都覺得郭氏是在編譯,不是翻譯,所以筆調(diào)風格是郭氏的,而不是原作家的。”
有鑒于此,年輕的翻譯家高植動了翻譯《戰(zhàn)爭與和平》的念頭。1942年,抗戰(zhàn)5年,生活至艱,作為3個孩子的父親,他一人的薪水要養(yǎng)活5口之家,但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高植決心動筆翻譯《戰(zhàn)爭與和平》以激勵國人抗日之決心。他根據(jù)的是毛德英譯本,這個毛德(AylmerMaude)從1897年即和托爾斯泰交往甚密,因而此譯本直接得到精通德、法、英文的托爾斯泰本人的校訂和修改,因而是世界上最權威的《戰(zhàn)爭與和平》英譯本。在郭沫若的譯本基礎上,高植做了大量修改,并以“郭沫若、高植”的名義出版了《戰(zhàn)爭與和平》,這個譯本極少存世,較為常見的是高植日后重新從蘇聯(lián)1941年俄文原版翻譯的《戰(zhàn)爭與和平》,1957年7月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為了將托爾斯泰準確地譯介入中國,高植可謂嘔心瀝血,不想如今,卻要擔上“托兒所”所長的罵名,想來也是讓人感覺無奈。可是,這么多人在翻譯托爾斯泰,我們都知道托爾斯泰是個怎么樣的人了嗎?巴金在《隨想錄?“再認識托爾斯泰”》中感嘆道:“‘再認識托爾斯泰,談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爾斯泰,有多少人咒罵托爾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爾斯泰,但誰能說自己‘認識托爾斯泰?”
巴金和托爾斯泰的淵源可以追溯到1928年12月,那一年,他從法國結(jié)束留學回到上海,應胡愈之之邀,在《東方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托爾斯泰論》的譯文(原文作者托洛茨基),首次署名巴金。在《“再認識托爾斯泰”》中,巴金說自己“不是托爾斯泰的信徒,也不贊成他的無抵抗主義,更沒有按照基督教福音書的教義生活下去的打算”,那時候他信奉的是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各取巴枯寧的“巴”字和克魯泡特金的“金”字,乃成今日中國之“巴金”。
可是,托爾斯泰剛剛被介紹進中國的時候,他的思想,就是作為無政府主義的一種被廣為接受的。《新青年》3卷4號上的《托爾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作者是無政府主義者、北大教授黃凌霜。而當時,比黃凌霜更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則是以講中古文學史聞名的劉師培,他同樣很推崇托爾斯泰。
時過境遷,在社會主義思想摧枯拉朽般歷史推車面前,無政府主義很快成了過眼云煙,可是托爾斯泰并未就此過時,他似乎變得更為復雜,在他長老般的濃密虬髯下,那博愛如圣徒般的心靈,如大象般緩緩走過一百年的塵埃。
誰能理解托爾斯泰?
為紀念托爾斯泰逝世100周年,各類圖書推薦、影片放映、報告活動在各地悄然舉行,從不同的角度審視這位巨匠,也許我們就能離他更近一些,而不要急著大呼:這是“托兒”,這是禽獸!誰是真正的“托兒”我們心里還不清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