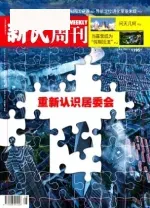散文家也斯
嚴飛
一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香港的城市外貌老被地產商所支配,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老被媒體轟炸所淹沒,也斯不過是在想:“那些小路旁邊的事物,那些沒有放大登上報刊頭版的人,也許也有他們值得聽聽的故事呢。”
我對詩歌沒有天賦,也所知甚少,只是粗淺地從艾青入門,讀北島、食指、海子、顧城、于堅。他們的詩總能進入我心靈的最深處,撥動我的神經,讓我在某一個瞬間,或者某一個時間和空間交匯的點上,覺察出自己一種近乎原始的渴求和訴說。不過到了現在,這樣的詩人越來越少,甚至有一段時間出現了所謂的“梨花體”,這對于詩歌而言,真是一種反諷。
但是有一天我讀到女詩人尹麗川從北京后海喝酒回來后寫的兩句話,立馬靈魂受到了想象力的強烈沖擊,史學的鏡像和美學的視像交織在一起,久久不能停罷。我知道,我一定是哪根神經突然錯位,否則不會這么激動,并且發出文人才有的嗟嘆。北京朋友若是知道我這個連北京都沒有正兒巴經待過的人竟然會如此,定會認為我多愁善感,外加一句“不靠譜”。
尹麗川只是寫道:“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我們去后海看雪,就回到明清。”
之所以扯到我對詩歌的認識,是因為我在讀香港作家也斯(梁秉均)的詩時,似乎總是難以生發出同感式的共鳴,甚至連圖像的影子都沒有。事實上,在也斯的香港詩歌中,經常會出現舊時香港的瑣碎景象與人物,這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是很多香港本土作者的敘事潮流——從舊時香港的老街道、老街坊、老味道、老故事中緬懷,進而追尋自己的香港本土意識與認同。
這就很奇怪,為什么明明在香港的時間遠遠多于北京,對香港的認識也遠遠勝于北京,可就是無法從也斯的詩中讀出香港呢?也斯曾說過,他最不能忍受來自外地的作家對香港一知半解式的解讀,因為“這很容易變成獵奇式的浮光掠影”。我想這應該出自我的身份原因,沒有在香港有過一段成長時期“刻苦銘心”的記憶,這大概是我嘗試以“在地”姿態解讀香港的一個難以克服的硬傷。
然而我在翻看也斯的散文集《也斯的香港》時,卻發現了他文字中情深意綿的另一面,以及另一個香港。
《也斯的香港》記錄了香港一些典型或者不典型的人物和地方,最早的一篇閑談書與街道的文章竟然寫于1970年,可見也斯記錄的香港,是一個三維度的香港,加入了時間這一重要元素。同時,也斯又很愛擷取城市中的某個獨特側影,例如柴灣的一棵榕樹、北角的一間食貨鋪、小說家劉以鬯的一次創作沖動,然后通過可能并不顯眼的日常生活描寫,從點滴中讓讀者去感受香港的面貌。
例如,也斯在《從甕中長大的樹》一文中,將與自己一樣成長于六七十年代,在種種混雜文化背景下汲取營養的香港文化人譬喻為“我們都是從甕中長大”,并且進一步指出:“在香港長大,其實也是在種種限制中長大。因為限制特別明顯,也分外自覺去超越它。幸好甕口總可以張望天地,甕內也有寬大的圓腹。”這種“甕中樹”的思想又貫穿于也斯的其他文章中,可以是在香港擠迫空間中無家可歸的詩(《蘭桂坊的憂郁》),可以是在繁華喧囂的上環高樓間鮮艷的畫作(《在上環繪畫古詩》),也可以是北角破敗市井中不少朋友彼此交叉相匯的童年(《鏡像北角》)。也斯在重現他們這一代對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貢獻時,也將“甕”的概念流線化,甕的體積在時間的長軸上越來越大,而甕中人的呼喊和抗爭卻越來越弱小:“香港作為寫作的環境的確愈來愈不理想,發在綜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檢查、刪改,或因編者的疏忽、美術編輯的輕狂、校對的固執而變得面目全非。在這樣的情況下,特別感到寄人籬下之苦。在香港寫作這么多年,最近可是愈來愈感到專欄的水平低落,不負責任的意見充斥,流行言論愈來愈張狂,要發表不同想法愈來愈難。香港是我的家,寫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變成一個陌生的地方,找一個地方說想說的話也不是那么容易了。”(《蘭桂坊的憂郁》)
這是一段具有抗爭意味的文字,也是一段憂心香港逐漸失去本我的吶喊。所以,相對于詩人也斯,我更喜歡散文家也斯和他筆下的香港。也斯沉浸于香港的瞬間意象,再演化成故事,娓娓道來。一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香港的城市外貌老被地產商所支配,香港人的集體記憶老被媒體轟炸所淹沒,也斯不過是在想:“那些小路旁邊的事物,那些沒有放大登上報刊頭版的人,也許也有他們值得聽聽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