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何其難
○王培元
一
人們常說的“實事求是”一詞,其實也是“古已有之”的。
《漢書》第五十三卷“河間獻王劉德傳”云:“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實事求是,據唐人顏師古注,即“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之意。
欲求真是,必先得事實,這大概是有起碼的認知經驗和思維正常的人都明白、知道的。但要真正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征諸古今史實,做不到的時候,怕倒是往往居多。
而以“實錄”為名目的史書,可以說是汗牛充棟。民國時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校印的《明實錄》中,曾收入《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簡稱《太祖實錄》)。萬斯同在《讀〈洪武實錄〉》一文中說:“高皇帝以神圣開基,其功烈固卓絕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后,其殺戮之慘一何甚也?……蓋自暴秦以后所絕無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謗,亦非人之所能掩也。乃我觀《洪祖實錄》,則此事一無見焉。”
于是,他追問道:“縱曰為國諱惡,顧得為信史乎?”接著,又在指出了“瑣屑之事”所記“累累不絕焉”之后,再詰問道:“是何暗于大而明于小,詳于細而略于巨也?”最后,得出此書“君子即不觀可也”的結論。
魯迅說,正史“涂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華蓋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這只不過是一個小小不然的例證而已。
二
啟功是清代皇族后裔、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知道許多皇家掌故。他在《啟功口述歷史》中,曾根據自己的聽聞談道:雍正計有十子,長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即已死去,二、三、七、八、九、十子,皆夭折,六子過繼給了別人。只有第四子弘歷和第五子弘晝,有繼承大統的可能。結果,弘歷當了皇帝,即清高宗乾隆皇帝,弘晝只能被封為和親王。
在爭奪帝位的過程中,弘歷和弘晝的關系十分復雜、微妙。生辰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只因弘晝比弘歷晚出生一個時辰,就決定了他們的兄弟關系及終身的君臣地位。影響他們復雜關系的,還有一個特殊背景。按清制,某后妃生了孩子,必須交給另外的后妃去撫養,目的是防止母子關系過于親密,進而聯合起來別有所圖,甚至謀求皇位。和親王系雍正耿氏妃所生,而撫養他的,則是乾隆的生母(雍正時被封為熹妃,乾隆即位后,稟雍正遺命,尊為孝圣憲皇太后)。而乾隆生下來之后,又由別人代為撫養。
乾隆的生母,雖不是和親王的生母,但因從小把和親王撫養大,對其感情也就特別深,對他的喜愛,甚至遠遠超過了自己的親生兒子乾隆。乾隆長大后,自然很了解此種感情和這層關系,他當上皇帝以后,也就時時加以提防。因為他繼承了皇位,生母就是皇太后,而太后在清朝是有很大權力的,甚至是廢立大權。乾隆總擔心太后因喜愛和親王,會借故廢掉自己,而立和親王為帝。所以,就采取了極為審慎周密的措施:一方面,對太后十分恭敬,晨昏定省,禮儀上格外尊崇,甚至大興土木,修建大報恩寺,為太后做壽;另一方面,到哪兒都帶著太后,表面是向外界宣示母慈子孝,自己時刻侍奉于太后左右。實際上,是時時處處盯著她,隔斷其與和親王的聯系。讓給別人看著,究竟不如自己看著更放心、更踏實。

《啟功口述歷史》,啟功口述,趙仁珪,章景懷整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版,80.00元
《清史稿·后妃傳》云:“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養。……太后偶言順天府東有廢寺,當重修,上從之。……上每出巡幸,輒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東巡者三,幸五臺者三,幸中州者一,謁孝陵,獵爾木蘭,歲必至焉。遇萬壽,與王大臣奉觴稱慶。……慶典以次加隆。……先以上親制詩文、書畫,次則……諸外國珍品,靡不具備。”
對“史”與“實”的抵牾之處,啟功說道:“如果把‘奉太后’‘南巡、東巡’等解釋為‘孝敬’,也許勉強可通,但‘獵爾木蘭’就令人費解了。‘木蘭’是滿語‘吹哨引鹿’的意思,清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圍場打獵習武,稱‘木蘭秋獵爾’,稱其地為木蘭圍場。……顯然,‘木蘭秋獵爾’,就是當時的軍事演習,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關系?為什么也非要帶著她?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到承德的避暑山莊?這不明明是對太后存有疑慮,才時時帶在身邊嗎?”(《啟功口述歷史》P 12-13,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清史稿》的有關記載,居然蒙騙過了現代著名學者王伯祥,他在《乾隆以來系年要錄》里,對乾隆每天親侍太后左右,兩人如何母慈子孝,大書特書,作為“煞有介事的美談”。了解“大孝子”乾隆真相的啟功,為此書所作跋中有云:
后世秉筆記帝王事跡之書,號曰“實錄”,觀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飲食,未聞言吃真飯,喝真水,以其無待申明,人所共知其非偽者。史書自明實錄,蓋已先恐人疑其不實矣。又實錄開卷之始,首書帝王之徽號,昏庸者亦曰“神圣”,童騃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實矣。
葉圣陶十分欣賞這段話,以為“此事可通讀報章”。可見“實事求是”之難。
三
當年,河南遂平縣查岈山公社(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開始時名為“衛星人民公社”),遵奉上邊的旨意,為了“給人民公社爭光”、“給黨爭光”,靠弄虛作假,放出了第一顆“高產衛星”,把10畝地麥子的收成11178斤,按2.9畝計算,平均畝產一下子就變成了3854斤,最后扣點麥余粒,按畝產3530斤上報。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方璜題為“衛星公社放出第二顆衛星——2畝9分小麥3530斤”的報道。配發的社論《向創造奇跡的農民兄弟致敬》,更是添油加醋、推波助瀾,開頭所引詩云:“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瞞報浮夸、欺騙輿論的極不正常的情況呢?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成都會議”。與會者討論的中共中央將提交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經過毛澤東的修改,已初步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的構想。參加會議的《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說此時的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涌,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重大歷史事件》,新華出版社1995年版)
在會上,毛澤東還談到了“個人崇拜”問題,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7卷P 369,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澤東的秘書、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陳伯達,在發言中主張:“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道:“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
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則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被譽為“毛主席的好學生”的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毛澤東的秘書手記》,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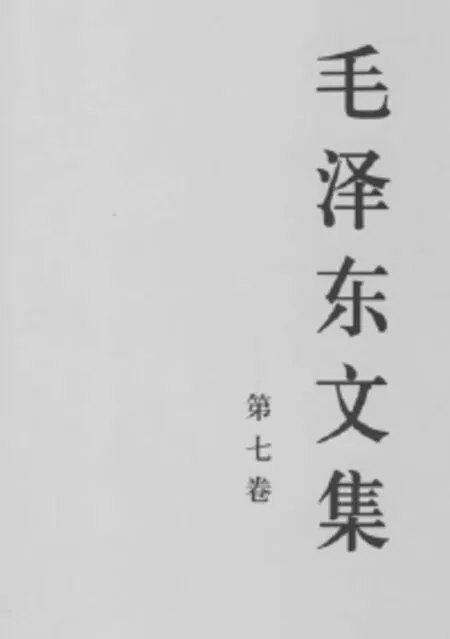
《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大32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29.00元
毛澤東說一不二,其他高級干部對黨的領袖則亦步亦趨。為了趕英超美,中共中央相繼提出并大規模實行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號稱“三面紅旗”。而結果呢?1959-1961年,出現了全國性的駭人聽聞的大饑荒。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表揚了河南,肯定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受寵若驚的吳芝圃,于是戟指發誓地承諾: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其后,河南的大躍進掀起了更大的浪潮,浮夸風在全省范圍內猛烈刮起來。全國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出現在了中原大地上。然而,民眾為此付出了極為巨大的代價。
《河南日報》1960年的元旦社論,卻仍號召持續躍進,以“開門紅 春意濃”為題,繼續粉飾太平。嗚呼!
挨著河南的安徽,也是重災區。中央領導董必武到阜陽視察,省里事先做好部署,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腫病人集中看管起來,不讓董看到真實情況。全省的饑餓狀況,一直被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捂著,既不向中央匯報,也不讓群眾說真話。毛澤東卻很信任他,還派他兼任山東省委書記。
而一些敢于講真話、實事求是的干部,如說“徐水是浮夸風、共產風的典型”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等,則被說成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反黨集團”、“小腳女人”,遭到無情打擊、殘酷批斗,直至撤職、查辦。
我的故鄉山東的范縣,1958年秋也曾做出一個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宏大規劃,提出3年內即把全縣993個自然村,變成25個“新樂園”。“新樂園”什么樣呢?“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種種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毛澤東十分欣賞,以為“是一首詩”。此規劃印入了中共中央宣傳部1958年11月4日編印的《宣教動態》中,在黨內廣為傳布。
時任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的趙健民,親自到范縣看過,發現當地搞的所謂共產主義完全是假的。他實事求是地向省委第一書記舒同反映情況,卻被扣上了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撤消職務,發配到濟南鋼鐵廠當副廠長。到了1959年,范縣的食堂就辦不下去了,全縣水腫病肆虐,餓死了不少人。
“實事求是”,何其難也!
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嚴重饑餓和死亡,1960年1月1日,《人民日報》在元旦社論《展望60年代》中,公開宣稱農業生產遇到了“幾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災害”。這一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再次說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把自然災害的影響強調得更嚴重:“在1959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
而在《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團結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中,作者金輝以國內一批著名氣象水文專家,根據全國120個水文站點歷年水文氣象資料,編制的《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等級資料表(1895-1979)》為基礎,得出了“1959-1961年全國旱澇態勢相當正常”的研究結論。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高素華也指出:“1959年到1961年,在全國范圍內沒有出現大面積的旱災和澇災,也沒有出現大面積的低溫災害。這三年是正常年景。”
四

《社論串起來的歷史》,袁晞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版,40.00元
半個世紀倏然而逝。這一頁國人無論如何也難以忘懷的沉重歷史,終于翻過去了。然而,追述起來,依然令人心魄為之戰栗,感到憤怒而且悲哀。出生于山西農村的作家趙樹理曾經說:“1960年時的情況是天聾地啞。”眼下坊間書寫近百年歷史的書籍,也似乎頗不少了,但是,能夠直面歷史,真實地記載這段異常慘痛、荒謬和瘋狂歲月的著作,簡直是寥寥無幾。
殷鑒不遠,寧不慎乎!
聽說,“實事求是”四個大字,被刻在大大的石碑上,眼下矗立在京城一黨校的校園里。自然,我是聽說而已,并未親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