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記》:棱角分明 求真不茍
○張學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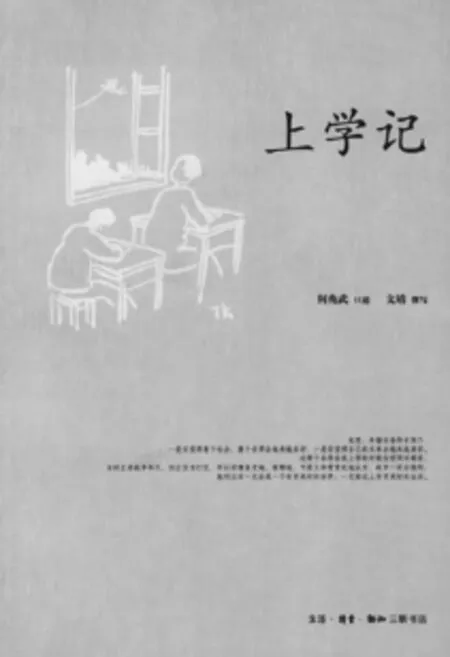
《上學記》,何兆武著,三聯書店出版社,2006年8月,19.80元
文化傳承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應該是把最真實的歷史存在、歷史精神、歷史意識和個人真實的歷史體驗和感受傳給后人,這樣后人在承接先輩的文化遺產中才能有一個可靠的依憑。
《上學記》由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寫完成。書中棱角分明的斷語和求真不茍的精神,讀之使人感到快慰。
關于讀書
率性而談,不加掩飾,臧否人物,愛憎分明,快人快語,睿智里包含著學者的堅定判斷。我以為,這正是何先生的話語風格,從中能看出老一代學人可貴的風骨。總的來說,這部傳記性的口述之作,屬于回憶性的文字著述。但是在回憶風格的行文走筆中,又不拘謹于一般意義上的回憶錄,而是選點記述,側重感知,照應現實,顯示情懷,表現出對歷史的相當尊重的科學精神。這樣的回憶,比常規意義上的只提供重要史料梳理歷史脈絡的回憶錄,對讀者的當下閱讀,更具一種過來人現身說法的況味。
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曾經紅極一時而廣為傳布,自有傳播馬列哲學的基本功勞在。它把深奧的馬列哲學經典轉化為大眾能看懂的語言和結構,呈現給人們,我們不能抹殺其歷史上的價值。但是,何先生看到了另一個問題,就是比喻多于論證從而顯得武斷的不足。他認為比喻不能代替論證,“一直到解放后聽他的講演,我也不怎么欣賞,在我的印象中,他的武斷更多于論證”。(P 37)并且,在當時,他就這么認為。再如錢穆的《國史大綱》,說好話的稱道的至今還大有人在。可是何先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意,因為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只看到她好的一面,對她不好的一面卻閉口不談。(P 111)另外,錢先生的世界近代史知識不夠,影響了他的判斷。還有,楊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寫得很不符合當時的情況。(P 134)這里涉及到了文學創作中的藝術真實和歷史真實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藝術家往往以藝術真實為武器,回敬那些挑三揀四的細節上指責,以為自己細節上的失真辯護;歷史學家往往以歷史存真的姿態指謬。二者的恰當統一和協調,才是文學創作中所應遵循的。何先生正是抓住了一二九時期北京大學的學生實際,指出小說寫林道靜與男士同居并且還不止一個,這不符合歷史細節。
還有,對中國圖書館管理的大為不滿。他認為:圖書館不是珍藏樓。(P 120)而現實是,圖書館多辦成了珍藏樓,給讀者的借閱帶來極大的不便利,手續多多,環節麻煩,效率低下,令讀者氣悶。
關于年輕人的成長
何先生認為:年輕人受教育不一定是在課堂上聽老師講的。(P 40)自然,課堂是青年人受教育的一個重要途徑,但是在今天許多人把課堂上接受教育當成了唯一的途徑。從《上學記》里看,何先生當年求學知識的途徑除了課堂之外,還有逛書店、看電影等。這對我們學習觀念上的偏差應當是有益的提醒。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學校教育的培養,但一味迷信課堂,獲益是有限的,要是碰到應試教育而不自知,那將是悲劇性的結果。

《大眾哲學》(修訂本),艾思奇著,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18.00元

《國史大綱》(上下冊),錢穆著,商務印書館1996年6月版,60.00元
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但沒有人不想作出應有的成就。我們至今不是講實現人生的自我價值嗎?何先生告訴說:想要做出成績總要有三個方面的條件:一是天賦;二是環境;三是個人努力。(P 47)我們的青年學子不是都在做著自己的職業生涯規劃嗎?何先生這個排序提醒每個人,必須對自己有一個熟悉的了解。我注意到,何先生沒有把“努力”放在第一位,而我們現在的提倡中多把勤奮努力放在第一甚至是唯一的高度上。不錯,個人的努力是前提,但是,如果不切合自己的天賦實際一味盲目努力,那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劇。當然,還有環境的條件問題。在這里,我寧愿這樣理解:即這三個條件不能絕對割裂地理解,一個人要做出點成績,這三個條件缺一不可,該是各在各的軌道上起作用。
年輕人必備的品質:要想超越前人,必得先看出前人的不足,要是拜倒在他的腳下,那就永遠也超不過他。自慚形穢的人,如我,大概永遠不會是有為的。(P 129)這個話,說起來不容易,做到就更不容易。許多有成績的前人,往往在青年人面前擺起權威的姿態;許多年輕人,在權威面前往往謙卑到喪失了自我的地步。老師們大聲訓斥著自己的學生為什么沒有創造性,可是學生在這教誨面前早不知所措了。何先生的話提醒青年人,一定要守住自己的獨立性。要有挑戰權威的精神,要在權威面前有不自慚形穢的堅挺自信。
關于歷史人物
書中寫道:“1935年12月,以宋哲元為首在北京成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也是日本侵華的特殊產物,因為無論是國民黨或日本那一方面來了,都不會有他的份。日本不過是利用他作為向‘特殊化’的過渡,如果真正國民黨勢力控制了,也不會要他這種非嫡系的舊式軍閥。今天卻為宋哲元送上一頂‘愛國將領’的桂冠,似乎很不實事求是。不應無視歷史,‘愛國’一詞不宜貶值。”(P 53)這是多么硬朗的話語。他還說:“我們對宋哲元的痛恨絕不亞于對日本的痛恨。如果以大刀、水龍鎮壓‘一二·九’運動的宋哲元是愛國,難道‘一二·九’運動是賣國嗎?盡管宋哲元后來并未做漢奸,但他的所作所為與‘愛國’相去甚遠,如果不是他一味地妥協求全,北京、天津和河北不至于那么輕易地淪陷,等于拱手送人。”(P 54)
對聞一多,何先生說:“聞一多先生早年追求純粹的美,后來成為民主斗士,旁人看來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徹底的思想轉變,但我以為那不過是一些表面的變化。”(P 140)還說:“我以為,聞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貫之的,本質上還是個詩人,對美有特別的感受,而且從始至終都是一包熱情,一生未曾改變過。現在不是很多人在討論:如果魯迅活著會怎么樣?其實同樣可以問:如果聞一多活著會怎么樣?僅憑一包熱情,恐怕也不會暢行無阻,我這么想。”(P 141)
何先生對吳晗的印象很不好。他舉了三件事。一是作為二房東,經常趕人搬家,說是親戚要來住,把房子收回去。(P 153)二是跑警報時倉皇失態。何先生說:“有一次拉緊急警報,我看見他連滾帶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面色都變了,讓我覺得太有失一個學者的氣度。”(P 154)三是教學上的問題。當時吳在教師中輩分很低,是個青年教師,也仿照著老教師的做法,給人一種妄自尊大的感覺。學生和他交涉,他一怒之下宣布罷教。解放后吳晗寫檢討,總覺得他心里有個疙瘩,即“希望自己躋身名教授之列”。何先生對清華大學在解放后給吳晗立像大不滿意,說:清華比他優秀的人多了,為什么偏偏給他立像?(P 155)
關于歷史精神
《上學記》是一部回憶錄,但不是一般的僅僅實錄史料史實的回憶錄。在閱讀的時候,分明感到字里行間里灌注著一種堅不可摧的歷史精神。我們的學術,我們的藝術,恕我直言,就缺乏一種歷史精神。諸如一些回憶錄里,回憶者在回憶的時候不免有粉飾、修飾、篡改乃至偽造之嫌。歷史精神,簡單地說,就是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就是對自己當時的感受的尊重,就是面對歷史真實的負責的態度。何先生的筆下不僅如此,還特別重視歷史細節的呈現。我不是說何先生的所說就一定得相信和接受,而是我相信他的所言沒有違背自己的感受和判斷。面對《西南聯大校史》(北大出版社出版),他表達了自己的不滿意,認為“真正的歷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寫出來”。(P 189)再如北京大學的百年校慶的紀念文字中,絕口不提歷次“運動”。這些做法,在何先生看來,都是不合適和不應該的,也是不尊重歷史的。
為什么會這樣?何先生給出一個善意的理解和回答。他說:“可惜我們現在看過去的人總是帶著諒解的眼光,只看到融洽的一面,沒有看到他們彼此相互看不起的那一面,沒有把人與人之間的一些矛盾真正揭發出來。”(P 117)我想,文化傳承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應該是把最真實的歷史存在、歷史精神、歷史意識和個人真實的歷史體驗和感受傳給后人,這樣后人在承接先輩的文化遺產中才能有一個可靠的依憑。《上學記》屬于個人回憶錄作品,但她把作者真實的體驗和感受記載下來,一個活生生的何先生的感受讓我們讀起來感到親切和溝通。他把人與人之間當年的許多矛盾揭發出來,他把可能的歷史壁壘鑿孔打通,他給讀者一個可以傳遞的歷史感知。我們有幾千年的文化積淀,汗牛充棟的文化典籍足可以讓后人望而卻步。如果再加上人為的遮蔽和掩飾,真的進入歷史將是何其難哉!何先生的直言不諱,給讀者帶來了福音。無論是聞一多、吳晗,還是宋哲元,無論是艾思奇,還是北大的校慶紀念,還有現實中的諸多現象,何先生就他的感受,發出了可貴的真實聲音。因此,有理由期望何先生的《上班記》快快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