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峻:挖掘李莊精神
○張 弘
在矛盾和溝通中相互融合
問(wèn):《發(fā)現(xiàn)李莊》中有一個(gè)細(xì)節(jié)很有意思。為祖師殿翻蓋瓦房的泥水匠爬到屋頂上,看到同濟(jì)醫(yī)學(xué)院師生在做人體解剖試驗(yàn)。于是謠言四起,說(shuō)“下江人”到鄉(xiāng)下捉人來(lái)吃,接著來(lái)了兩個(gè)營(yíng)的軍隊(duì)戒嚴(yán)。后來(lái),傅斯年提出堵塞不如疏導(dǎo),利用展覽的形式很快消除了誤解,使謠言不攻自破。此外,李濟(jì)的兩任房東都很刁蠻。從這些事來(lái)看,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在李莊,遭遇到了科學(xué)與迷信,現(xiàn)代文明與鄉(xiāng)土社會(huì)之間的沖擊。你如何看這種矛盾?
岱峻:國(guó)家最高學(xué)術(shù)科研機(jī)構(gòu)遷在西南邊陲一個(gè)小小的村莊,這種事恐怕是空前絕后的。其間遇到的困難,諸如環(huán)境的落差、貧病兵匪的威脅、科學(xué)與迷信的沖突、精英學(xué)術(shù)與鄉(xiāng)邦文化的隔膜等,層出不窮,難以想象。解決這些問(wèn)題,一是有國(guó)家機(jī)器的支持,比如地方政府協(xié)調(diào)、軍隊(duì)保護(hù)、物質(zhì)供給;二是遷到李莊的學(xué)術(shù)科研機(jī)構(gòu),對(duì)地方的依賴性也不很強(qiáng),即使彼此有些誤會(huì),似也不傷大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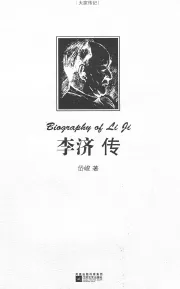
《李濟(jì)傳》岱峻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32.00元
就在外來(lái)者中,也有德日學(xué)派(同濟(jì)大學(xué))和英美學(xué)派(史語(yǔ)所、社會(huì)所等)的格。在中研院內(nèi)部,也有陶孟和與傅斯年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lái)”、傅斯年與李濟(jì)在板栗坳演出的“全武行”、吳定良苦心孤詣籌備多年的體質(zhì)人類學(xué)研究所終成泡影……但這些矛盾也顯示了人性的豐富性,而各種矛盾最后也統(tǒng)攝服從于全民抗戰(zhàn)這個(gè)大背景。于是在這個(gè)彈丸之地,人們又彼此妥協(xié)、溝通、融合,朝著一個(gè)大的目標(biāo)艱難前行。
問(wèn):你覺(jué)得,這些機(jī)構(gòu)扎根李莊,以及學(xué)術(shù)工作者和李莊女性的通婚,對(duì)于李莊的鄉(xiāng)民和鄉(xiāng)紳社會(huì)來(lái)說(shuō),帶來(lái)了怎樣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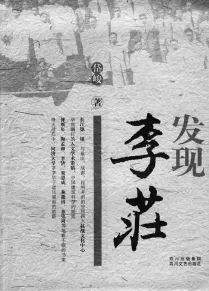
《發(fā)現(xiàn)李莊》岱峻著,四川文藝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29.00元
岱峻:這些機(jī)構(gòu)盡管扎根李莊長(zhǎng)達(dá)6年,一批研究人員和李莊女性通婚,的確給李莊帶來(lái)不小的變化,如文明水準(zhǔn)和文化素質(zhì)的提高,眼界的開(kāi)闊,一些環(huán)境條件的改變等。人員的交流,比如羅哲文是宜賓當(dāng)?shù)氐母咧猩涣核汲烧袨榫毩?xí)生,現(xiàn)在是古建泰斗。李莊當(dāng)?shù)厝藙Y臨跟史語(yǔ)所最后到了臺(tái)灣,成為甲骨文專家……
但這種變化畢竟有限,只是量的積累(比如在少數(shù)幾戶家庭),還沒(méi)對(duì)社會(huì)產(chǎn)生質(zhì)的改變。一個(gè)地方文化的形成,是逐步接受逐步發(fā)展的過(guò)程。一個(gè)錯(cuò)位的時(shí)空,就像夏天的一場(chǎng)雨,太陽(yáng)一出,很多東西都可能蒸發(fā)得干干凈凈。我在書里寫道:“第一次走進(jìn)李莊,幾乎叫做空手而歸。有一次,我在板栗坳的山路上,遇到了一個(gè)當(dāng)?shù)氐睦相l(xiāng),他問(wèn)我,‘你是收舊門窗的嗎?’我還向一個(gè)村干部打聽(tīng)當(dāng)年的中央研究院,他說(shuō),‘哎呀,老師你開(kāi)玩笑,中央的人怎么會(huì)到我們這兒來(lái)呢?’”研究人員與李莊女性的結(jié)合,也不值得特別贊美,其中雖也有神仙眷侶比如逯欽立娶羅南陔的女兒羅筱蕖,但有的婚姻質(zhì)量并不高,只是“將就”而已。對(duì)此,傅斯年當(dāng)年就極不贊成,他怕特殊時(shí)空的錯(cuò)位會(huì)釀成年輕人日后的婚姻悲劇。這種事,與“文革”中大學(xué)、科研機(jī)構(gòu)辦在農(nóng)村一樣,與女大學(xué)生嫁給農(nóng)民等相似,成功者肯定有,但概率不一定高。
問(wèn):史語(yǔ)所在生活條件那樣艱苦的條件下,取得了豐碩的學(xué)術(shù)成果。為什么?是否可以用董同龢的“要以抗戰(zhàn)的精神來(lái)讀書做學(xué)問(wèn)”來(lái)解釋?
岱峻: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批學(xué)人首先是有一種文化的自覺(jué),以抗戰(zhàn)的精神來(lái)讀書做學(xué)問(wèn),有“憂道不憂貧”的高貴精神、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的社會(huì)擔(dān)當(dāng),更大的原動(dòng)力則是強(qiáng)烈的民族自尊心。讀書治學(xué),為民族復(fù)興儲(chǔ)能,是那批學(xué)人的行為理性。正是有此精神動(dòng)力,才會(huì)在山鄉(xiāng)僻野崛起一座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城。歷史上一段黑暗時(shí)期,竟成了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發(fā)展的一次機(jī)遇。
談到史語(yǔ)所學(xué)術(shù)科研的成功,還有下列幾個(gè)條件:
其一,進(jìn)史語(yǔ)所的門檻高,每個(gè)人都經(jīng)過(guò)傅斯年的嚴(yán)格挑選。創(chuàng)辦史語(yǔ)所,傅斯年首先聘請(qǐng)了陳寅恪、李濟(jì)、趙元任、李方桂、董作賓、徐中舒等著名學(xué)者領(lǐng)導(dǎo)或參加各組的研究工作。同時(shí)也注重對(duì)年輕研究員的培養(yǎng)。著名人類學(xué)家張光直曾深有感觸地說(shuō):“三四十年代的歷史語(yǔ)言研究所是一個(gè)人才薈聚的寶庫(kù)。所長(zhǎng)傅斯年先生雄才大略,學(xué)問(wèn)眼光好,又有政治力量和手腕。他以‘拔尖主義’的原則,遍采全國(guó)各大學(xué)文史系畢業(yè)的年輕菁英學(xué)者,把他們收集所里,專門集中精力作研究工作。所以三四十年代被他拔尖入所的學(xué)者多半是絕頂聰明,讀書有成,性情淳樸、了無(wú)機(jī)心的書生。……高去尋、勞、丁聲樹(shù)、張政、陳、董同、嚴(yán)耕望等先生都可為代表。這批人才的儲(chǔ)集,可以說(shuō)是傅斯年先生對(duì)中國(guó)史學(xué)上最大的貢獻(xiàn)。”
其二,傅斯年經(jīng)營(yíng)史語(yǔ)所,對(duì)治學(xué)方法、研究方向、課題選擇甚至參考書都考慮得很細(xì)。在他手下,有壓力,也容易出成果。對(duì)此,李濟(jì)談到:“他具有超人的組織能力及對(duì)于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深切了解。他最知道,現(xiàn)代的學(xué)術(shù),尤其是科學(xué)的工作,如現(xiàn)代的戰(zhàn)爭(zhēng)一樣,是集團(tuán)的,不是個(gè)人的。在他領(lǐng)導(dǎo)下的一切工作,都從選拔人才及組織入手。無(wú)論是辦研究所或大學(xué),他總是像一個(gè)設(shè)計(jì)的總建筑師經(jīng)營(yíng)一個(gè)偉大的建筑一樣,有一套完整的藍(lán)圖,并且與他的工程師充分地合作,按部就班,一段一段地,完成他的計(jì)劃。”胡適也評(píng)價(jià)傅斯年辦史語(yǔ)所,實(shí)行了英國(guó)培根所講的“集團(tuán)研究的辦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進(jìn)國(guó)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國(guó)做到了”。
其三,史語(yǔ)所有一座戰(zhàn)時(shí)中國(guó)最好的文科圖書館。鄧廣銘寫道:“我跟傅先生去,除了想求得他指導(dǎo)外,還有一個(gè)原因,那就是北大、南開(kāi)、武漢大學(xué)南遷,都沒(méi)有帶圖書資料去,后方南遷的,只有史語(yǔ)所帶了個(gè)圖書館,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圖書資料。”董作賓曾撰文介紹板栗坳的史語(yǔ)所圖書館:“這是第一院,是山村入口的第一所,而且是一所最大的房子。大門是一排九間,門內(nèi)的大廳,也是一排九間,中間的七大間是漢籍書庫(kù),這無(wú)疑的要算大后方惟一的文史圖籍最完備的圖書館。再后一進(jìn)是西籍書庫(kù),還有些善本書分存第三院。這里共有中文書十三萬(wàn)多冊(cè),西文書一萬(wàn)多冊(cè),中外雜志二萬(wàn)冊(cè),因此,除了史語(yǔ)所同人閱讀之外,許多有關(guān)系的機(jī)關(guān)團(tuán)體,都有人在這里研究參考。——這一座精神食糧的倉(cāng)儲(chǔ),中國(guó)文化的寶庫(kù),到現(xiàn)在真算是能夠供應(yīng)當(dāng)前的需要而取之無(wú)禁,用之不竭。也不負(fù)十年前傅孟真(斯年)先生購(gòu)求時(shí)每?jī)?cè)書必經(jīng)他親手審擇,和近年來(lái)數(shù)萬(wàn)里輾轉(zhuǎn)遷運(yùn),愛(ài)護(hù)保管的一片苦心了。”
四是有與國(guó)外學(xué)術(shù)界交流的平臺(tái)。史語(yǔ)所有一批外籍研究員,如伯希和等,與歐美國(guó)家的學(xué)術(shù)機(jī)構(gòu)建立著互惠互利的學(xué)術(shù)交流關(guān)系。即使在李莊板栗坳如此艱難的條件下,還接受了印度的訪問(wèn)學(xué)者,接待過(guò)費(fèi)正清、李約瑟和英國(guó)博物館館長(zhǎng)Jayne等。
問(wèn):在我的印象中,知識(shí)分子在民國(guó)早期收入很高。抗戰(zhàn)期間,李莊的知識(shí)分子、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都十分貧窮。這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岱峻:戰(zhàn)前,中研院職員的薪俸是很高的。按1930年7月2日頒布的標(biāo)準(zhǔn),書記的月薪是30-60元,事務(wù)員、助理員60-180元,專任編輯、技師120-300元。專任研究員最高月薪可達(dá)500元。那時(shí)一般人的收入,石璋如在上個(gè)世紀(jì)30年代的殷墟發(fā)掘時(shí)寫過(guò),一般民工月薪是5個(gè)大洋,小學(xué)教員是15個(gè)大洋。
后來(lái),國(guó)民政府發(fā)出通知,國(guó)難期間的生活費(fèi)暫按以下規(guī)定執(zhí)行:薪金60元以下者照發(fā);60元以上者暫支60元。戰(zhàn)時(shí)知識(shí)分子的地位,又淪落到“七娼八丐九儒”的處境。
被遺忘的李濟(jì)和不無(wú)偏頗的傅斯年
問(wèn):中國(guó)考古學(xué)之父李濟(jì)在大陸被淡忘,主要原因在哪里?
岱峻:近年來(lái),關(guān)于李濟(jì)的話題逐漸為學(xué)術(shù)界、文化界和大眾傳媒重視,重申李濟(jì)對(duì)殷墟考古發(fā)掘的貢獻(xiàn),《李濟(jì)文集》等著作也在內(nèi)地出版。耐人尋味的是,李濟(jì)自1949年播遷臺(tái)灣,建立起臺(tái)灣考古學(xué)體系,作為臺(tái)灣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軍人物,曾一度官至“中研院”代院長(zhǎng)(1958年),而此前不僅是大陸,就是在臺(tái)灣也沒(méi)有一本關(guān)于他的傳記、年譜或回憶錄問(wèn)世。
分析原因,在大陸,是那場(chǎng)改朝換代的暴風(fēng)驟雨,轉(zhuǎn)瞬間它滌蕩了過(guò)去時(shí)代的所有痕跡。1950年后,當(dāng)《中國(guó)通史簡(jiǎn)編》《沫若文集》等書再版時(shí),刪去了原來(lái)關(guān)涉李濟(jì)的全部文字;上海魯迅紀(jì)念館開(kāi)館時(shí),掛出魯迅與楊杏佛的合影,裁去了三人照左邊的李濟(jì);西安易俗社懸掛的“古調(diào)獨(dú)彈”匾額,捐匾的12人中涂掉了李濟(jì)的名字……提到李濟(jì),總是作為政治批判的靶子。2005年臺(tái)灣文人李敖訪問(wèn)大陸的前一天,他還在鳳凰衛(wèi)視“李敖有話說(shuō)”中,啐李濟(jì)的口水……
而今,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如胡適、錢穆、傅斯年、梅貽琦、趙元任等早已進(jìn)入我們的閱讀視野,唯獨(dú)李濟(jì)仍鮮為人知。其中一個(gè)原因,或在于他是個(gè)純粹的學(xué)者,始終躲閃著政治風(fēng)雨,1949年幸免于被宣判為“文化戰(zhàn)犯”的命運(yùn),也沒(méi)有像胡適那樣在50年代受到數(shù)億人的口誅筆伐變得家喻戶曉,因此很快就淡出了大陸學(xué)術(shù)界。
在臺(tái)灣,李濟(jì)雖是“最后一個(gè)迷人的重量級(jí)的學(xué)閥”(李敖語(yǔ)),但他“不留情面”、“直道而行”的狷介性格,仍“是個(gè)被上級(jí)、同僚、晚輩、學(xué)生害怕的人”(宋文薰語(yǔ))。他是純粹而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者,所從事的考古學(xué)、人類學(xué)的專業(yè)鴻溝也總會(huì)令人望而生畏。
問(wèn):你在書中寫道了李濟(jì)和傅斯年的矛盾。你怎么看?
岱峻:明人蘇竣在《雞鳴偶記》中把朋友分為四類:“道義相砥,過(guò)失相規(guī),畏友也;緩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飴,游戲征逐,昵友也;和則相攘,患則相傾,賊友也。”李濟(jì)為人主張“直道而行”,傅斯年又稱“傅大炮”,兩人是一種畏友的關(guān)系。
1928年,李濟(jì)從歐洲回來(lái)路過(guò)廣州,與傅斯年一見(jiàn)如故。李濟(jì)評(píng)價(jià)傅斯年,“他是認(rèn)識(shí)到東西方文化彼此間的不同并具體設(shè)法使這兩種文化結(jié)合的中國(guó)學(xué)者的范例。”而傅斯年夯實(shí)了“想請(qǐng)他擔(dān)任我們研究所的考古一組主任”的決心,此前他在李濟(jì)與金石學(xué)家馬衡之間掂量不定。
40年代初,李濟(jì)的兩個(gè)女兒相繼在昆明和李莊去世。傅斯年見(jiàn)他情緒低落,曾與他作過(guò)一次推心置腹的長(zhǎng)談,勸他外出考古,移情西北。這件事更增添了李濟(jì)對(duì)傅斯年的信賴和親近;但兩顆心靠得太近,反而更容易受傷害。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fā)生了——
中博院籌備處在南京成立時(shí),傅斯年兼首任主任;1934年7月,李濟(jì)接任主任,仍兼史語(yǔ)所考古組主任。史語(yǔ)所和中博院的關(guān)系始是父子,后為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規(guī)模的田野發(fā)掘轉(zhuǎn)入室內(nèi)整理后,做田野的就分成兩撥,一撥在史語(yǔ)所考古組,一撥如郭寶鈞、尹煥章、趙青芳等轉(zhuǎn)入中博院。過(guò)去一家人吃飯,李莊時(shí)期分灶自理,一處在山上板栗坳,一處山下張家祠,天長(zhǎng)日久,難免不衍生是非。
1943年,史語(yǔ)所與中博院等合組西北考察團(tuán)。6月中旬,為曬印敦煌照片,考察團(tuán)的中博院職員曾借用史語(yǔ)所考古組照像室的兩種藥料。傅斯年本可睜只眼閉只眼,但他卻一副“親兄弟明算賬”的作派。6月20日,他約李光宇上山,詢問(wèn)此事原委。李光宇是李濟(jì)的遠(yuǎn)房侄子。投鼠忌器,當(dāng)傅斯年覺(jué)察時(shí)忙致信李濟(jì),“向兄請(qǐng)罪,敬乞曲諒。”李濟(jì)回應(yīng),“自當(dāng)由弟負(fù)責(zé)償還,擬明日親往覓購(gòu)”,解釋中猶有抱怨:“照像室管理事,除飭李連春趕緊造具清冊(cè)呈送鈞覽外,并祈即派一品學(xué)較優(yōu)之人嚴(yán)格管理,以維公物”。李濟(jì)第二天在史語(yǔ)所的所務(wù)會(huì)上指桑罵槐,向辦事員汪和宗發(fā)難。傅斯年氣急敗壞。兩人信來(lái)函往,筆戰(zhàn)不止。最后傅斯年上告朱家驊要求查辦,還驚動(dòng)了李濟(jì)年邁的父親。重慶中研院總辦事處代理總干事葉企孫回函傅斯年:“關(guān)于向博物院索回木匠之米代金事,兄及汪君毫無(wú)作弊之事實(shí)嫌疑及動(dòng)機(jī)至為明顯。濟(jì)之兄隨意誣人,殊屬失當(dāng)。但亦只能假設(shè)此因心緒不佳所致而原諒之。”
林徽因在給友人的信中談?wù)撨^(guò)這類事:
1943年春天,在逃難來(lái)李莊的研究人員中間包括他們的妻子們?cè)趦?nèi),染上了一種最終導(dǎo)致?tīng)?zhēng)吵、憤怒、謾罵和友誼破裂的煽動(dòng)性流言蜚語(yǔ)。這是一個(gè)思想偏狹的小城鎮(zhèn)居民群。最近,一些快樂(lè)的或者滑稽形式的爭(zhēng)吵已在受過(guò)高等教育的人群中發(fā)展到一種完全不相稱的程度。我很懷疑,是不是人們?cè)谝粋€(gè)孤島上靠十分菲薄的供應(yīng)生活,最終就會(huì)以這種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來(lái)。
時(shí)局艱危,供給匱缺,交通閉塞,內(nèi)心煎迫,急中生亂,借此宣泄,也許是形成“孤島心態(tài)”深沉的社會(huì)原因。而李濟(jì)一家的悲情是當(dāng)時(shí)所有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談?wù)摰脑掝}。這場(chǎng)“誤會(huì)”,并沒(méi)傷及兩人的友誼。李濟(jì)終身感激傅斯年,他后來(lái)曾坦誠(chéng)地說(shuō),“是因受傅斯年之聘主持殷墟發(fā)掘而得以施展抱負(fù)的,如果沒(méi)有傅斯年的幫助,自己在考古學(xué)方面的成績(jī)肯定要小得多。”1950年傅斯年去世后,李濟(jì)在《值得青年們效法的傅孟真先生》一文中寫道:“他手創(chuàng)的及畢生領(lǐng)導(dǎo)的歷史語(yǔ)言研究所過(guò)去的工作成績(jī),已能使歐洲的漢學(xué)家再也不敢低視中國(guó)學(xué)人的工作能力。十余年前,有一個(gè)美國(guó)學(xué)者曾告訴我說(shuō):你們中國(guó)有傅所長(zhǎng)這種人,你們的前途是無(wú)限量的!愛(ài)慕傅先生的青年們,切莫要因?yàn)楦迪壬ナ溃雇鈬?guó)的觀察家換一種說(shuō)法。”
李濟(jì)與傅斯年是共事了二十多年的畏友諍友。上世紀(jì)90年代的史語(yǔ)所所長(zhǎng)杜正勝在回顧傅斯年志業(yè)時(shí),說(shuō)過(guò)這樣一段話:“從現(xiàn)在保存的檔案分析,史語(yǔ)所創(chuàng)所四巨頭(指傅斯年、陳寅恪、趙元任、李濟(jì)四位)中,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和發(fā)展策略與傅斯年最契合者,恐怕要推李濟(jì)。”
問(wèn):根據(jù)你的研究,兩人的矛盾使得傅斯年遷怒李濟(jì)的學(xué)生田野考古第一人吳金鼎,在職稱問(wèn)題上壓制他,并改變了其人生軌跡。在這件事情上,應(yīng)當(dāng)怎樣看傅斯年的作為?
岱峻:對(duì)吳金鼎的業(yè)績(jī),同仁多很佩服,如石璋如評(píng)價(jià):“吳先生是龍山文化的發(fā)現(xiàn)者,——直到現(xiàn)在為止,在田野工作上來(lái)說(shuō),稱得起是田野考古第一人。”
吳金鼎為何要離開(kāi)李莊,離開(kāi)史語(yǔ)所,離開(kāi)了田野考古工作?李光謨?cè)嬖V我:
吳金鼎離開(kāi)李莊或許有些別的原因。他原來(lái)是專任副研究員,1942年史語(yǔ)所給他轉(zhuǎn)成“技正”。不知這會(huì)不會(huì)對(duì)他的積極性有所挫傷?他們兩口子特別恩愛(ài)。在山東做考察也帶著夫人,那是在出國(guó)以前了。后來(lái)夫婦倆都去了英國(guó)。夫人陪讀是自己掏錢。回來(lái)后,為了照顧吳金鼎,幫助整理材料,幫著分類,但是夫人從來(lái)不要公家的薪水,完全是盡義務(wù)。給他轉(zhuǎn)為“技正”,這么限制他,他肯定留不下來(lái)。像吳先生這么一個(gè)優(yōu)秀的考古學(xué)家為什么傅斯年不留他?這些事好像都可以找到原因,但要細(xì)分析起來(lái)又什么都說(shuō)不清楚。
吳金鼎是李濟(jì)唯一的親傳弟子。從李光謨的欲言又止的神態(tài)上猜測(cè),會(huì)不會(huì)緣于李濟(jì)與傅斯年的矛盾?我從史語(yǔ)所的檔案中看到一些蛛絲馬跡:
1941年2月1日,史語(yǔ)所召開(kāi)年度第一次所務(wù)會(huì)議,“決定聘丁聲樹(shù)為專任研究員(李方桂提)、聘芮逸夫陳勞為專任副研究員(傅斯年等提)、聘吳金鼎為專任副研究員(李濟(jì)提)”。1942年1月19日,史語(yǔ)所函總辦事處:“擬改副研究員吳金鼎君為技正,助理研究員全漢升為專任副研究員,請(qǐng)補(bǔ)呈院裁奪。”1月29日,傅斯年給吳金鼎寫信,解釋“發(fā)予技正聘書之原由”。按中研院薪俸標(biāo)準(zhǔn)規(guī)定,技正最高每月400元,而專任研究員則是每月500元。由專任副研究員改為技正,實(shí)際上是斷了晉升的階梯。2月12日,吳金鼎回函傅斯年:“屢蒙先生及所中師友一再嘉許獎(jiǎng)勵(lì),嗣后更當(dāng)努力學(xué)業(yè)以報(bào)知遇之雅。”
1943年1月12日,吳金鼎致函傅斯年:“琴臺(tái)發(fā)掘報(bào)告鼎所擔(dān)負(fù)部份約于本年三四月間可以草就,此間事完結(jié)后,再一步工作維何,極盼所中早日指派以便預(yù)先籌備。”同一天,傅斯年致電李濟(jì),“歷年舊例,本院與人合作(名稱)皆列在前,此次本以川博為主體,但本所應(yīng)在中博前,乞改正。余均欣佩贊同,祝發(fā)掘成功。”這件事可看出傅斯年與李濟(jì)各自的心思。我猜想,依傅斯年“遷怒”的性格,回復(fù)吳金鼎的信多半不會(huì)有好氣。于是才有吳金鼎3月6日的信說(shuō):“所中經(jīng)費(fèi),深能體會(huì),數(shù)年來(lái)深感經(jīng)濟(jì)壓迫,國(guó)家情形如此,現(xiàn)決意投軍委會(huì)戰(zhàn)地服務(wù)團(tuán),諒必能見(jiàn)允。”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跳出三界外,不在此行中。這或許就是吳金鼎投筆從戎離開(kāi)史語(yǔ)所的真實(shí)原因。抗戰(zhàn)勝利后,他應(yīng)母校之邀在成都華西壩主持齊魯大學(xué)復(fù)員工作。他致函傅斯年:“勝利消息傳來(lái),實(shí)可喜可賀,現(xiàn)已呈請(qǐng)上峰乞脫軍籍,諒可邀準(zhǔn),惟以母校齊魯大學(xué)年來(lái)迭經(jīng)風(fēng)波,擬趁機(jī)略盡綿薄,謹(jǐn)此請(qǐng)求準(zhǔn)予解除技正職務(wù),等半年或一年后,再聽(tīng)命從事田野考古。”從信中看,他對(duì)“技正職務(wù)”始終難以釋懷。
除了對(duì)待吳金鼎的不公,傅斯年在處理游壽的問(wèn)題上同樣也有失當(dāng)之處。
1943年8月21日,游壽由中博院借調(diào)到史語(yǔ)所。去史語(yǔ)所,游壽多半是出于學(xué)術(shù)上的考慮。游壽是負(fù)氣離開(kāi)李莊的。1946年10月4日,游壽擲給史語(yǔ)所所長(zhǎng)傅斯年、代理所務(wù)的董作賓一紙嗔言:“平生志在為學(xué),豈較區(qū)區(qū)作駑馬戀棧耶,豈效無(wú)賴漢專以告訟為事,即日離渝歸東海。”
其所以然,一是性格原因,一是時(shí)代原因。傅斯年性格硬直,嫉惡如仇,遇事火爆,難以自制。在“抗戰(zhàn)建國(guó)”的旗幟下,民族主義統(tǒng)攝各種階級(jí)和社會(huì)矛盾,威權(quán)主義也被泛化和強(qiáng)化,并在很多程度上贏得人心。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傅斯年也成了史語(yǔ)所“威權(quán)”的化身,史語(yǔ)所的人敬他怕他,“檻外人”則傳他惡名,稱他“學(xué)閥”。這是一柄雙刃劍,在血刃仇寇時(shí),大氣磅礴的傅斯年,不畏權(quán)勢(shì),“雖千萬(wàn)人,吾往矣。”但有時(shí)也會(huì)誤傷同志。此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問(wèn):史語(yǔ)所成績(jī)卓然,與傅斯年有很大關(guān)系。在你看來(lái),傅斯年的貢獻(xiàn)主要體現(xiàn)在哪幾個(gè)方面?
岱峻:傅斯年是五四那一代人,他受胡適最大的影響也許莫過(guò)于對(duì)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理解:“研究問(wèn)題,輸入學(xué)理,整理國(guó)故,再造文明”。當(dāng)時(shí),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有兩種不同的發(fā)展趨向:李大釗、陳獨(dú)秀等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開(kāi)辟了中國(guó)革命的新篇,在“主義”層面上,使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走向救亡與啟蒙運(yùn)動(dòng);胡適發(fā)起的整理國(guó)故運(yùn)動(dòng),在學(xué)術(shù)文化的“問(wèn)題”層面上,用科學(xué)方法對(duì)三千年來(lái)破碎的古學(xué)進(jìn)行一番有系統(tǒng)的研究,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
傅斯年是胡適“新學(xué)術(shù)之路”的實(shí)踐者,從1928年到1937年上半年,他締造和領(lǐng)導(dǎo)的“史語(yǔ)學(xué)派”,實(shí)現(xiàn)了“爭(zhēng)東方學(xué)的正統(tǒng)在中國(guó)”的豪言壯志。史語(yǔ)所歷史組整理明清大內(nèi)檔案,校訂了大量史籍,提高了史學(xué)標(biāo)準(zhǔn);語(yǔ)言組調(diào)查了中國(guó)東部12個(gè)省的方言和西南地區(qū)的土語(yǔ),采集了許多邊疆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用科學(xué)的方法對(duì)各種方言進(jìn)行分析;李濟(jì)帶領(lǐng)考古組和中博院在安陽(yáng)進(jìn)行了15次殷墟發(fā)掘和3次山東城子崖發(fā)掘,發(fā)現(xiàn)了大量國(guó)寶,使紀(jì)元前1400年來(lái)的殷代傳聞變成信史。史語(yǔ)所因而獲得法國(guó)法蘭西學(xué)院的“儒蓮獎(jiǎng)”。
流寓李莊,諤諤之士傅斯年肩負(fù)著“衣冠南渡”的歷史重任,成了知識(shí)分子服膺的精神領(lǐng)袖。“史語(yǔ)所剛遷到南溪縣李莊的板栗坳,傅斯年坐鎮(zhèn)重慶,遙領(lǐng)史語(yǔ)所,如同下盲棋,運(yùn)籌帷幄需要更多的心智。……千頭萬(wàn)緒,幾乎每一兩天都要和李莊通一封信。”在“請(qǐng)名家”不易的情況下,傅斯年改行“找新才”的原則,賞識(shí)和激勵(lì)后學(xué)之士。學(xué)者周法高、嚴(yán)耕望、王利器、陳等人,都是在傅斯年的教誨下選定了終生從事的學(xué)術(shù)道路,并成就名山大業(yè)的。傅斯年仗義行俠,在物質(zhì)極度欠缺的情況下,還不惜賣書來(lái)接濟(jì)朋友,林徽因、梁思成夫婦和董作賓一家都曾受到過(guò)他的雪中送炭的溫情照顧。傅斯年是國(guó)民參政會(huì)參政員,他積極闡述抗日救國(guó)的政見(jiàn),還提筆為文,被稱作有軍事知識(shí)的文人。他不懼權(quán)威,大義凜然地彈劾孔祥熙。政治上他急流勇退,謝絕蔣介石招任政府委員的好意,回到史語(yǔ)所,閉口不談?wù)巍<幢愫髞?lái)到了臺(tái)灣,他也不卑不亢,迎接盟軍統(tǒng)帥麥克阿瑟時(shí),“在機(jī)場(chǎng)貴賓室,敢與總統(tǒng)及麥帥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wàn)世開(kāi)太平。”傅斯年既是一個(gè)自由主義的知識(shí)分子,又是一個(gè)民族主義者、愛(ài)國(guó)主義者。兩種思想在他身上都同樣表現(xiàn)充分,這就導(dǎo)致了他最后的悲劇命運(yùn)。
問(wèn):如果說(shuō),從文化和學(xué)術(shù)的角度,存在著一個(gè)內(nèi)涵豐富、彌足珍貴的“李莊遺產(chǎn)”,那么它的內(nèi)涵是什么?我們今天應(yīng)該怎樣繼承和發(fā)揚(yáng)?
岱峻:“中國(guó)李莊”,不僅是一個(gè)地域的概念,也是凝聚著抗戰(zhàn)文化人心中永志難忘的愛(ài)國(guó)情結(jié)。概括李莊精神,那就是舊時(shí)中國(guó)知識(shí)分子“憂道不憂貧”的理想主義情懷。
時(shí)窮節(jié)乃現(xiàn)。抗戰(zhàn)時(shí)期,中國(guó)知識(shí)界群體表現(xiàn)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覺(jué)擔(dān)當(dāng)。對(duì)于蟄處李莊的學(xué)人群體來(lái)說(shuō),盡管亦有如考古學(xué)家吳金鼎等投筆從戎和同濟(jì)學(xué)子慷慨從軍等悲壯之舉,但更多的則充分體現(xiàn)出了胡適所倡導(dǎo)的“健全的個(gè)人主義”:“救國(guó)的事業(yè)需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guó)的預(yù)備在于把自己造成一個(gè)有用的人才。”梁思成、童第周、董作賓、董同龠禾、李方桂、馬學(xué)良等在某一方面研究的領(lǐng)軍人物,都是在物質(zhì)極度匱乏、身體狀況非常羸弱的情況下,進(jìn)行田野考古或獨(dú)立研究,完成了開(kāi)山之作或扛鼎之作,奠定了某一學(xué)科的基礎(chǔ)的。甚至像李濟(jì),戰(zhàn)爭(zhēng)與疾病奪去了他兩個(gè)可愛(ài)的女兒,仍沒(méi)有耽誤手頭的殷墟考古整理與研究。
同時(shí),“人文薈,歌壯烈。績(jī)弦誦,聲未絕。念李莊父老,萍水扶協(xié)。”知識(shí)界勇于為學(xué)術(shù)獻(xiàn)身,為民族文化之命運(yùn)擔(dān)當(dāng),另一端的普通民眾,也對(duì)知識(shí)界表現(xiàn)出慣有的尊重與禮遇。鄉(xiāng)紳這個(gè)階層亦儒亦民的身份,使他們?cè)跍贤癖娕c知識(shí)界時(sh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聯(lián)系作用。
“李莊精神”,表現(xiàn)著對(duì)國(guó)家民族一種深沉的愛(ài)。今天無(wú)論我們持守什么樣的價(jià)值觀,有意義的人生總離不開(kāi)對(duì)真理和智慧的追求。只有樹(shù)立對(duì)真理和智慧的信仰,才會(huì)歷經(jīng)挫折而決不輕言放棄,才會(huì)在日益紛繁喧囂的當(dāng)下而守候自己的精神家園。同時(shí),要專注于自己的事業(yè),執(zhí)著于正在做的事,一步一步踏實(shí)地走下去,以求在靜夜,觸摸心懷,無(wú)愧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