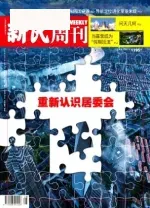11 .15祭
王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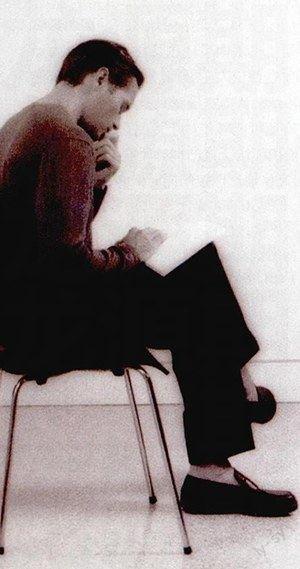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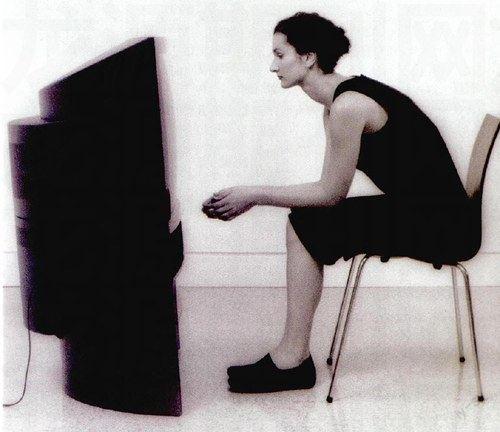
11·15,海之上,國有殤!
11·15,在這個仿佛難以破解的密碼般日期出現之前,靜安——這個上海著名的中心城區,就如同她的名字一般美好。我參加過事發地所在區域的世博后發展思路大討論,知道其城區的目標是“國際靜安”,而社區的理念是“宜居江寧”。
這幾年,以文化為重的靜安還在打造國際一流的戲劇谷。卻不料,大喜之后就是大悲。突發的大悲之后,難以置信的人們糾結于這樣幾個細節:一是“無證焊工”;二是消防主官第一時間“自我肯定”;三是事發地大樓的“最終歸宿”。
因為每一年度都要編撰《上海民生發展報告》,所以我對安全生產監督、消防臨戰指揮、災難地最后處置、事發后公眾心理疏導等課題及其國際比較,一直是極為關注的。事發的當天和第二天,我正在安全生產監督系統調研;第三天,我到事發地實地了解情況。之后迄今,在任何場合、任何通訊手段以及任何面對面的交流中,上述三個“糾結”總是無法回避的。這里,我嘗試著解構一二。
第一個細節,即關于“無證焊工”,這在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這樣職業教育發達、就業準入門檻嚴格的國家是無法理解的行業名詞。在韓國,倒也發生過有證焊工同樣操作失誤引發安全事故的案例。而在中國,不僅僅是上海,因為吝嗇雇傭付酬的原因,“無證焊工”一直是建設系統公認的弊病,而且總是各地在建工地的“導火索”。這一現象,類似于“打人的城管”總是“臨時工”一樣。而今后,即使工地上的“無證焊工”都變成了有證焊工,職能部門也要經常性地加強對其進行安全文化教育引領。如果沒有文化自覺,再熟練的技能、再細化的法規、再嚴格的行規,都可以發生漏洞,都可能積聚產生“潛規則”的土壤。
第二個細節,人們注意到——公安部主管消防的副部長在第一時間積極肯定了消防官兵的“功不可沒”;幾乎同時,上海消防局主官聲稱盡管臨戰投入設備先進,但高樓救火一直是“世界難題”。國際媒體也注意到,本次救援過程中的參戰消防官兵無一傷亡,也算是個奇跡。我當然不愿意看到參戰消防官兵犧牲的報道,因為他們是人民的子弟兵,和我們一樣都有父母、親人,都是血肉之軀。然而,第一時間“自我肯定”畢竟是不合時宜的。
我認為:煙火散盡之后,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加緊吸取災難教訓、仔細分析事故原委。同時,我們也有舉行“功過聽證會”的政治條件和社會基礎。何況,事發地居民信息化程度和媒體信息化極高;照片、錄像、視頻都刻錄著每一輛消防車到達的具體時間和實戰表現。因此,第一時間“自我肯定”如同百米起跑線上的“搶跑”行為。就算是表述“無法克服”的“世界難題”,臉部表情也應該是有愧的。有讀者和我這樣強調,既然戰勝不了所謂的“世界難題”,那也就應該引咎辭職了,不妨換個有膽有識的人來做。對此,我建議大災、大難之后關于救援工作的評價,最好由人大舉行聽證會之后向公眾發布,以避免社情民意的分裂。
第三個細節,牽動著我們內心最柔軟的深處。關于事發地大樓的處置,建筑加固專家從專業角度出發,認為大樓的創傷面是可以在短時間修復的,功能上作為商業用房和居民住宅還是可行的。然而,在電視和視頻直播下的住居者、鄰近地群眾和一般受眾,其心理的創傷面卻是無法在短時間修復的,商、住方面對其進行設計意義不大。也有讀者提議,大樓可以建成實證型的上海消防博物館;或者把原有的上海消防博物館遷入,用以從事公共安全文化教育。一個叫王思懿的小學五年級女孩和我說,如果今后膠州路建成消防博物館,她愿意和同學們去瞻仰、去緬懷。我要告訴她的是,從已有的災難后公眾心理疏導實踐來看,大樓最好拆除建成公共綠地,并由公眾集資建一座紀念碑;紀念碑上可以沒有銘文,也可以刻上遇難者的姓名。這也算是一種國際經驗吧,只是今天我們才意識到。至于大樓原住民的安置,我建議除了永久性地進行心理跟蹤治療外,實施分散性居住安置。而新鄰居們在滿腔熱情地呵護他們的同時,務必回避11·15的話題。有時候,對具體的、個體的人生而言,遺忘是為了更勇敢地前進——對政府和公權力而言,情況當然正好相反。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民生發展報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