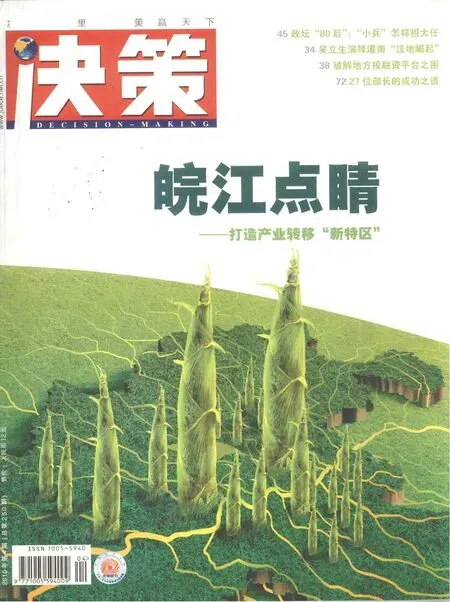開放式村部的雙樓模式
■本刊記者 賀海峰
開放式村部建設(shè)是基層治理方式的一場深刻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安徽省委書記王金山、副書記王明方、組織部長段敦厚都對這一探索給予了肯定。
2008年2月22日,農(nóng)歷正月十六。眾目睽睽之下,伴隨一聲巨響,杜集區(qū)高岳街道雙樓村部的圍墻、門樓,被轟然推倒。與此同時,鮮艷奪目的五星紅旗在村部上空飄揚起來,功能齊備的村民休閑健身廣場修建起來,高達20米的太陽能路燈矗立起來。
一場名為“開放式村部建設(shè)”的基層治理方式變革,由此破土而出。
從拆除圍墻到拆除“心墻”
王善永,擔(dān)任雙樓村黨支書迄今已有36年之久,對農(nóng)村工作游刃有余。當初甚至連他都沒有想到,推倒圍墻、建設(shè)開放式村部,會產(chǎn)生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
為什么要推進這場變革?杜集區(qū)委書記顧文告訴《決策》,直接動因是,2007年,區(qū)委、區(qū)政府投資237.7萬元新建了9個村級組織活動場所。但是,當村部越來越漂亮、硬件越來越齊全時,一個新的問題隨之產(chǎn)生:有的村部往往一兩個月都不動鎖,村部的高墻、鐵門把群眾擋在了門外,辦事、娛樂極不方便,干群關(guān)系隨之疏遠。這與黨的宗旨以及推動科學(xué)發(fā)展、構(gòu)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馳。

“區(qū)委當時的態(tài)度很明確:調(diào)整方案,拆除圍墻。黨支部是戰(zhàn)斗堡壘,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黨員、老百姓才是村部的真正主人。”顧文回憶說,“當然還有其他層面的考慮。比如,傳統(tǒng)采煤大區(qū)的特殊區(qū)情,決定了杜集信訪維穩(wěn)壓力相對較大。為什么壓力大?村干部與老百姓溝通不夠。為什么溝通不夠?村干部把自己當成了官。只有開放,才能真正實現(xiàn)村民自治;只有開放,才能切實增強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戰(zhàn)斗力、號召力。”
試點的重任,交給了工作基礎(chǔ)較好的雙樓村。
然而,反對之聲不絕于耳。阻力來自兩方面:一是村民議論紛紛,責(zé)怪村干部是“敗家子”。“好端端的圍墻,花錢建起來,又花錢推倒。”“這是不是在搞形象工程?是不是為了村干部自己的利益?”二是村干部擔(dān)心,圍墻拆除之后,村部安全如何保障。“拴只狼狗在那里也沒有用。”“要隨時作好東西被砸爛、被偷走的準備。”
村支書王善永當時也是躊躇再三,“非常心疼,舍不得拆。經(jīng)過10多天激烈的思想斗爭,我才最終下定決心。”隨后,他多次主持召開黨員代表大會、村民代表大會,反復(fù)征詢意見,終于達成共識。盡管威信很高,但他坦言“整個過程十分艱難”。
開放式村部建成后,雙樓村氣象為之一新。開闊的廣場、漂亮的中央花壇、雅致的涼亭、高規(guī)格的籃球場、一應(yīng)俱全的健身器材……每逢天氣晴好,村民總是自發(fā)來到這里,組織戲曲、舞蹈、小品、籃球比賽、拔河比賽等各種文體活動,剎那間,村部成為一片歡樂的海洋。過去村民不敢去、不愿去、不能去的“冷清院落”,變成了時時開放、人人愛去、群眾滿意的“溫馨家園”。
而更讓村干部驚訝的是,時至今日,村部沒有碎過一塊玻璃,沒有丟過一件東西。“千萬不要低估老百姓,他最能分清什么是真正為了他好。他信服的就會擁護,他擁護的就會愛護。”顧文告訴《決策》。
“群眾動嘴,干部跑腿”
開放式村部更深一層含義,是村干部隨叫隨到,全天候為村民服務(wù)。
據(jù)說,在北方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稅取消后,老百姓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有吃有喝不找你,不偷不搶不怕你,有病有事要找你,解決不了就告你”。村干部和村民隔閡之深,基層組織治理方式之滯后,可見一斑。有人比喻,干部是油,老百姓是水,油珠子漂在了水面上。
根本原因在于兩條:一是村部功能不健全,群眾來了沒法辦事;二是村干部服務(wù)水平跟不上,群眾來了辦不好事。
開放式村部建設(shè)顯然是有的放矢。其可貴之處,在于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拆除一堵墻,建好六個室,設(shè)立四個欄,打造五個中心”的工作思路。具體地說,就是推倒村部圍墻,同步建立黨員活動室、圖書閱覽室、為民服務(wù)代理室、調(diào)解警務(wù)室、文體活動室、計生服務(wù)室,設(shè)立黨務(wù)公開欄、村務(wù)公開欄、信息發(fā)布欄、政策宣傳欄,把開放式村部打造成為黨員活動中心、村民議事中心、便民服務(wù)中心、教育培訓(xùn)中心、文化娛樂中心。一言以蔽之,方便群眾、拓展服務(wù)功能,被擺在了頭等重要的位置。
在雙樓村為民服務(wù)代理室,我們看到,村部為村民提供了好幾十種代理服務(wù)。戶口遷移、生育證辦理、家電下鄉(xiāng)補貼……只要村民備齊手續(xù)交到村部,均由村干部負責(zé)到鎮(zhèn)里或者縣區(qū)代辦。村民王淮北告訴《決策》:“以前辦理身份證,一般要往街道派出所跑好幾趟。現(xiàn)在大不一樣了,只要我們把照片交到村部,村民干部就會直接把辦好的身份證送到家門口。”過去的“干部指揮、群眾跑腿”,已經(jīng)切切實實變成了“群眾動嘴,干部跑腿”。
又如,以關(guān)愛留守未成年人為初衷的“少兒之家”建設(shè)。雙樓村安排“四老”(老黨員、老干部、老校長、老教師)作為校外總輔導(dǎo)員,同時聘請校外文體輔導(dǎo)員、健康輔導(dǎo)員、法制輔導(dǎo)員、安全輔導(dǎo)員,全面開展“愛心助成長”和黨員一對一結(jié)對關(guān)愛留守未成年人的“黨心暖童心”等活動,把開放式村部打造成了少年兒童的生活之家、學(xué)習(xí)之家、文體娛樂之家。國家信訪局常務(wù)副局長王石奇聞知此事,大年初一從北京專程趕到杜集區(qū)進行觀摩調(diào)研。
村部功能由行政命令型向指導(dǎo)服務(wù)型轉(zhuǎn)變、由單一辦公向多種服務(wù)轉(zhuǎn)變,逼迫著村干部必須自覺加強學(xué)習(xí)、轉(zhuǎn)變作風(fēng)、提升能力。王善永說,作為一名村干部,自己肩上的責(zé)任更重了,帶頭學(xué)理論、學(xué)政策、學(xué)技能的勁頭更足了。另外,開放式辦公,增加了工作透明度,黨員干部的言行舉止、工作作風(fēng)、辦事能力,都置于群眾的視野之內(nèi)和監(jiān)督之下,有利于增強服務(wù)意識、提高工作效率,“在這過程中,我們也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村民們在想些什么、需要什么。”
高岳街道辦事處工委書記陳明月告訴《決策》:“過去群眾上訪常常繞過村和街道,直接到區(qū)、市政府。現(xiàn)在,開放式村部建設(shè)使群眾有了可以說話的地方、能夠辦事的地方,村干部也不再把矛盾往上推。2009年,高岳街道拆遷1280戶、征地3200畝,沒有發(fā)生一起群體上訪事件。”
長效機制如何建立
兩年來,雙樓村開放式村部建設(shè)總計投入80余萬元。顯然,如果沒有資金來源,開放式村部不僅很難建立起來,而且很難發(fā)揮出應(yīng)有的功能,為老百姓辦實事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怎么辦?雙樓村因地制宜,通過大力發(fā)展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一手抓促進農(nóng)民增收,一手抓壯大集體經(jīng)濟。以發(fā)展蔬菜設(shè)施栽培為例,通過土地流轉(zhuǎn),全村先后建設(shè)節(jié)能溫室大棚159棟,然后承包給農(nóng)戶。村黨支部與山東壽光合作,做好產(chǎn)前引進新品種、產(chǎn)中引進新技術(shù)、產(chǎn)后開拓市場等一條龍服務(wù)。村民閆明承包了3個蔬菜大棚,年均純收入接近6萬元。“這比外出打工強多了!”他說。而村集體經(jīng)濟年均純收入也隨之水漲船高,一舉超過了70萬元,真正實現(xiàn)了可持續(xù)發(fā)展。
“雙樓經(jīng)驗”很快在杜集區(qū)推廣開來。全區(qū)一共建立健全村民議事、黨員活動、結(jié)對幫扶、村民素質(zhì)教育、村干部培訓(xùn)等長效機制20多項,從根本上保證了開放式村部的有效管理以及各項工作的有序展開。譬如,區(qū)委制定“村干部集中培訓(xùn)月”,一周一專題,把信訪接待、文明創(chuàng)建、全程代理等納入培訓(xùn)計劃,邀請學(xué)者、官員講課,切實提高村干部的服務(wù)水平。現(xiàn)在,村干部不僅待遇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高,而且紛紛上起電大,不少人甚至已經(jīng)拿到了本科文憑。
2009年6月,淮北市委書記畢美家敏銳地預(yù)見到,這不僅是拆除一堵墻,這是一場革命!市財政立即撥專款2600萬元在全市推廣開放式村部建設(shè)。其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安徽省委書記王金山、副書記王明方、組織部長段敦厚等都對這一探索給予了肯定。
中國浦東干部學(xué)院調(diào)研組認為,發(fā)軔于雙樓村的開放式村部“實際、實用、老百姓得實惠,可學(xué)、可比、可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