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智造”
■本刊記者 徐浩程
深圳已經意識到那些曾經帶給深圳成功的全球化力量同樣可以扼殺深圳,產業(yè)競爭力逐步下降而資源和環(huán)境壓力日益上升的現實,迫使深圳開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走上自主創(chuàng)新之路。
華為與富士康誰能代表深圳的未來?
在2009年之前,這個問題也許還不會得到明確的回答,但在富士康2010年初一連串事件后,對于富士康外遷天津等地,深圳市一位官員開始告訴媒體,“富士康要走,對于深圳短期可能有點壓力,但長期是件好事。政府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姿態(tài)會表一下,但不是真的想留。”
而對于華為,一位深圳市的前領導曾說過:如果失去一個華為,深圳將至少5年暗淡無光;失去兩個華為,深圳的現代化進程可能放緩8年;失去三個華為,深圳就淪落為一個死氣沉沉的三流城市。
顯然,深圳已經意識到那些曾經帶給深圳成功的全球化力量同樣可以扼殺深圳,產業(yè)競爭力逐步下降而資源和環(huán)境壓力日益上升的現實,迫使深圳開始調整經濟發(fā)展方式,走上自主創(chuàng)新之路。
《第三次浪潮》的沖擊
這座城市自主創(chuàng)新夢的發(fā)端與一本書——《第三次浪潮》有關。

這本1983年引入國內的書給了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粱湘不小的觸動和啟示,挑起了深圳對科技與先進工業(yè)的欲望,并最終誘發(fā)了中國大陸第一個科技園區(qū)的誕生——1985年7月,在粱湘的積極謀劃下,深圳與中科院聯合開發(fā)建設的深圳科技工業(yè)園奠基。
此后,科技園雖然幾經變遷,卻最終嬗變?yōu)樯钲诳萍嫉膿u籃,這也許是當時的決策者始料未及的。
1996年,以科技園為中心,深圳整合周邊地區(qū)建設“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yè)園區(qū)”。到2001年,在高新區(qū)的基礎上,深圳市又規(guī)劃了“9+2”的深圳高新技術產業(yè)帶。目前,在這片區(qū)域,集聚了深圳絕大部分高新技術產業(yè),僅2008年就實現工業(yè)總產值2278.58億元,單位面積產出居國家高新區(qū)首位。
在硬件建設的同時,深圳創(chuàng)新夢的軟環(huán)境也在逐漸成形。1993年5月,深圳發(fā)布了《深圳市企業(yè)獎勵技術開發(fā)人員暫行辦法》等文件,以資金及政策優(yōu)惠等形式鼓勵企業(yè)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當年6月,深圳再次發(fā)布《深圳經濟特區(qū)民辦科技企業(yè)管理規(guī)定》,對內地科技人員來深圳創(chuàng)辦科技企業(yè)給予政策優(yōu)惠。
自此以后,深圳市多次出臺鼓勵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的文件及優(yōu)惠政策,尤以1998年2月出臺被稱為“22條”的《關于進一步扶持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的若干規(guī)定》為代表。該條例充分利用了深圳“特區(qū)”的優(yōu)勢,在全國率先出臺一些針對高科技的突破性的扶持政策,涉及稅務、財政、國土、人事、勞動、住宅、外事、銀行等部門迅即研究落實。
這是中國地方政府在財稅等經濟政策上進行突破的首次嘗試。
1998年9月,深圳市再次打破了國家規(guī)定企業(yè)“技術入股”不能超過20%的限制,發(fā)布《深圳經濟特區(qū)技術成果入股管理辦法》,從而使華為于1998年后在公司內部大規(guī)模實行“全員持股計劃”提供了法律支撐。
在這一系列軟硬環(huán)境的建設中,深圳涌現出了一大批憑借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在國內外市場各領風騷的行業(yè)龍頭企業(yè),形成了國內最大的本土創(chuàng)新企業(yè)群。深圳市政府做的一個統(tǒng)計顯示:深圳高新技術產值當中,有50%來自本土企業(yè);同時,深圳有“4個90%”的殺手锏,即90%以上研發(fā)機構設立在企業(yè),90%以上研發(fā)人員集中在企業(yè),90%以上研發(fā)資金來源于企業(yè),90%以上職務發(fā)明專利出自于企業(yè)。
2009年6月19日,時任深圳市代市長的王榮在騰訊深圳總部調研時表示:“在金融危機下,深圳依然能夠保持一個較為理想的增長態(tài)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有一批成長性好、抗擊能力強的高科技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
“星云”的背后
2009年11月,第十一屆高交會在深圳開幕。
開幕當天,最大的主角是國家超級計算機深圳中心以及落戶中心的國內第一臺、世界第三臺實測性能超千萬億次的超級計算機“星云”。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都認為該工程絕非一個重大項目這么簡單,而將各種意義與詮釋附著在上面。
之所以如此,是源于深圳自主創(chuàng)新特色背后的尷尬。“4個90%”是深圳的自主創(chuàng)新特色,同時,也正是深圳的尷尬。由于歷史原因,深圳長期徘徊在國家重大科技布局之外,國家級研究機構匱乏,加上本地缺乏研究型大學,導致深圳盡管企業(yè)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較強,源頭創(chuàng)新能力卻嚴重滯后,這也使得深圳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不夠。因為沒有研究型大學和重量級科研機構,科技創(chuàng)新大多只能在企業(yè)中進行。
“這種創(chuàng)新模式太自發(fā)、太民間,是無序的。”南山區(qū)科技局局長朱建平分析道,所謂無序,就是企業(yè)想到或者有需求時,才會進行創(chuàng)新探索,沒有點面結合,沒有整體布局,有點“亂點鴛鴦譜”的意思。
2003年前后,深圳高層愈發(fā)感受到,如果說以前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主要是資金和技術儲備不足的話,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缺乏后勁,缺乏自主核心競爭力。
“因為缺乏核心競爭力,我們的產業(yè)雖然很大,但是我們又感到很苦。”朱建平頗有些無奈地說,現在的IT產業(yè)源頭在西方,原始核心技術、標準以及協(xié)議都在別人手上,“我們必須用更多外圍專利才能讓人家開放接口,華為、中興每年要為此付出高額的專利費。”
一個更為典型的例子是,加拿大RIM公司放棄了其在深圳建立一個通訊研發(fā)中心的打算,盡管深圳擁有華為、中興兩大全球通訊“新貴”,有著良好的產業(yè)基礎。
“RIM公司認為,即使是選擇通訊產業(yè)較弱的廣州,也比選在深圳好,因為他們至少有一個電信研究所。”加拿大高新技術協(xié)會中國首席代表孫曲說,過于商業(yè)化和實用主義的氛圍,讓深圳缺失了很多基礎研究的必要條件——非商業(yè)的、“中性”的科技大學、研究機構等,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種軟環(huán)境。
從那之后,深圳開始籌建南方科技大學,并布局引進國家級的科研機構和項目,以解決產業(yè)發(fā)展的后勁乏力問題。
1999年,深圳高新區(qū)內成立了深圳虛擬大學園,目標是開展人才培養(yǎng)和實現院校科研成果的轉化。至今高新區(qū)虛擬大學園已引入51家國內外大學入駐異地辦學。
2004年10月,“深圳國際科技商務平臺”建立,是高新區(qū)打造高端人才、技術平臺載體的又一嘗試。該商務平臺目前已引進包括加拿大高技術協(xié)會、英國西南英格蘭地區(qū)發(fā)展局、美國CEO俱樂部等22個國家和地區(qū)的31家海外機構入駐。
而在國家超級計算機深圳中心落地前后,另外四個國家工程實驗室以及一批重大科研機構和創(chuàng)新團隊亦先后落戶深圳。
顯然,在企業(yè)主導的創(chuàng)新之外,深圳正在構建更多的創(chuàng)新載體與平臺,這構成了深圳完整的自主創(chuàng)新力。
再造一個深圳工業(yè)
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的增強,將帶動整個深圳的變遷,這首先體現在主導產業(yè)上。
2010年2月11日,深圳市三大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發(fā)布會上,時任深圳市常務副市長許勤宣布,生物、新能源、互聯網三大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將成為未來深圳的支柱產業(yè)。
在許勤看來,三大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的出臺可謂水到渠成。對于全國“熱捧”的這三大產業(yè),深圳市在產業(yè)規(guī)模、產業(yè)能力尤其是創(chuàng)新能力方面,都有自己的優(yōu)勢。其中一個典型是互聯網產業(yè)。
近期,深圳打造互聯網支柱產業(yè)戰(zhàn)略已初現端倪。2009年9月20日,阿里巴巴首席執(zhí)行官馬云來到深圳;2010年2月1日,百度首席執(zhí)行官李彥宏也來了;2010年3月28日,已永久落戶深圳的中國IT領袖峰會第二次會議召開,互聯網巨頭、創(chuàng)業(yè)投資巨頭齊聚深圳。以騰訊為基礎打造的深圳互聯網支柱產業(yè)雛形已經開始顯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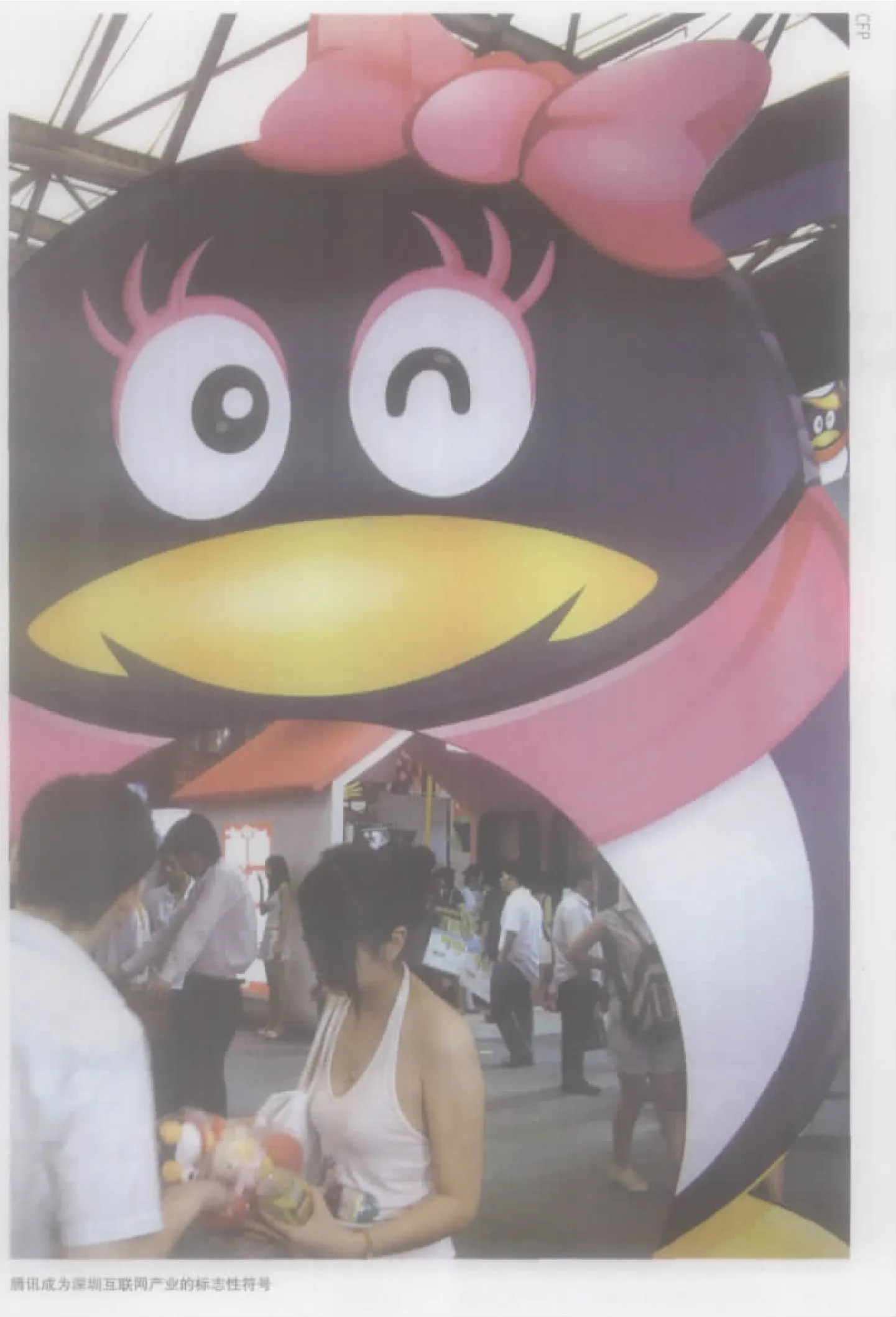
按照許勤的期望,未來7年,深圳將通過規(guī)劃部署、通過政策的引導和政府資金以及社會資金的共同投入,迅速壯大包括互聯網在內的三大戰(zhàn)略性新興產業(yè),預計到2015年形成6500億元的規(guī)模。
2009年,深圳實現地區(qū)生產總值8201億元,按照6500億元的目標規(guī)模計算,三大新產業(yè)在產值上相當于再造一個深圳工業(yè)。
不過,這還不是深圳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全部的效益,更重要的是,深圳將憑借其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打造創(chuàng)新型城市。
深圳對“創(chuàng)新型城市試點”的堅持,始于2005年。在是年5月召開的深圳第四次黨代會上,深圳明確提出“實施自主創(chuàng)新戰(zhàn)略,建設自主創(chuàng)新型城市”的奮斗目標。2006年4月深圳向國家發(fā)改委呈報了《關于懇請國家發(fā)改委共建深圳區(qū)域創(chuàng)新城市的請示》。這是深圳第一次向國家發(fā)改委申請建設“創(chuàng)新型城市”。
等到2008年3月12日,深圳市相關領導再次赴京向國家發(fā)改委呈報了一份《關于深圳建設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的請示》,重申了深圳的意愿。此時,在這場略顯漫長的競賽中,深圳身邊已經多了不少頗具實力的挑戰(zhàn)者——2006年初,上海、武漢、蘇州等城市幾乎是不約而同地加入了申報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試點的行列。
3個月后,憑借其多年形成的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深圳終于收到國家發(fā)改委的一紙批文。2008年9月,深圳召開全市自主創(chuàng)新大會,頒布出臺《關于加快建設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的若干意見》和《深圳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總體規(guī)劃(2008-2015)》以及《關于增強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促進高新技術產業(yè)發(fā)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等重要政策文件,在加大科技投入、加強創(chuàng)新基礎能力建設、扶持企業(yè)自主創(chuàng)新、保障產業(yè)發(fā)展空間、吸引創(chuàng)新人才等方面都提出了操作性強、含金量高的創(chuàng)新優(yōu)惠扶持政策。為了切實有效推進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建設,深圳進一步成立了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領導小組,印發(fā)了《深圳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總體規(guī)劃實施方案》。
“創(chuàng)建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不僅僅是深圳的事,也是國家創(chuàng)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重要步驟”,許勤一語道明建設國家創(chuàng)新型城市的重大戰(zhàn)略意圖。對此言最好的詮釋是5年前美國《時代》周刊刊發(fā)的一篇文章,在這篇題為《深圳的誕生與再度輝煌》一文中,作者稱“深圳今天面對的轉型問題,整個中國經濟也將遇到,深圳今天的探索將為中國的下一步提供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