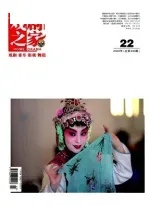塑造戲曲人物形象之我見——從我扮演苗老伯說開去
□連君斐
從事戲劇表演事業已有三十余年,屈指算來,扮演各種不同的老生形象也有數十個。這次我們寧波市鄞州越劇團排演謝柏梁老師創作的極具現實主義題材的新編現代戲《孔雀西南飛》,團領導決定讓我扮演苗老伯,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全新的挑戰。
該劇講述80后的寧波姑娘蘭芳赴貴州支教的故事。通過講述浙黔兩地互助互愛的感人事跡,展現了寧波新一代青年敢于挑戰自我、樂于助人的風采。歌頌了苗老漢一家的熱情純樸、樂于助人的優良品德;描述了主人翁實現自我人生價值的心路歷程和人格魅力。
全劇通過描述東部沿海城市與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之間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行為的碰撞,折射出寧波人“敢為、求實、爭先”的精神面貌,贊美了新一代寧波人尤其是80后與時俱進和敢闖敢試的創業理念。同時,鼓勵有知識、有抱負的青年到基層一線,到艱苦的環境里去磨煉自己,通過自身奮斗實現人生的最大價值。

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演好戲中的角色,讓觀眾在欣賞真善美的同時,獲得人生的啟迪,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出演苗老伯的任務,決心竭盡全力塑造一個生動的形象。
作為一個女演員,扮演古裝戲的男性形象,有不少傳統的技巧可以借鑒,即使對角色理解不深,也可以借助豐富的水袖、胡須、臺步等技巧手段來彌補外形與內在的不足。可是現代戲,沒了程式化的技巧,怎么辦呢?再加上我退居管理崗位,近年未經常性參與演出,這次重回舞臺底氣不足。接受這個任務后,感到角色演技難度大、心里壓力重、有畏難情緒。但想到劇中主人翁在那么艱苦的環境中,堅持教書育人,我沒有理由退縮。于是,我積極行動起來,一步一步地開始了這次艱辛的角色創作之旅。
一、角色分析是塑造人物的基礎
我拿到劇本反復閱讀,揣摩故事情節。從作者提供的文字中認識劇中的“我”——苗老伯。從“暴雨傾風怒嘯、東邊日出西邊雨”等詞分析苗寨時而大雨滂沱,時而晴空萬里的無常氣候。從幺妹省下吃飯錢攢學費、反對說洋話、巫醫治病、不會開易拉罐等情節中,了解苗寨人貧困、守舊、落后的現狀。從“寨子里是有規矩的”、“他們都是善良質樸的山里人”、“這辦法可是老祖宗傳下的”、“米酒香噴噴,我來敬一杯”等臺詞中體會苗老伯這個山寨里的長輩形象。作為苗寨里的長者,劇中的“我”應該具有因循守舊、愛憎分明、勤勞純樸、心地善良、熱情豪放的性格。他是歷經了人生風霜雪雨,在漫長的歲月蹉跎中,培養出了自信和強悍的性格。我深知,只有在對人物內心拿捏準確后,我在舞臺上的表演形式才能更加準確生動。
二、角色形象構思是塑造人物的依據
通過對苗老伯上述文學形象的分析,我對苗老伯有了基本的認識,從而激起我對生活中類似“我”的聯想,有意識地在生活中觀察老人的形態。比如:路上看到有的老年人雙手背后,步子邁得較慢,目光局限在眼前等等。我把這些生活素材作為創作原料,開展創作想象,進行“我”的形象構思,使我通過腦子里的表象活動“看到”未來舞臺演出時“我”的形象。
“我”的外部形象設想:七十左右,古銅色的肌膚,臉上較多皺紋,胡子蒼白,彎著脊梁,習慣性拿著煙筒,邁著八字步,說話語調緩慢,目光看不遠。生氣時神情嚴肅,高興時眉開眼笑。
心理行動線設想:因為生活在貧困的山寨,思想觀念落后,所以迫切希望能學到解決溫飽、增加收入的實用知識。“我”對蘭老師教聽不懂又沒用的洋話持反感的態度。因為山寨氣候變幻莫測,出行非常不便,所以有病一般用土辦法醫治。“我”支持巫醫為幺妹治病,阻止蘭老師把幺妹送到醫院治療,也擔心山高路險會出人命。蘭老師在苗寨吃苦受累受委屈,為苗寨拉贊助、建學校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好事,使“我”感到以前對她誤解很慚愧。在她支教期滿時,苗寨舉行最隆重的儀式歡送她,表達對她的歉意和敬重之情。
三、角色形象體現是塑造人物的主要環節
我和苗老伯無論從哪一方面看都存在著很大的不同,如:性別、年齡、生活環境、成長過程等等。我必須克服這些困難,像他一樣地去思考、去生活、去活動。為了進一步加深對“我”的了解,接近我和“我”的感覺。我上網查閱苗族習俗、苗寨圖片,觀看苗族風情碟片,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態。使“我”眼前有物、心中有底。盡可能準確地將苗老伯形象表現在舞臺上。
四、“心到”才能眼明,眼明才能“傳神”
在第二幕,“我”聽說侯懶龍半夜去到寧波姑娘窗前把情歌唱,此時作者沒給臺詞,我用藐視的眼神盯著侯懶龍,以此來表現“我”心里討厭侯懶龍痞性的情緒。侯懶龍說寧波來的老師教洋話,學校稱作“屎庫兒”(school)、兄弟稱作“不辣子”(brother)、老婆稱“外敷”(wife)等聽不懂的詞,使“我”茫然,從心里反對學洋話。接著傳來畫外音:“How do you do”,我在表演時注意念白節奏的把握,放大音量放慢語速,一字一句力求讓同臺和觀眾聽清楚,說:“什么,豪賭、好賭還要賭?……”這時觀眾會心地發出笑聲,心里領會了作者沒有明說的意思,戲劇效果也出現了。蘭老師說:“學會英語,就等于開啟了世界的一扇窗戶。”學生們七嘴八舌附和著,“我”邊走邊嚴肅認真地說:“要那么多窗戶做什么?”再瞪了娃兒們一眼,用眼睛在說:“別多嘴!”然后回頭,目光柔和、慈祥地看著蘭老師,表現對遠方客人的尊重。接著用關心的語氣,婉轉地說:“蘭老師,山里冷窗戶要少開點。”我分析他潛在幾層意思:一是想反對、阻止教洋話,一時找不到理由;二是誠懇地提醒她少開門窗防寒氣、防流氓、防野獸。有一娃說:“這是知識的窗戶,不是我們家的窗戶。”這時“我”神色略顯尷尬緊接著說:“不管什么窗都要少開,就是當年的義和團,也不許念洋經。”于是和苗老太、侯懶龍等明確地反對教洋話,要求教點種地、養豬、算算寫寫的實用知識。通過這些行動,為蘭老師支教路上設置障礙,讓觀眾看到、聽到、感受到“我”和苗寨人保守的思想觀念。
五、塑造人物最好體驗人物一樣的生活
這點很難做到,但遇到相類似的情緒和感覺可以“借”。苗寨人喜歡抽煙,“我”習慣性常帶著煙筒。初排時我很別扭,看了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后,“借”了紀曉嵐的一些動作,比如:用雙手把煙筒放在腋下,還可以用它指指點點等等。解決了拿著煙筒不自如的問題。
第四幕“幺妹生病”初排時,“我”蹲在舞臺一角吸煙,覺得不合情理,也找不到感覺。連排的一段日子里,我把得知自己的親人查出甲狀腺結節需手術的切身體驗“借”到“幺妹生病”的情景中。最后幾次排練,我把幺妹看似自己的親人,“我”蹲到她身邊,運用生活化的肢體語言來展示這一段情緒。我為人物設計了一系列的小動作,比如:為她捶捶背、摸摸額頭。在巫醫對她作法痛打時,我用不忍的、哀傷的眼神,虔誠祈禱的表情來體現擔憂之情,這是情動于衷而形于外的表現手法,舞臺感覺也很自然,憑著本色,表達了我和“我”真實的內心感受。
六、演員在舞臺上要把自己讓位給角色,說他要說的話,做他能做的事。
表演時必須忘掉與角色無關的情緒,把所學的技巧運用于劇情中,為塑造人物服務。根據苗寨的民族風情和“我”的性格特點,最后一幕歡送儀式,男女老少都應該載歌載舞。這舞蹈對我來說難度更大,一是我從沒跳過舞蹈;二是頸椎、腰椎間盤突出加高血壓,使我學習舞蹈越發艱辛。最初排練時,“我”坐在上場門的石頭上觀看,但這不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規定情境。在大家的幫助下,我克服病痛的折磨,苦練了幾個舞蹈動作。到合成彩排時,“我”情不自禁地進入興奮狀態,同大家一起跳舞、歌唱、敬獻醇香的美酒,演繹著苗族獨特的生活習慣,展現了苗族同胞純樸善良、熱情好客的豪爽性情。
創作過程是艱辛的。人物的塑造,沒有完美,只有更美。舞臺形象的最后完成是由觀眾的想象、觀眾的感受形成的。《孔》劇公演后,聽到一些評論:有的觀眾說這老頭演得真像;有的朋友說演得真實可信。該劇多次在中央電視臺戲曲頻道播放并榮獲“向祖國匯報—寧波市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優秀展演劇目”。
我將在今后的創作旅程中,不斷精益求精,以戲出情、以情動人、以人見善,把苗老伯——這個新時代的老生形象塑造得更美。